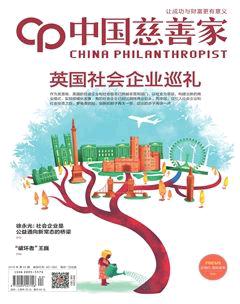向春:環保局的“戰友”
章偉升
2014年1月,一封從重慶發往北京的舉報函,在半年后引發了中國環保界的一股“風暴”。
舉報函長達16頁,指出129名環保系統公職人員將環境影響評價(以下簡稱環評)師的資質“租借”給環評機構以牟取利益。
按工程項目審批流程,政府部門和環評機構在環評業務上嚴格分開。且法律明令禁止公務員參與營利性行為,也不得在營利性機構中兼任職務。這些名為環評公司環評師,實為國家公職人員的“影子環評師”,并不從事為環境把關的環評工作,但每一份環評報告均借由他們的“資質”撰寫。
2011年起,環保組織重慶兩江志愿服務中心(以下簡稱重慶兩江),開始根據公開資料搜集、整理關于環評師和環評機構的違規信息,并在2014年年初將舉報函遞交至環保部。為了避免舉報函石沉大海,重慶兩江的創始人向春每隔一兩個星期就會致電環保部詢問進展。
2014年7月31日,環保部開始清除“影子環評師”,對62人予以通報批評并注銷登記。9月16日,環保部再次發文,通過取消或降低資質、縮減業務范圍以及限期整改等方式整肅31家環評機構。
向春介紹,在被處理的名單中,近三分之二系重慶兩江舉報,“類似的名單我們還有很多,只是什么時候公布的問題。”
至此,重慶兩江與環保部完成了一次令人頗為驚奇的“官民合作”。實際上,與政府合力推動環保一直是重慶兩江的基本策略。
一家位于重慶某區的電鍍廠造成大面積水體污染,其廠區緊鄰自來水廠取水口。該區環保局屢番促其整改卻不見效果。為了摘除這顆“腫瘤”,在只有幾十名外勤的情況下,環保局不惜派人全天監察,甚至強堵排污口。廠方和環保局長期僵持不下。
2013年,重慶兩江介入做污染調查和水質檢測,發現工廠每次排出的水都嚴重超標,于是也開始給廠方施壓。經過半年的交涉和評估,廠方認識到所制造的污染已經無法通過凈化設備解決,便將生產線全部拆除。向春認為,在這一輪的“博弈”中,民間組織產生了增量的作用。“在以前,企業只感受到了政府的壓力,現在又增加了另外一個壓力,所以改善速度很快。”
在電鍍廠所在的區域,一家日本五十鈴集團投資的工廠不斷向大氣中排放大量污染物,被向春比喻為大氣方面的“腫瘤”工廠。電鍍廠項目的成功合作,為重慶兩江與環保系統再次聯手“拿下”這家工廠夯實了基礎—雙方詳細商討,共同約見了廠方負責人。環保局從行政角度告知廠方,若不改善污染狀況,新的項目審批便不予通過、新上馬的生產線也得停工等等;而向春則從民間輿論、投融資,甚至通過日本環保團體向該廠母公司五十鈴集團施壓等方式,督促該工廠予以整改。“做電鍍廠時,我們和當地環保部門還只是從各自的角度、兩條線去推進。但是我們做大氣這家時,完全是精誠合作。”
現在,重慶兩江與當地的環保系統已經建立了相互信任的良性關系。“有時候也要相互給時間”,向春坦言,建立信任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推動政府部門的行政效能需要講究節奏,并非越急越好。“比如重慶環保部門本身的變化是我們最為關注的,他們提高能效就是整個系統提高效能。民間組織的價值就是在這個層面進行推進,而不僅是在某個個案上的結果和價值。”
民間組織在向春看來完全可以是政府部門非常有力的“戰友”,只要雙方力量配合得當,污染企業的整頓速度會大大加快。
他說行政部門行使權力需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內,這會產生時間差,“他們去查企業排污,需要監察、附議、聽證等等,一套行政處理流程下來,半年的時間都沒了。”而民間組織的靈活性在于“只要不違法,都可以干”。媒體、互聯網和資本市場都是民間組織推動企業治理污染的手段,“比如現在的公益訴訟,這也是政府覺得民間組織可以在里面發揮作用的地方。環保部門自己不能做,民間組織可以。行政罰款可以罰你一百萬,這對企業構不成太大壓力,但通過公益訴訟可以讓企業損失一兩千萬。”
向春認為,民間組織的監督也是在幫助企業贏得未來。“如果企業因為我們的監督而較早做到了可持續化,未來被淘汰的可能性就比較小。眼下能賺多少錢,并不代表你能走多遠。”
與政府部門相互信任、合作,于向春而言,也有助于從事環境監督時降低人身風險。“我們基本不會和企業單獨接觸,因為風險太大。在重慶做環境監督的話,我們會拉上環保部門一起,而且三方會談會比較理性。”
在2014年亞布力論壇上,向春表示,他從事環保八年幾乎沒有遇到過來自企業的任何威脅。
在向春的經驗里,最大的風險來自兩方面:一是在污染現場,二是曝光事實后。為了規避現場調查時遇到傷害,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工作以縮短現場的作業時間。如果被廠方發現,盡管在廠區外調查并不違法,但無論對方要求刪照片還是扣押拍攝器材都予以配合。“刪東西是他們最大的訴求,回頭再拍就可以,但鬧到派出所浪費的時間更多。而且,那還是當地的派出所,對吧?”不起爭執、能安全離開現場是向春規定的第一工作原則,“至于后期的打擊報復,真是沒遇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