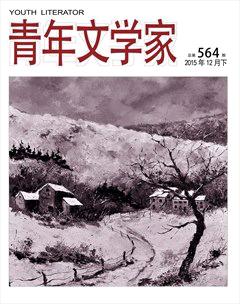從結(jié)構(gòu)主義視角淺析電影《賽德克?巴萊》
摘 要:魏德圣導(dǎo)演的影片《賽德克·巴萊》以歷史上真實的“霧社事件”為原型,其中彰顯了歷史、文化、人性等多方面的深刻內(nèi)涵。本文擬從結(jié)構(gòu)主義的角度對其分析,發(fā)掘《賽德克·巴萊》中人類學(xué)的色彩和魅力。
關(guān)鍵詞:結(jié)構(gòu)主義;野蠻;文明
作者簡介:彭翀,女,漢族,湖南永州人,廣西師范大學(xué)2013級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方族群文化。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6-0-02
影片《賽德克·巴萊》的名字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刻內(nèi)涵。“賽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萊”是真正的意思,賽德克·巴萊即“真正的人”。在賽德克族的信仰中,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賽德克·巴萊。在他們生命結(jié)束走向祖靈之家的時候,要經(jīng)過彩虹橋,彩虹橋的盡頭是一個獵場,只有真正勇敢的戰(zhàn)士才能通過這座橋成為賽德克·巴萊。電影《賽德克·巴萊》即講述了賽德克族的一段悲壯歷史:1930年,臺灣在日本的統(tǒng)治之下,原住居民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shù)缆时姺纯谷毡镜闹趁窠y(tǒng)治,發(fā)動了震驚當(dāng)局的霧社事件。
列維斯特勞斯作為結(jié)構(gòu)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二元對立思想深邃而明晰,為人類認(rèn)識歷史、認(rèn)識自身、認(rèn)識他者提供了一個極為有利的工具。在《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中,充滿了二元對立的事物,這些事物充分反映了人們二元對立的思維和情感。從結(jié)構(gòu)主義的視角賞析這部電影,不僅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賽德克族人民的精神內(nèi)核,也可引起諸多對于現(xiàn)代文明和發(fā)展的反思。
一、獵場與學(xué)校 :野蠻與文明的碰撞
“沒有出草取過敵人首級的男人,是沒有資格在臉上紋上圖騰的。收橋的祖靈看著他們,干凈沒有圖騰的臉,你們不是真正的賽德克!”從這一方面來看,賽德克族是野蠻的,或者說,他們可以被歸為現(xiàn)代文明定義的野蠻體系中。日本人殖民者占領(lǐng)臺灣島后,在當(dāng)?shù)亟⒘肃]局、商店、學(xué)校,并派出了老師對賽德克族的小孩進行日語教學(xué),傳授他們生活的禮儀。
電影中,花岡一郎作為一名賽德克族人,已經(jīng)接受了日本的文化并為日本殖民政府工作,他對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shù)勒f:“頭目,我們現(xiàn)在不好嗎?我們不必再靠獵殺過日子,這樣文明的生活不好嗎?”莫那·魯?shù)婪磫枺骸笆裁唇凶鑫拿鳎磕腥吮黄葟澭崮绢^,女人被迫跪著幫傭陪酒……郵局?商店?學(xué)校?什么時候讓族人的生活過得更好?反倒讓他們看見自己有多貧窮了!”莫那·魯?shù)赖倪@番話,幾乎將表象中的野蠻與文明顛倒,引發(fā)更深層的思考。隨著情節(jié)的不斷推動,日軍在打壓賽德克族人的抵抗過程中一直處于劣勢,日本軍官最終決定使用糜爛性炮彈滅絕賽德克族人時,他對下一級的軍官說了這樣一段話:“叫你們文明……你們卻逼我野蠻!”至此,日本殖民者的行為將其文明的外套卸下,裸露出他們野蠻的目的。當(dāng)文明的方法無用時,日本人決定用生化武器征服他們,糜爛性炮彈對人身體的傷害是殘忍并具有毀滅性。
野蠻與文明是對立的,在這部電影里也是互相轉(zhuǎn)換的。看似野蠻的賽德克族,實則有著自己堅定信仰的文明;看似文明的日本殖民者,實則掩藏著不易暴露的野蠻。野蠻與文明的二元對立,不是進化的兩個階段,二者可以共存甚至可以在同一文化中共生。獵場里有廝殺和血腥,學(xué)校里有知識和文化,作為兩種不同形式的載體,它們有各自傾向的一面。但是,獵場里也有文明,賽德克族的文明是對勇敢的追求,是對“血祭祖靈”唯一不變的堅持。學(xué)校里則暗藏著統(tǒng)治他者思想的預(yù)謀,是包藏著野心的地方。
二、彩虹與太陽:自我與他者的糾纏
每一個賽德克族人都在追尋賽德克·巴萊,真正勇敢的人才能通過彩虹橋,到達另一端的獵場。彩虹在賽德克族人的心里,是世俗通往神圣的橋梁,是尋找祖先的路途。電影中多次出現(xiàn)了彩虹的意象,彩虹即代表者賽德克族對自我的認(rèn)識,彩虹就是他們的身份標(biāo)識。彩虹是與自然相連接的,代表著原始和人的自然天性,而作為日本殖民者的代表的太陽,則是征服和文明的代表。原本是界限分明的兩種信仰,卻在臺灣島這片土地上發(fā)生了交織,從而引發(fā)了信仰的錯亂和身份認(rèn)同的模糊。
作為道澤群屯巴拉社的頭目鐵木瓦力斯,在小時候受到了莫那·魯?shù)赖耐{:“我不會讓你長大的”。這在鐵木瓦力斯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一道陰影。后莫那·魯?shù)缆?lián)合眾部落發(fā)動對日本殖民者的反抗,鐵木瓦力斯知道家園的獵場和親人都被統(tǒng)治著,失去了原來的自由,但他在小島的友善誘騙下,竟然聯(lián)合日本殖民者一同對抗鎮(zhèn)壓莫那·魯?shù)腊l(fā)起的反抗。小島一直以朋友的方式和態(tài)度與鐵木瓦力斯相處,這讓鐵木·瓦力斯以為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朋友,這種朋友關(guān)系勝過同族的關(guān)系,而小島也利用了鐵木瓦力斯自小在心里的陰影,使得兩個部落互相殘殺,而這正是日本殖民者最樂意看到的結(jié)局。鐵木瓦力斯的內(nèi)心是糾纏的,他深知自己失去了獵場和家園,也知道應(yīng)該“血祭祖靈”,但在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下,在日本殖民者友善的外表下,他選擇了將矛頭對象曾經(jīng)生活在同一土地的族人。
然而,在彩虹和太陽兩種信仰交織的文化中,鐵木瓦力斯的身份認(rèn)同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本是賽德克人。他們身上流淌著賽德克族人的血液,但是他們卻從心里認(rèn)同日本的文化和文明。他們身份和處境的尷尬是最具代表性的。當(dāng)了日本警察的一郎和二郎游離于本族人與日本人之間,身份的曖昧注定被兩個圈子所排斥而處境尷尬。一方面本族人嘲弄他們有一身“日本警察的皮毛”,而不把他們視為同類;另一方面,哪怕他們接受了日本文化,與各自妻子的名字、服飾完全日化,仍要面對日本人的質(zhì)疑:兩個番人難道也能生出一個日本孩子?當(dāng)花岡一郎得知莫那·魯?shù)酪?lián)合各個部落大規(guī)模的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他想阻止這一切的發(fā)生,他認(rèn)可日本的文明,認(rèn)可當(dāng)下的有秩序的生活狀態(tài),但當(dāng)莫那·魯?shù)婪磫査裁词俏拿鲿r,反問他最終是想進祖靈的獵場還是日本神社時,花岡一郎猶豫了。賽德克族的血液在他身上流淌,“血祭祖靈”的信仰是他從出生就帶著的一個根,然而日本的殖民文化卻在不斷的松動著他原來的根。
自我與他者的糾纏最激烈的一幕在花岡一郎幫族人取得槍支后,并沒有參與戰(zhàn)斗。他身著賽德克族的衣服,手持番刀,他的妻子也是賽德克人,她身穿和服,與花岡一郎達成一致。花岡一郎番刀一揮,將自己的妻子殺死,然后他又捂死了自己還在襁褓中的孩子。最后,花岡一郎選擇了極具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破腹自殺。就如他的弟弟花岡二郎所說:“切開吧,一刀切開你矛盾的肝腸吧……哪兒也別去了,當(dāng)個自在的游魂吧。”在這,彩虹信仰與太陽信仰的交鋒達到了頂點,自我與他者的矛盾突出至極。兩種文化就如兩股勢力在花岡一郎的心里交織斗爭,身份認(rèn)可的錯亂導(dǎo)致花岡一郎在自我與他者中不斷地游離。
身份的認(rèn)同并不總是非此即彼,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也并非絕對。在花岡一郎的身上,自我與他者即對立又共存,自我有時即是他者,他者有時亦是自我。
整部影片《賽德克·巴萊》無處不顯示著二元對立的文化和文化的載體。作為人類學(xué)中非常最重要的結(jié)構(gòu)主義,正與此不謀而合。這種二元對立的結(jié)構(gòu)既有以極端對立的形式出現(xiàn),也有以溫和可容的形式出現(xiàn)。番刀與槍炮、獵場與學(xué)校、彩虹與太陽,這些都是二元對立也是二元對立的文化的載體。它們可以被理解為時間縱向發(fā)展出現(xiàn)的載體,也可被視為同一時代橫向的不同類別。
參考文獻:
[1][法]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張祖建譯.結(jié)構(gòu)人類學(xu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6.01.
[2][美]賈雷德·戴蒙德,謝延光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M].上海: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2014.03.
[3]雷攀.太陽與彩虹的信仰之戰(zhàn):《賽德克·巴萊》電影敘事學(xué)解讀[J].中國電影評論,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