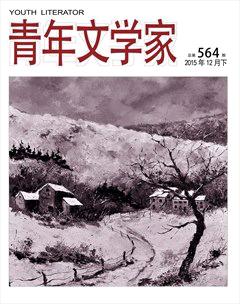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使者》在中國(guó)的翻譯與傳播
摘 要:《行人》是夏目漱石于1912年12月6日至次年11月5日發(fā)表在東京·大阪《朝日新聞》上的報(bào)紙連載小說(shuō),在他十年寫(xiě)作生涯中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行人》是夏目晚期三部曲中的一部,這是一部標(biāo)志著夏目漱石思想走向成熟的作品。《行人》到1985年在中國(guó)有了第一部譯本《使者》,此書(shū)雖較早的傳播到中國(guó),但大眾傳播的影響并不大,就連寫(xiě)關(guān)于夏目漱石的《使者》論文以及文章的也屈指可數(shù),這種現(xiàn)象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分析《使者》在中國(guó)接受及影響等傳播的情況,可以使我們?cè)鰪?qiáng)對(duì)外國(guó)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了解,促進(jìn)與世界各國(guó)的文化交流,從而使之化為有益于我國(guó)的教育啟示和營(yíng)養(yǎng)。
關(guān)鍵詞:使者;夏目漱石;文化交流;大眾傳播
作者簡(jiǎn)介:閆倩(1992.2-),女,籍貫山東青島,天津師范大學(xué)2014級(jí)碩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
[中圖分類(lèi)號(hào)]:H05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5)-36--02
夏目漱石的《使者》(日文名《行人》,1912-1913 年連載于《朝日新聞》,單行本出版于 1914 年),從相關(guān)文獻(xiàn)提供的信息得知,譯本于近 30 年后重印,于1985年在中國(guó)有了第一本翻譯《行人》的作品。
《使者》被編選在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小說(shuō)選下》中,由張正立根據(jù)日本筑摩書(shū)房《夏目漱石全集》1979年初版第十次印刷本等書(shū)翻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夏目漱石小說(shuō)選上下》兩本,篇幅達(dá)一百多萬(wàn)字,是繼50年代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的《夏目漱石小說(shuō)選》規(guī)模最大的漱石作品的中文譯本,在我國(guó)翻譯史上值得重視的成果。
之后出版的《使者》是大陸2013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收錄的譯本是根據(jù)新潮社《日本文學(xué)全集5夏目漱石(一)1968年5月版譯出。
目前,《使者》在中國(guó)大陸僅有張正立對(duì)此書(shū)加以翻譯出版。國(guó)內(nèi)學(xué)者中,較早研究和引用《使者》的是北京師范大學(xué)著名中文系教授何乃英在1989年發(fā)表的一篇《展示內(nèi)心沖突批判利己主義--評(píng)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的思想傾向》論文。隨后零零散散學(xué)者發(fā)表關(guān)于《行人》的學(xué)術(shù)文章。然而夏目漱石的很多作品在中國(guó)的影響很大,許多著名學(xué)者紛紛翻譯、研究他的作品。如《我是貓》在中國(guó)的流傳就很廣,僅譯本就多達(dá)30多種。但為何《行人》這部作品就無(wú)人問(wèn)津呢?這與夏目此部作品的翻譯情況有很大關(guān)系,翻譯版本的單一性為了解漱石的此部作品增添障礙。僅對(duì)《使者》題目的翻譯就意見(jiàn)不一:夏目漱石取“行人”兩個(gè)漢字作為書(shū)名是有出典的。它取自我國(guó)的《列子》,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dú)w,失家者也。”在夏目漱石看來(lái),小說(shuō)主人公一郎是“失家”的“行人”,被譯者用《使者》代替,王向遠(yuǎn)等日本學(xué)者覺(jué)得有些不妥。
而在另一些人看來(lái),這部作品的題目若按日語(yǔ)「ゆきひと」字面意思的話翻譯成“行人”的確沒(méi)錯(cuò),但為了能讓讀者更好地理解這部作品的視角和主角的身份翻譯成“使者”反而認(rèn)為更加妥當(dāng)。 二郎“我”這個(gè)身份絕不是什么旁觀者,而是推動(dòng)一郎精神走向的重要人物,文中的“我”就是使者。對(duì)于這種說(shuō)法,筆者認(rèn)為顯然不怎么準(zhǔn)確的,因?yàn)楦鶕?jù)漱石門(mén)下“四天王”之一,德文學(xué)者、文藝評(píng)論家,巖波書(shū)店版《夏目漱石全集》的主編小宮豐隆對(duì)《行人》的解說(shuō)以及日本《國(guó)語(yǔ)大辭典》的解釋?zhuān)恢卑选靶腥恕弊x作「こうじん」、而不是「ぎょうにん」或者「ゆきひと」。在《國(guó)語(yǔ)大辭典》中,「こうじん」的解釋有三個(gè):1、道を行く人。また、旅をしている人。2、 使者。3、 賓客の接待をつかさどる官の中國(guó)風(fēng)の呼び名。4、 出征兵士。筆者認(rèn)為,《行人》題目的翻譯應(yīng)該取國(guó)語(yǔ)大辭典的第一個(gè)解釋?zhuān)虼酥弊g“行人”為好,而“使者”已經(jīng)主觀局限了作者原意(雖然這原意已無(wú)從知曉),理解未免有些牽強(qiáng),當(dāng)然,還希望有更多的有識(shí)之士多提寶貴意見(jiàn)。
下面針對(duì)《使者》的內(nèi)容,試分析一下張正立在湖南人民出版的譯本《使者》中的翻譯風(fēng)格和特點(diǎn)。
原文:
大阪へ下りるとすぐ彼を訪うたのには理由があった。自分はここへ來(lái)る一週間前ある友達(dá)と約束をして、いまから十日以?xún)?nèi)に阪地で落ち合おうそうして一緒に高野登りをやろう、もし時(shí)日が許すなら、伊勢(shì)から名古屋へまわろう、と取り決めた時(shí)、どっちも指定すべき場(chǎng)所をもたないので、自分はつい岡田の氏名と住所を自分の友達(dá)に告げたのである。
「じゃ大阪へ著き次第、そこへ電話をかければ君のいるかいないかは、すぐ分かるんだね」と友達(dá)は別れる時(shí)念を押した。岡田が電話を持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そこは自分にもはなはだ危しかったので、もし電話がなかったら、電信でも、郵便でもいいから、すぐ出してくれるように頼んでおいた。友達(dá)は甲州線で諏訪(すわ)までいって、それから引き返して木曽を通った後、大阪へ出る計(jì)畫(huà)であった。自分は東海道を一息に東京まで來(lái)て、そこで四五日用足(ようとし)かたがた逗留してから同じ大阪の地を踏む考えであった。
張正立譯文:
在大阪下車(chē)后馬上拜訪岡田是有原因的,我到這里一周前已和一位朋友約好十天內(nèi)在大阪碰頭,然后一起登高野山,如果時(shí)間允許,就從伊勢(shì)轉(zhuǎn)到名古屋。當(dāng)時(shí)我們誰(shuí)也沒(méi)有在指定地方見(jiàn)面,我就把岡田的名字及住址告訴了我的朋友。
“到大阪后,我往那里打個(gè)電話,馬上就知道你在不在了。”朋友同我分手時(shí)囑咐說(shuō)。岡田有沒(méi)有電話,我也確實(shí)沒(méi)把握,便要求朋友:若是那里沒(méi)有電話,馬上給我來(lái)個(gè)電報(bào)或書(shū)信。我的朋友計(jì)劃先到甲州線的諏訪,然后折回,經(jīng)由木曾到大阪。我想從東海道一口氣到京都,在那里逗留四五天,辦完事以后再到大阪。
在這段譯文中,張正立的翻譯簡(jiǎn)潔流暢,以忠實(shí)原文的直譯傳達(dá)出原文的內(nèi)容,可以看出他扎實(shí)的工筆。但對(duì)有些對(duì)原文的翻譯也較為粗略,存在有關(guān)副詞及連詞的漏譯問(wèn)題,如「すぐ車(chē)を雇って岡田の家に駆けさせた。」「自分はつい岡田の氏名と住所を自分の友達(dá)に告げたのである。」等處。其中,「すぐ」應(yīng)譯作“徑直”較為恰當(dāng),根據(jù)上下文的聯(lián)系,這里的意思是沒(méi)有去別的地方,直接去了岡田家,因?yàn)橄挛挠刑岬侥赣H托我給岡田帶了禮物,母親希望能趕快送到。由此,筆者認(rèn)為此處對(duì)「すぐ」一詞的省略不太恰當(dāng)。「つい」譯作最終,因上文說(shuō)我和朋友一直沒(méi)有商量好地方,最終才做了這個(gè)決定,筆者認(rèn)為此處沒(méi)有譯出「つい」一詞的意思,譯作在原文的語(yǔ)氣就顯得有些輕描淡寫(xiě)。
再者,有些翻譯有和原文出入的地方,如「取り決めた時(shí)、どっちも指定すべき場(chǎng)所をもたない。」雖然「どっちも」也可以指人,但后面「場(chǎng)所をもたない」是沒(méi)有場(chǎng)所、地點(diǎn)的意思,此處筆者認(rèn)為譯為“由于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決定好地點(diǎn)”較為合適。此處譯者譯為“當(dāng)時(shí)我們誰(shuí)也沒(méi)有在指定地方見(jiàn)面”對(duì)比原文實(shí)屬不妥。
除出版翻譯書(shū)籍這種傳播路徑外,當(dāng)下互聯(lián)網(wǎng)已漸漸成為人們學(xué)習(xí)和進(jìn)行學(xué)術(shù)交流的有效資源。其中在微博中提起夏目漱石《使者》這本書(shū)的博友,大多以心靈雞湯的形式被大家轉(zhuǎn)載分享出來(lái)。可以看出漱石的思想在中國(guó)有借鑒意義,能夠與中國(guó)人的生活及思想產(chǎn)生共鳴,這種共鳴是作為人的一種自我反省和對(duì)生活的感悟。另外在百度貼吧中有關(guān)夏目漱石帖子就多達(dá)7988個(gè),其中關(guān)于《使者》的帖子有十多余條,這為我們搜集資料提供了很多方便。
總之,《使者》在中國(guó)的傳播有多種多樣的途徑。學(xué)術(shù)傳播之路雖稍有改善,但總體來(lái)看一直停滯不前,而網(wǎng)絡(luò)傳播作為一種新興力量更推進(jìn)了夏目漱石這部作品在中國(guó)的影響,這啟示我們?cè)谖膶W(xué)經(jīng)典的傳播之路上要重視網(wǎng)絡(luò)傳播的作用,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也要以中國(guó)的文化環(huán)境為基礎(chǔ),不能照搬外來(lái)的東西,做到本土化的成功轉(zhuǎn)換。
參考文獻(xiàn):
[1]何乃英,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說(shuō)[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2]夏目漱石著,張正立等譯,夏目漱石小說(shuō)選(下)[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1985.
[3]王成,夏目漱石文學(xué)在中國(guó)的翻譯與影響[J].翻譯論壇,2001(1).
[4]王向遠(yuǎn),八十多年來(lái)中國(guó)對(duì)夏目漱石的翻譯、評(píng)論和研究[J].日語(yǔ)學(xué)習(xí)與研究,2001(4).
[5]李玉雙,試析夏目漱石文學(xué)中的宗教情結(jié)[J].魯東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