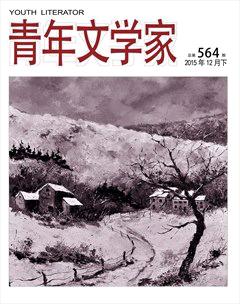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熱鬧”夢(mèng)境與“野性”思維
基金項(xiàng)目:該文為2014年江蘇省高校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基金項(xiàng)目“民俗文化視野下南通童子戲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4SD649)階段性成果。
摘 要:南通童子戲作為一種民間文藝形式,它的蓬勃生命力在于其滿足了百姓的民俗心理需求。通過對(duì)童子戲唱本《十三部半巫書》“熱鬧紛呈”的夢(mèng)境分析,探討童子戲運(yùn)用夢(mèng)戲迎合百姓的原始“野性”心理,解剖民間百姓的獵奇、迷信及習(xí)俗心理需求在童子戲中的體現(xiàn)。
關(guān)鍵詞:童子戲;夢(mèng)境;民俗
作者簡介:陳云(1979-),女,江蘇南通人,江蘇南通科技職業(yè)學(xué)院講師,文學(xué)碩士,從事民俗文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hào)]:C95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5)-36--02
南通童子戲,亦稱僮子戲或通劇,是現(xiàn)在世界上僅存兩種的原始祭祀戲劇之一,起源于“以舞降神”的巫覡演唱,流行于南通地區(qū),包括市區(qū)(崇川區(qū)、港閘區(qū)、開發(fā)區(qū)、通州區(qū))、轄縣(海安、如東縣)、縣級(jí)市如皋市,是一種地方性小戲種,因其最初的表演者是被稱為“童子”的南通巫師而得名。
作為傳統(tǒng)戲劇,童子戲于2007年列入江蘇省第一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國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此后童子戲受到更多的關(guān)注,學(xué)者和愛好者們也對(duì)童子戲展開了深入研究。但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童子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發(fā)展、儺祭儀式、唱腔音樂等方面,從文本角度進(jìn)行研究尚待開發(fā)。童子戲的文本,歷來依靠同門師承、口傳心授,即使有傳世者,也多為手抄本。1995年,南通市民間文學(xué)集成辦公室和南通市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huì),組織出版了由童子藝人楊問春、施漢如收集整理的童子戲文本《十三部半巫書》,最大程度地保存了童子說唱的內(nèi)容,為童子戲研究做出了貢獻(xiàn)。
一
《十三部半巫書》,俗稱童子書,是童子說唱神仙事跡、宣教勸化的書目,主要有《鬧荒》(半部)、《袁樵擺渡》、《賣卦斬龍》、《陳子春》、《唐僧取經(jīng)》、《劉全進(jìn)瓜》、《收瘟斬岳》、《九郎替父》、《九郎借馬鬧東海》、《九郎借鞍》、《九郎借鞭》、《請(qǐng)星迷路》、《陽元請(qǐng)神》、《五郎游地府》。其中寫夢(mèng)11處,推演了劇情的發(fā)展。夢(mèng)境可謂“熱鬧”紛呈。
(一)夢(mèng)引作戲,以夢(mèng)“入”戲
運(yùn)用夢(mèng)的手法來推進(jìn)戲的故事發(fā)展,將夢(mèng)境引入戲,只是借助夢(mèng)境的植入來實(shí)現(xiàn)靈魂的出游、來交代前塵往事或?yàn)楣适碌陌l(fā)展指明方向。
前半部《鬧荒》中“唐王天子龍床睡,真魂出竅登天門,五爪金龍?jiān)苼眈{,月宮早到面前存”①,唐太宗李世民夢(mèng)游月宮,“唐王站在蟾宮里,癡心妄想看佳人”②,調(diào)戲仙女,天譴災(zāi)禍,“只因唐王游月宮,調(diào)戲仙女惹禍根”③,旱災(zāi)連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通過這個(gè)夢(mèng)境,引入后面的故事,是整部戲劇情節(jié)的重要推手,也對(duì)塑造唐王的人物形象及主體表達(dá)起到很大的作用。
《唐僧取經(jīng)》中,觀音托夢(mèng)小僧人,“取得真經(jīng)回東土,將功折罪轉(zhuǎn)天門”,領(lǐng)旨前往西天取經(jīng),借助于夢(mèng),銜接劇情,故事順理成章地發(fā)展下去。
戲中的夢(mèng)境都是清楚明白的,并不如生理學(xué)意義上的夢(mèng)那般跳躍、混沌、無邏輯性和不連貫,只是借用了夢(mèng)的外殼裝入了想要表達(dá)的內(nèi)容。夢(mèng)境貫穿整部戲劇的始終,夢(mèng)在情節(jié)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夢(mèng)乃魂行,以夢(mèng)“演”戲
在古人看來,“夢(mèng)”并非是虛妄的片段而是一種真實(shí)的知覺,是靈魂活動(dòng)的一種方式。《賣卦斬龍》中,唐王接受了老龍的賄賂,與魏征下棋,不讓魏征前去斬龍王,“早晨下了茶時(shí)候,茶時(shí)下了午辰光,巧巧下了午時(shí)正,……魏征表面在下棋,魂飛魄散無主張,……魏征低頭拾棋子,乘勢(shì)伏案進(jìn)夢(mèng)鄉(xiāng),……魏征雖然沒有醒,誰想魂魄走外邦”,魏征在夢(mèng)中魂魄急赴龍宮,劍斬龍王,其身體猶在唐王身邊,從而也引發(fā)后面的龍王狀告唐王的劇情。
(三)夢(mèng)顯征兆,以夢(mèng)“預(yù)”戲
早在商周時(shí)代就有了關(guān)于夢(mèng)卜的記載,夢(mèng)在民俗中一直存有某種預(yù)兆,昭示吉兇和未來的走向。《陳子春》中,“夢(mèng)見衙門東山倒,斷了中間梁一根,又見一對(duì)鴛鴦鳥,留雌去雄好孤凄,老鼠跳在油瓶內(nèi),又有花貓把住瓶,若有老鼠有性命,抓住花貓打破瓶。奴家又夢(mèng)牙齒落”,夢(mèng)預(yù)示后面陳子春將遇強(qiáng)盜劉洪,妻離己喪,官位被竊,推動(dòng)劇情的跌宕起伏。
二
百姓生活是童子戲創(chuàng)作的豐富源泉,在《十三部半巫書》中處處皆是各種物質(zhì)的、心意的、行為的民俗生活事項(xiàng),傳遞出南通地區(qū)的民俗傳統(tǒng),彌漫著本地域的鄉(xiāng)土民情。童子戲是百姓的舞臺(tái),走向鄉(xiāng)村,走進(jìn)生活,把貼近百姓的心理作為戲劇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diǎn),處處或隱或顯地受到百姓“野性思維”的影響。
“野性思維”最早由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明確提出,他認(rèn)為思維方式可分為“野性的”和“文明的”兩大類,無高低之分,無好壞的價(jià)值之分。野性思維,屬于未開發(fā)的、未馴化的原始思維,蘊(yùn)藏于人的生活,關(guān)涉人的生活,無需習(xí)得或訓(xùn)練,以最淳樸的原始形式存在,是人的固有天性,受自由的意識(shí)活動(dòng)支配。古人謂“夢(mèng)者,象也”,就是說“夢(mèng)者,想象也”,夢(mèng)的活動(dòng)及其變化過程,都是由人的意識(shí)想象構(gòu)成,同人類的原始思維即野性思維極其相似,因?yàn)樵妓季S與夢(mèng)象活動(dòng)一樣,不受邏輯規(guī)律的支配,都是以意象拼接推移變化,都以意象活動(dòng)表達(dá)意念和思想。佛洛伊德指出,夢(mèng)采用一種原始的表現(xiàn)方法,把隱意變成顯象。夢(mèng)的活動(dòng)采用時(shí)空知覺的濃縮、無隔、跳躍等特征表達(dá),與人的野性思維表達(dá)是一致的。
《十三部半巫書》中的夢(mèng)境荒誕迷離、莫可名狀,把一切外在的感覺經(jīng)驗(yàn)化為內(nèi)在心理事件,“在夢(mèng)中收拾一場(chǎng)怪誕”,心游萬里,思維跳躍,發(fā)乎想象,用形象表達(dá)思想,這無疑受到一種野性狀態(tài)的思維方式進(jìn)行的潛在支配。童子戲,作為地方戲種,劇作者及觀眾基本來自于農(nóng)村,文化程度較低,較多原始思維,夢(mèng)的表現(xiàn)形式符合他們的創(chuàng)作思維,也獲得百姓觀眾的認(rèn)同和歡迎。
童子戲的創(chuàng)作者和接受者來自于一個(gè)群體,他們的文化背景相似,思維方式相似,創(chuàng)作者了解接受者的心理需求,寫對(duì)方所想,演對(duì)方所思,深入觀眾的內(nèi)心,才使得童子戲這個(gè)地方劇種在南通地區(qū)得以繁衍發(fā)展。
三
在原始的“野性思維”的支配下,童子戲用夢(mèng)來說戲,用夢(mèng)來演戲,充分顯現(xiàn)百姓最原始的本真心理,充滿鄉(xiāng)土淳樸的民俗心理需求在童子戲中得以體現(xiàn),童子們的表演迎著鄉(xiāng)村百姓的呼喚,使百姓獲得最淳樸的精神滿足。
雖然在中國古代并沒有科學(xué)的心理學(xué)分析方法,但在民間,人們很早就形成了將夢(mèng)與人的心理相勾連的思維范式。明代莊元臣《叔苴于》載:“思淫夢(mèng)感,思?xì)w夢(mèng)家,思榮夢(mèng)貴,思財(cái)夢(mèng)獲,思食夢(mèng)嘗,此心能造夢(mèng)之驗(yàn)也。”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mèng)”,心理與夢(mèng)境緊密相連,童子戲順應(yīng)這種民俗心理,將民間“心中所想”在“夢(mèng)中相尋”的夢(mèng)境表現(xiàn)出來。
(一)夢(mèng)境的傳奇色彩滿足觀眾的獵奇心理
童子戲與巫術(shù)有密切關(guān)系,屬于儺戲,既要娛神,也要娛人,是一種貼近普通百姓的民間戲曲,娛樂功能是童子戲獲得觀眾喜愛的重要原因。童子戲重視戲劇的濃厚傳奇色彩,從表演形式到內(nèi)容都充滿迷離奇幻。在數(shù)千名的夢(mèng)文化影響下,普通老百姓對(duì)夢(mèng)境有一種特殊情結(jié),他們認(rèn)為在夢(mèng)境中,可以擁有超乎自然的能力,可以忽而天上,忽而人間,又忽而地府,這些在平常生活中不可能出現(xiàn)、也難以置信的情節(jié),在夢(mèng)中都可以出現(xiàn)。
這種夢(mèng)幻的、離奇的情節(jié),使情節(jié)離奇曲折,扣人心弦,也滿足了觀眾的獵奇心理,最終達(dá)到娛人的目的。獵奇心理,屬于人的原始野性心理,對(duì)自己不知曉、不熟悉或比較奇異事物表現(xiàn)出好奇感。民眾的獵奇心理,比較普遍,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心理,本質(zhì)上也是一種獵奇心理。童子戲的夢(mèng)境,為觀眾所陌生未見,在鄉(xiāng)風(fēng)淳樸的南通農(nóng)村,他們對(duì)上天入地的神幻夢(mèng)境充滿了好奇。
如《鬧荒》中唐王做春夢(mèng),夢(mèng)入仙境“蟾宮景致勝凡塵”,仙女“眉如初月眼似星,秋波回掃攝人魂”,描繪出最美事物的想象,符合百姓對(duì)絕佳仙境的心里憧憬,也透射出百姓對(duì)絕色仙女的性別向往。再如《賣卦斬龍》中魏征打瞌睡,夢(mèng)游斬龍,沒有帶刀和劍,拔根端午節(jié)的菖蒲當(dāng)寶劍,駕起云霧趕赴龍宮,舉劍斬龍,這種逆轉(zhuǎn)性的夢(mèng)境讓劇情跌宕,為百姓所喜聞樂見。這些傳奇色彩濃郁的夢(mèng)境,極大滿足了觀眾的好奇之心,使得童子戲成為南通百姓向往的“流行音樂”,是他們農(nóng)暇時(shí)的精神享受。
(二)夢(mèng)境的鬼魂神靈迎合觀眾的迷信心理
鬼神觀念在上古初民的意識(shí)中就已經(jīng)萌生,人體內(nèi)有一種可以脫離肉體而存在的異質(zhì),稱之為靈魂。靈魂出竅,可以遨游人間之外的天界與地府,天地人三界,三界內(nèi)存有鬼神。童子戲請(qǐng)三界之神,為百姓消災(zāi)祈福、驅(qū)鬼治病,為鄉(xiāng)民“做會(huì)”,如“消災(zāi)會(huì)”、“催生會(huì)”、“青苗會(huì)”、“豬欄會(huì)”、“牛欄會(huì)”、“羊欄會(huì)”、“換土?xí)钡取?/p>
在淳樸未開化的“野蠻”狀態(tài)下,鄉(xiāng)民們?cè)谔鞛?zāi)人禍面前無能為力,對(duì)生命個(gè)體或群體有支配力量的鬼魂神靈充滿畏懼和信崇,求神拜佛,祈求得以護(hù)佑。童子是神與人的溝通者,童子戲是充滿迷信色彩的巫戲,以唐王還愿為目的,請(qǐng)神跑三界,是百姓迷信心理的徹底展現(xiàn),既娛樂了百姓,也迎合了百姓,讓百姓更為堅(jiān)信鬼神的存在,因此童子戲中呈現(xiàn)靈魂出游、神靈托夢(mèng)等熱鬧夢(mèng)境,現(xiàn)實(shí)即夢(mèng),夢(mèng)即現(xiàn)實(shí),渾然入迷。
如《魏九郎替父請(qǐng)神》、《唐僧取經(jīng)》中,觀音菩薩騰云駕霧,托夢(mèng)皇娘,托夢(mèng)江流小和尚,皆因當(dāng)初“唐王魂魄游地府,奈何橋上許三愿”,《十三部半巫書》處處可見鬼魂神靈的身影,各方神圣輪流登場(chǎng),彌漫著濃郁的迷信色彩。這種迷信觀念沉淀在民俗心理結(jié)構(gòu)中,成為民俗心理中比較穩(wěn)定且具有傳承性的部分,在老百姓的思想中深層埋烙。
(三)夢(mèng)境的占卜方式順應(yīng)觀眾的習(xí)俗心理
從古至今,在我國民間流傳著諸多關(guān)于夢(mèng)的民俗,如占?jí)簟⑵韷?mèng)、圓夢(mèng)、解夢(mèng)等。占?jí)艋顒?dòng)與日常生活相聯(lián)系,滲透于日常事象中,成為人們生活體驗(yàn)的一部分。占?jí)艟哂幸环N特殊的神秘感。
這種對(duì)夢(mèng)的功能性認(rèn)識(shí),積淀為民俗心理中一個(gè)相對(duì)穩(wěn)定的部分。占?jí)袅?xí)俗就是這種普泛性的民俗心理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射,成為一種習(xí)俗心理定勢(shì)。童子戲作為最接地氣的藝術(shù),“寫夢(mèng)”既反映民俗生活,也符合民俗心理,以夢(mèng)入戲,占?jí)艚鈮?mèng),這是民眾的原始思維在戲劇中的表現(xiàn),順應(yīng)民俗需要。
如《陳子春—唐僧出世》中,殷鳳英“夢(mèng)見衙門東山倒,斷了中間梁一根,又見一對(duì)鴛鴦鳥,留雌去雄兩離分,一只雄鳥遭槍打,留下雄來好孤凄……奴家有夢(mèng)牙齒落,骨肉夫妻兩離分”,通過占?jí)簦嬖V陳子春在船上有可能出現(xiàn)的兇兆,但是陳子春未聽信于夢(mèng),結(jié)果被強(qiáng)人劉洪搶妻劫官,自己命喪大海。再如小江流,夢(mèng)見“袈裟破了無人補(bǔ),破了僧鞋無人縫”,催促他踏上尋母之路。夢(mèng)境,或喜,或愁,或憂,將夢(mèng)境的虛幻帶入現(xiàn)實(shí)生活,影響心理走向。占?jí)羟榻Y(jié),在民俗中非常普遍,從古到今,一直影響著現(xiàn)代人的生活和思維。童子戲以這種人們樂見的占?jí)粜问剑瑢∏樽匀煌七M(jìn),貼近民俗心理需求。
戲劇傳播的過程很大程度上也是民俗傳播的過程。戲劇并非廟堂藝術(shù),其誕生之始就和民間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民間習(xí)俗以及民間心理自然而然影響戲劇創(chuàng)作與表演。童子戲的文本在傳承過程中由民間藝人的搬演,面向民間大眾進(jìn)行演出,所表演的也是民間大眾喜聞樂見的內(nèi)容,這些表演是順應(yīng)民俗心理的,這樣才會(huì)在民間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xiàn):
[1]季歇生,十三部半巫書,南通市民間文學(xué)資料選,1995(3).
[2]韓玉芬,吳新化,高職文秘專業(yè)校企合作人才培養(yǎng)模式研究,湖州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J].2010(03):51-54.
[3]曹高菲,高職院校文秘專業(yè)實(shí)踐教學(xué)模式的改革與構(gòu)建,哈爾濱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J].201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