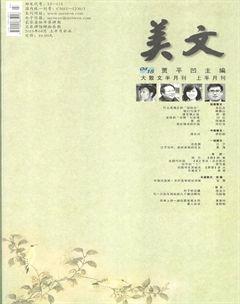江子寫作:前所未有的還鄉
黃海
江子的散文寫作是這樣的——
比如恢弘的歷史人物和個人史一樣,是碎碎的。比如歷史上的某人,像個異類,獨行客、浪人和最后的過客,對江子來說,寫作是要努力把英雄回塑到人的過程。
比如他的日常,都是片段的,漫游者,在異地,經歷和遭遇,他把自己當一個人來完成。
比如他寫到那些鄉村消失的事物,照相館、理發店、鄉村診所,那些人,有名字和沒名字的人,他用兩個詞比方:陰影或暗疾,物有陰影人有暗疾。他說:“做一個健康的人。”我的理解是他祈愿與他們溫暖、 共濟和平等。
可是當我們在遭遇享樂消費的時候,什么都有可能被消解,被個我,被流行,甚至可能被遺忘……不知恥的健忘令人類靈魂游蕩,沒有歸路。朝花弄月,夕照抱云,隨處的詩情畫意不過在詩中,被小清新。也許是我悲觀,禪心已眠,看此景生不出禪心。
山中畫一座寺廟,不如山路石級畫一僧。
畫中有物,卻不見人。情何以堪啊。
由此我想到江子寫的那些家國,我心頭驚顫,他寫的那本書叫《田園將蕪:后鄉村時代紀事》,書名足夠驚艷和高大,令我讀罷不能,但我不認為他是要完成一種現代人的鄉愁儀式,不是要給裸露的鄉村披上新衣,比如說賦予什么意義。他在解剖田園的構成——那些人同樣有欲望,有心魔,有陰暗,同樣有病痛,有沉重,有雜陳,當然還有美好、有善良、有人性。
但是為什么江子還要像魯迅先生那樣吶喊:救救鄉村?千百年來,鄉村被田園牧歌,被標簽化,要么貧窮,要么詩情畫意;要么故土難離,要么懷鄉不遇,總是那么讓人難以為情。是我們的鄉村有了疑難雜癥還是寫作者自身病入膏肓?
江子的鄉村為我提供了什么?我自以為他是為那片鄉土在陳情。他像拖拉機的橡膠輪胎在碾壓大地,工業化讓手工業者成為藝人。也許,對他來說還鄉的意義在于這片鄉村已經空空蕩蕩。他不是在目測,而是種親歷。
他對于鄉村的表達是具體到人,這些活著的他們(名字不詳)和死因不明的河清和玉生們,江子通過這些鄉村肖像完成了他對自己鄉土的情感,也還原了他們生機而陰暗的生活現場。這些只能在文字中見到的物和人,他們處境艱難,卻夢想依存;勞作不倦,卻田園正在荒蕪。傳統鄉土情懷與現代城市進程的交織,余下徘徊、困頓、矛盾、無望,而鄉村那景不再,生生不息的田園已成空余,這就是江子要表達的鄉村現實,不是一種,沒有選擇,這是鄉村的最后歸途,我們都不愿看到。
現實版隨所處可見——
君不見青山綠水,雞鳴狗叫的田家院落……
君不見漁舟唱晚,荷葉田田的水澤渡口……
這里正在淪陷,正在消失。鄉民逃離,土地污染,鄉村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我們準備好了嗎。我相信江子不是一個守舊者,懷舊也會加劇鄉土的陣痛,它解決不了當前鄉村遭遇的境況。當農業固有的秩序、環境、鄉俗迅速被打壞、被破壞時,誰都不能只做旁觀者,但我們也不做一個審判者。
江子用個人的自我審視、反思、警醒完成了一種懷鄉儀式,他想莊嚴,但面帶蒼涼;他想完美,但心存悲愴……這些早已遠離時代的詞,竟和個人的呼吸緊密聯系,我們能去掉這些沉重的心靈枷鎖嗎?
嗚鳴的火車聲與故鄉的炊煙,尖銳的汽車鳴笛與急促的犬吠,瀝青水泥路與小橋流水……他們并存,人在田園,鳥在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