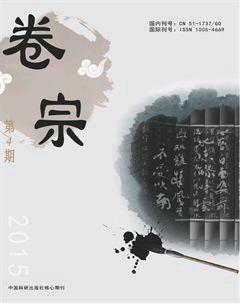淺談中國古代圖書館的發展及概況
宋松
摘 要:本文從圖書和文獻的起源及關系談起,以具有代表性的朝代為脈絡,對我國古代圖書館的產生和發展做一淺略地概述。
關鍵詞:古代;官藏
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其優秀的文化歷史傳承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圖書和圖書館的產生和發展是呈現中國文化進程最直觀的且極具說服力的一個部分。本文試就古代圖書館的發展概況略作說明。
1 圖書是文獻的基礎,文獻是圖書的匯總
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總是離不開語言和思想的交流,人們常用自己的口頭語言為主,配以各種不同的表情、動作、或舞之、蹈之,來傳遞心中所想表達的意圖。語言的這種形式雖然直接,但也有其局限性,這種口口相傳、口耳相傳的方式經常會把正確信息和意圖誤傳、漏傳,以至于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誤會和麻煩,加之我國自古民族眾多、語言地域性強,方言的使用也各有特色,使得語言的局限性進一步凸顯出來,人們不得不采取其他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于是,文字產生了。我國最早文字的雛形應為象形字、甲骨文,此時只是一些簡單的符號標記。文字的產生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載體,通過這個載體不斷地把文字、符號、、思想、語言等人類各種言行記錄貯藏起來,保存了知識、記錄了文明,從而推動了歷史進程,這個載體,就是文獻。“文獻“一詞最早包涵兩層意思,即“文賢”,也就是圖書和博學之人的意思。到元代時,“文獻”成為泛指古代傳記、經史、奏疏、評論等文字典藏的總稱。我們說,圖書是文獻的基礎,也是一種特殊的文獻。它具有保存、交流、傳播、擴散的功能,我國古代的圖書基本上以棉帛、簡牘、紙張為主,這三種載體上記錄了人類各時期的生產生活形態和文明發展的成果。除此以外,我國古代文獻的載體還有甲骨、鐘鼎、玉石等。可見,文獻涵蓋的內容很寬泛,圖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個分支系統,是一個基礎。再由這個分支系統不斷地加以積累和衍生,形成一個大的文獻匯總體系,二者相輔相成。
2 古代圖書館的發展及概況
隨著大量圖書文獻的產生,迫切需要有專門的人來進一步管理、需要有專門的地點來放置和保存這些文化成果,于是歷朝歷代的藏書館、藏書閣應運而生。 我國現存的最古老的藏書樓叫天一閣,在今天的浙江省寧波市。始建于于清嘉靖四十年(1561年)。據記載,天一閣當時有藏書7萬多卷。藏書之地最防火災,而自古有“天一生水”的說法,水可以滅火,因此便將此藏書樓取名為天一閣。
天一閣收藏的圖書文獻中 ,很多在現在看來可稱為國之瑰寶、稀世珍品。其中有乾隆皇帝所賜的的銅版書《古今圖書集成》1萬卷,有明朝的地方志等。天一閣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天一閣收藏圖書近30萬卷,其中宋、元、清歷代的善本書8萬多卷,天一閣和這些史料的留存,為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外,我國古代的圖書館在兩漢、魏晉、隋唐時期都得到了良好的發展。比如,漢武帝在位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進行思想上的大一統, 于是盡收宇內藏書、編整圖書,以充實宮廷藏書和政府機構藏書,從思想、文化載體方面進行思想的桎梏,西漢的國家圖書由此而興。
到了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為了鞏固其統治,網羅了大量儒生,先后建立了如蘭臺、東觀、仁壽閣、宣明、鴻都等藏書場所,這些場所后來都成了東漢政府專門藏書之地。東漢以后,隨著政府藏書量的不斷增加,編著國史和校書事務的增多,急需要有專門的機構的和管理人員來從事歷史編纂及圖書典籍的管理工作,于是,藏書管理機構正式在朝廷建立起來,如蘭臺史令就是藏書機構的管理官員,校書郎承擔具體的書刊典籍的校對等工作。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藏書發展較快,很多作者為了讓自己的著作得以流傳,就將書主動送予官府收藏,有的則將所藏書籍直接請官府校對收藏,大大增加了書籍的貯藏量,提升了利用價值。
公元589年,楊堅統一了長期分裂的魏晉南北朝,建立了隋朝。這一時期比較突出的是佛道書籍受到重視,在隋朝官府對各類佛、道經書典籍進行了分門別類的整理,隋煬帝時還請了一位叫沙門智果的高僧在內道場撰諸經目,做現場指導。此外,隋官府還從全國各地召集調遣了大量書籍管理校對人員,對其它各類藏書進行了認真整理。據記載,隋朝中期時官府組織的大型書籍整理、官藏建設工作至少兩次,使得此時期的官藏書籍達近三萬卷,比開國時期增加了一倍,而且這些書籍在裝幀上也十分華麗壯觀,可謂是開創了封面設計藝術的先河,為以后的官府藏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唐朝,我國進入了社會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時期,此時期的藏書規模比隋朝大了許多,還設立了專門掌管文化的機構—秘書省,管理人員稱“秘書監”,我們熟知的魏征就擔任過這一職務。唐代最有名的幾處藏書地分別是弘文館、集賢殿書院、史館和崇文館,這些場所除發揮了了藏書這個重要功能外,很好地利用了這些藏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很多朝廷政務都常以藏書做為參考。2、以藏書為基礎編纂各類史書。3、用藏書做范本對“五經”及其他各類書籍進行注解、校對,為后世留下了珍貴的史料。
時至今日,在我國圖書館發展史上仍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最早的以“圖書館”命名的公共圖書館,它是江南巡撫無端方在南京創立的江南圖書館,此館共藏書約八百多冊,都按照一定序列及類別進行擺放,并制定出了一系列閱覽規章制度,每個月都設了開放閱覽日,當地的人們及軍學各界人士都可進館閱讀。除了江南圖書館,又陸續出現了比較著名的如京師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這些公共圖書館不僅藏書的種類豐富,其書籍的裝訂也采用了西式裝訂法。既有我們本國的書籍,還有許多外國傳教士翻譯的西方書籍,如我們熟知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翻譯的書籍就有二十多種,其中有心理學方面的書籍《西國記法》,指出了真正的記憶器官是‘“腦”,而非中國傳統認為的“心”。《萬國全圖》講述了世界各地的地理知識,《藥露記》是一本醫學方面的書籍,比較詳盡地介紹了西方藥物學方面的知識。還有如外國人金尼閣翻譯的第一部西方文學作品《伊索寓言》、艾儒略所譯的最早介紹西方大學課程及教育制度的《西學凡》等書籍。很多書籍的版式也發生了變化,改線裝為包背裝,即用較厚的皮棉或布面,印上金字或黑字,稱為“精裝”;用各種書皮紙包裝印制的封面,稱為“平裝”,這兩種裝訂方法我們現在依然在使用。這些新事物、新知識、新理念的出現大大增強了各種思想和文化的交流,開闊了國人的眼界,提高了國人的知識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質,打開了清朝緊閉的大門,推動了社會發展的進程。
以上所談僅是我國古代圖書館發展的一個粗略線條,在中國漫長的圖書館發展史中可謂“滄海一粟”。但不管怎樣,中國古代圖書館的興起和發展為后代圖書事業的繁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關更深入細致的探究工作還在等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