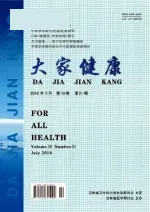自擬中藥香元助生湯在妊娠晚期促宮頸成熟的效果分析
陳 霞 張 靜
(1.山東省萊蕪市萊城區高莊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山東 萊蕪 271100;2.山東省萊蕪市萊城區楊莊鎮衛生院 山東 萊蕪 271100)
計劃分娩在產科領域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宮頸成熟情況是決定分娩的重要因素。目前臨床應用的促宮頸成熟方法有:靜脈點滴催產素、蓖麻油雞蛋餐、米索前列醇、水囊、米非司酮等。本研究探討了中藥香元助生湯促宮頸成熟的效果,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尋找妊娠晚期促宮頸成熟的新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收集我院2011年6月~2012年6月,因各種產科指征(羊水偏少、胎膜早破、延期妊娠、過期妊娠等)需引產的單胎頭位、無宮縮初產婦146例,年齡22~36歲,平均25.8歲;孕周為37~43周,平均38.76周;既往月經規律或早孕經B超推測預產期準確;無負荷實驗(NST)有反應型;宮頸評分(Bishop評分)<3分,免疫法檢查孕婦血E2(雌二醇)、P(孕酮)。分成治療組與對照組各73例。兩組在年齡、孕次、孕周、宮頸成熟度等方面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可比性良好。
1.2 方法
1.2.1 對照組:按催產素常規使用方法:5%葡萄糖液500 ml加入催產素2.5IU,以2.5 mIU/min開始,最多不超過12.5 ml U/min,根據宮縮情況調整滴速及濃度,每天最多用催產素7.5 IU,最多應用3天。
1.2.2 治療組:單用中藥香元助生湯(方劑:青木香12g,元胡12 g,月季花10g,七葉蓮12g,桃仁10g,香附12g,益母草15g,川牛膝10g,當歸15g,西紅花6g)。制備方法:將上述諸藥加水浸泡30 min后,煎煮l h,提取煎液。口服250 ml/次,2次/天,最多服3日。
1.3 觀察指標:所有引產孕婦用藥前均免疫法檢查血E2(雌二醇)、P(孕酮)值,行產科檢查、B超檢查及無負荷實驗(NST),用藥后行胎心監護,觀察記錄宮縮頻率及強度,末次用藥后12h再次行肛檢,免疫法檢查孕婦血E2(雌二醇)、P(孕酮)值變化情況。
1.4 效果:判定標準[1]顯效:指末次用藥后宮頸Bishop評分較用藥前增加3分或用藥期臨產;有效:指末次用藥后宮頸Bishop評分較用藥前增加l~2分;無效:指末次用藥后宮頸Bishop評分無變化者。
1.5 統計學方法:全部數據均經SPSS 8.0軟件處理,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等級資料采用Ridit檢驗。
2 結果
2.1 用藥后臨床療效情況:臨床總有效率為顯效和有效之和。經x2檢驗,兩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x2=13.95,P<0.05)。見表1。

表1 治療組與對照組用藥后臨床療效比較 [n(%)]
2.2 血雌二醇(E2)孕酮(P)變化各組用藥后E2(雌二醇)、P(孕酮)水平變化比較,經t檢驗有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2。

表2 血雌二醇(E2)、孕酮(P)變化比較
3 討論
催產素自50年代問世以來,一直是產科常規引產藥物,它的主要作用是促進子宮收縮,能選擇性興奮子宮平滑肌,增強子宮收縮力及收縮頻率;催產素應用時需靜脈給藥,專人看護,但可通過宮縮強弱調節劑量,并在必要時及時停止用藥,此方法受宮頸成熟程度的影響較大,促宮頸成熟作用不甚理想。中藥香元助生湯中應用元胡活血行氣止痛,青木香清熱解毒行氣,當歸補血;西紅花、桃仁活血,養血生新,月季花、七葉蓮活血祛瘀,通絡下胎,消腫止痛;川牛膝活血通經,性善下行;香附通行十二經之氣,氣行則血行;益母草增加子宮的收縮力。七味共同作用于胞胎,使其活血、行氣下胎之效更加滿意。宮頸組織學特點是以結締組織為主,其次為少量的平滑肌細胞,其中60%~80%為膠原纖維,其堅韌及軟化程度主要由膠原纖維的量和功能狀態決定[2],妊娠期的宮頸軟化分娩期的宮頸成熟,主要由于膠原纖維顯著疏松及分離、降解所致[3]。通過青木香、元胡、當歸、益母草、香附、紅花等組成具有活血行氣、養血和血、溫經通絡,進行促宮頸成熟的實驗研究,發現香元助生湯可影響宮頸膠原酶活性,加速宮頸膠原纖維斷裂、降解、重新排列[4],從而促宮頸成熟。(3)妊娠晚期雌激素水平升高、孕激素水平降低,雌激素與孕激素比值升高是宮頸成熟啟動的關鍵因素之一[5]。本研究治療組與對照組相比:E2水平明顯升高(P<0.05),P水平明顯下降(P<0.05),說明中藥活血行氣湯有明顯的促宮頸成熟作用。綜上所述,中藥香元助生湯用于妊娠晚期促宮頸成熟效果肯定。
[1]樂杰.婦產科學[M].第6版.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94(95):135-136
[2]林麗莎,何曉宇,曾敏紅;延期妊娠并發羊水過少66例臨床分析[J];中國實用婦科與產科雜志;2000年08期
[3]韓萬鳳;王敏;汪志敏;綜合評分法在判斷胎盤功能中的應用[J];山東醫藥;2006年09期
[4]王鶴,李穎,王寧;過期妊娠母嬰高危程度的探討[J];中國煤炭工業醫學雜志;2002年03期
[5]李瑋璟,王自能,黃以萍;妊娠40周后伴胎兒過熟綜合征胎盤超微結構電鏡觀察[J];暨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與醫學版);200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