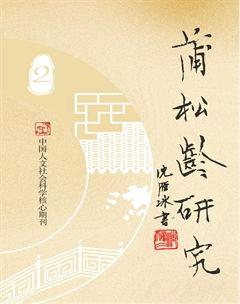陳淑卿與顧青霞:關于蒲松齡的寶應之戀(續)
馬俊慧+馬晽文麗
中圖分類號:K207 ? 文獻標識碼:E
[續2014年第1期]
四
正是《又贈孫安宜兼寄高魯壇》這一題11首詩,讓我們知道了蒲氏這位“夢中情人”的名字。多年后,他為其作了8首詩,題為《孫給諫顧姬工詩作此戲贈》,將這8首詩與上面的11首詩對照,其中的契合之處,不論自明。只不過物是人非,往日的情人,此時已經成為自己好友孫蕙的姬妾。孫蕙的另一位好友汪懋麟,曾經為孫寫過3首題為《莫春過樹百寓齋出姬人顧粲可玉山堂詩卷見示兼聽小史云岫彈琴》的詩,在“孫郎解珮得青霞”一句下注曰:“姬名也。” [11]蒲詩中明確出現“青霞”這個名字的有3題,即《為青霞選唐詩絕句百首》、《聽青霞吟詩》、《傷顧青霞》,前2題共3首當作于在寶應為孫蕙及其夫人祝壽期間,后1首則作于顧青霞去世之后。從上述第一首和汪懋麟的詩來看,顧青霞的原名應當叫顧粲可,小名喚作可兒,青霞當是淪為歌伎后起的藝名。
顧青霞何時成為孫蕙的姬妾,尚無專文論及,但在論及蒲、顧二人關系時,不少人言下之意都是蒲見到顧時,她就已經是孫蕙的侍妾,這是沒有依據的。在《聊齋詞集》中,有寫給孫蕙的4題詞,題下注“戲簡孫給諫”,寫的卻全都是顧青霞,看似奇怪,實際上是很有深意的。作為開題的第一首分為3闋,上闋是《夢幻八十韻》中描述的情形,中闋寫的則是包括《聽青霞吟詩》等在內的祝壽寶應期間的一切。下闋分為三層:第一層想象顧來到孫蕙府中后,“萬喚才能至,莊容佇立,斜睨畫簾。時教吟詩向客,音未響,羞暈上朱顏”;第二層寫蒲對顧的情感,“憶得顫顫如花,亭亭似柳,嘿嘿情無限。恨狂客兜搭千千遍,垂粉領,繡帶常拈”;第三層隱諱地說出對顧的思戀:“數歲來未領神仙班,又不識怎樣勝當年”,并借孫蕙夫人趙氏之口說出自己“廝妮子,我見猶憐”的心思。下面3題,則描述了他們又一次見面的情形:“凄涼一夜,銳減小腰圍”,“意惴惴,恐人覷破,急蹴纖彎”。這4題詞告訴我們,至少此時,顧青霞尚未成為孫蕙的姬妾,而蒲氏寫這些詞的目的,就是在委婉地請求孫蕙玉成自己和顧青霞的姻緣。從題中稱“戲簡”、不用“戲贈”看,這些詞不是當面呈交,應是通過信簡的形式傳遞給孫蕙的,結合詞的內容,這只能是在康熙十四年孫蕙達京任“給諫”之初。
上文我們曾經論及,康熙十年時,蒲氏的“夢中情人”應為十五歲,現在我們知道,這位“夢中情人”就是顧青霞,那么康熙十四年時,顧青霞應為十九歲。在《賀新郎·王子巽續弦即事戲贈》等5題中,《妾十九》一題中說“妾十九,妾十九,郎二九時妾始有”,而此年蒲氏剛好三十六歲。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賀新郎·王子巽續弦即事戲贈》等5題描述的就是《戲簡孫給諫》中“凄涼一夜”的情形:“枕頭邊,端相仔細,芳容如昨。”時間應當是蒲氏參加康熙十四年鄉試之前:“疇昔狂言上場頭,依樣葫蘆要作”,“囑郎休蹈從前過,蕩天涯歲月久拋卻”,再不要像當年北歸參加康熙十一年鄉試后那樣,因為落榜而音信杳無。因此,所謂“王子巽續弦即事戲贈”,就是“即王子巽續弦事戲贈顧青霞”。
汪懋麟的《莫春過樹百寓齋出姬人顧粲可玉山堂詩卷見示兼聽小史云岫彈琴》作于“庚申”即康熙十九年(1680),所以,顧青霞成為孫蕙的姬妾,當在康熙十四年隨孫蕙赴京后,康熙十九年前。
那么,顧青霞是哪一年成為孫蕙侍妾的呢?這就要說到上文曾提及的《閨情呈孫給諫》。無論從內容看,還是從抄本《聊齋偶存草》的排序看,該題為康熙十二年蒲氏對顧的思戀之作,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詩題中出現“孫給諫”卻令人難以理解,因為此時孫尚在寶應和高郵任上,任“給諫”是后來的事。另外一個奇怪之處是,這題詩的前4首竟又出現在康熙十八年(1679),題作《同沈燕及題思婦圖》,后5首則又出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題作《閨情》,這說明蒲氏康熙十八年、二十四年曾兩次使用了在康熙十二年寫成的這9首詩,這9首詩的原題即作《閨情》,康熙二十四年又使用后5首時,為區別起見,才在原9首題下注上了“呈孫給諫”4字。而蒲氏之所以在康熙十八年,將想象顧青霞懷念自己的4首詩題在《思婦圖》上,很可能就是此年顧由少女變成了少婦。
排在《同沈燕及題思婦圖》前的,是《贈劉孔集》,詩題中出現“贈”字,說明這兩人是見面的。孫蕙在淄川老家有一處別業萬仞芙蓉齋,袁世碩先生認為營造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 [12]50,則劉孔集此年出現在淄川,很可能即是為營造萬仞芙蓉齋而來。孫蕙營造萬仞芙蓉齋是為了顧青霞(此點將在后面論及),因此前幾個月還在與友人吟詩倡和的蒲氏,到了四月四十歲生日的時候,忽然就病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個月(《病中》)。結合《贈劉孔集》的內容,蒲氏的病因何而起是不難推論的,就是聽到了孫娶顧為妾的消息后,心靈受到打擊所致。此前一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恰好是鄉試之年,蒲松齡再次落榜,所以顧成為孫的侍妾當在康熙十八年春。此后,劉孔集為營造萬仞芙蓉齋來到淄川孫蕙的老家,上文我們曾提到過劉在蒲、顧之戀中可能的角色,故而蒲氏向劉抒發自己的失落之情。
康熙二十年(1681),孫蕙奉命入閩充福建鄉試副主考官。返程時在家鄉停留了一段時間,直到次年春方才返京 [12]50。從《上孫給諫書》中“自覺面目酸澀,不可以登君子之堂”一句看,蒲氏沒有與孫蕙見面,其中原因恐怕就是孫娶顧為妾之事,使蒲氏認為孫蕙這位“曩年把臂之交”,“不以我為人” [13]。但在孫蕙離家赴京后,蒲氏卻去過孫蕙家,《過孫給諫芙蓉齋》一詩可作證明。此年蒲氏總共只留下4題詩,這是第一題,最后一題即是《孫給諫顧姬工詩作此戲贈》。將兩題內容對照看,可知前題中的“搔首憶京華”之人正是指顧青霞。顧不隨孫蕙赴京,卻在孫赴京后于家中見蒲氏,這是很耐人尋味的。排在《過孫給諫芙蓉齋》之后的是《傷劉孔集》,疑劉去世的消息,正是此時于顧處得知。第三題《賦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也很值得重視,這首詩顯然是蒲氏對顧邀其“過芙蓉齋”的回味。這一年的4題詩全都與顧有關,而且第三題中“劫種三生寧可避”的感慨、對費長房“縮地術”的向往,均反映出蒲氏感觸之深,結合《孫給諫顧姬工詩作此戲贈》的內容,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次見面又一次燃起了蒲氏對于愛情的渴望。endprint
在路輯《聊齋詩集》中,有一首《臥萬仞芙蓉齋聽棋客爭道》,因不能編年被收入“姑附”詩中。萬仞芙蓉齋營造于康熙十八年,此后到康熙二十一年(1692)春孫蕙離家赴京,這期間蒲氏是不會臥于此處的。蒲氏臥于萬仞芙蓉齋,只能是上文所述的“過孫給諫芙蓉齋”之時或其后。
萬仞芙蓉齋并不在孫家的宅院中,而是坐落于孫的私家花園、即孫家宅院西側的逸峰園 ① 。萬仞芙蓉齋為顧青霞所居 [14],蒲氏“臥”于此處是很耐人尋味的。《聊齋志異》中有一篇《絳妃》,寫蒲氏“癸亥歲”夢至一處,“殿閣高接云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余級始至顛頭” [15]737,這無疑就是萬仞芙蓉齋。“癸亥歲”當指康熙二十二年(1693),因此,《絳妃》所記之“夢”,實為康熙二十一年夏蒲氏“過芙蓉齋”之記憶。這樣,就不難做出推論:康熙二十年孫蕙奉命入閩返程歸家后,次年春,顧青霞沒有再隨孫赴都,而是住在了康熙十八年營造的萬仞芙蓉齋中。就在這年夏天的一個傍晚,顧邀蒲氏來到住處,《過孫給諫芙蓉齋》當是蒲氏接到邀請時所作,當夜蒲氏臥在了萬仞芙蓉齋,《臥萬仞芙蓉齋聽棋客爭道》便是此時所作。題中用“聽”而不是“觀”,似乎也透露出一些信息:也許當時并不是像《絳妃》中描述的那樣,周圍有“諸麗者”吧。
按照《絳妃》所述,顧青霞請蒲氏來萬仞芙蓉齋,是“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那么這是一篇怎樣的檄草呢?通過蒲氏的“追記”,我們看到,這檄草其實就是對孫蕙憑借權勢,拆散蒲、顧之戀并奪人所愛的聲討,因此,所謂的“檄草”,實際上就是顧青霞對孫蕙霸占自己的控訴。顧青霞邀蒲氏于夜間在住處相會并互訴衷腸,也可以看出顧對愛情的執著,以及那種“背城借一”的勇氣,這甚至是蒲氏都不能望其項背的。由此可以看出,當康熙十八年,顧青霞被迫成為孫蕙姬妾時,她就已經做好了避開孫蕙、來淄川與蒲氏再度相會的計劃,營建萬仞芙蓉齋,也許就是她提出的嫁給孫蕙的條件之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孫蕙丁父憂,服未除便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在家中死去 [12]50。孫蕙死后,他的眾多姬妾們都被放還出去,但顧青霞卻留了下來,沒有再返回自己的故鄉。這當然不會是為了給孫蕙守節,而是因為淄川有她深愛著的人——蒲松齡,然而不久她卻寂寞地離開了人世。
五
《陳淑卿小像題辭》可分為5段:“舊本瑯琊”前為第一段,“伯鸞將婚”至“涕濕衾花”為第二段,“胡消息之能通”至“跂望豆于沙汀”為第三段,“遭逢苦而憂患深”至“凄絕斷腸之草”為第四段,下面為第五段。文中第三段講的就是蒲氏南游時與顧的“三夜”之緣,即《夢幻八十韻》中描述的“傳書之夜”,祝壽寶應期間的“宵奔之夜”,以及《夜發維揚》前的“離別之夜”。第四段講顧脫出風塵后與蒲氏的來往,這在首句中即已表明,以下分三層:首先描述的是康熙十四年的那一“夜”,接著說顧在成為孫妾后仍未忘懷蒲氏,最后是說在孫蕙去世后不久,顧青霞便也離開了人世。特別是其中“兒啼女號,謫我之惡聲未有”一句,甚至反映出顧在孫蕙死后,有不怕蒲氏家中反對,與蒲氏結為連理的念頭。下一段“五夜中現影行來”中的“五夜”,就是蒲、顧二人愛情生活的概括,第五夜恐怕正是“臥萬仞芙蓉齋聽棋客爭道”的那一夜。這樣看來,題在陳淑卿小像上的這篇文字,應當是王敏入及妻陳氏的遭遇,觸動了蒲氏內心深處敏感的神經,從而不可遏制地用文字抒發出來,就如同其將思顧之作題在《思婦圖》上一樣。這樣我們就可理解,蒲氏為何要在文章的最后說“千秋下有人拾得,恐當真真”,他告訴我們是在為顧作“小傳”,千萬不要當成是王敏入妻陳氏的“小傳”。
王敏入及妻陳氏的遭遇之所以觸動蒲氏,是因為他們的遭遇與顧青霞父母的遭遇有相通之處,這就是《陳淑卿小像題辭》中第二段描寫的情形:他們都是在戰亂中離開家鄉的,在異鄉相遇,鄉音讓他們彼此感到親近,遂私定終身,半年后一起回到男方家里,由于是“因亂成婚”、“為歡廢禮”不被男方父母接受,女方只好回到自己家中,但他們仍然暗中往來。后來被女方父母發現,他們失去了相互來往的機會。可能就是這個時候,女方有了男方的孩子,這個孩子就是顧青霞,也就是在下一段中所說的“嬌嬰”。至于顧青霞為何會淪落風塵,從《聊齋志異》中出現的一些篇章,如《嬰寧》、《阿霞》等等來看,應該是其母去世時托人不淑所致。
顧青霞的父親是什么人,目前尚無明確的資料作為論述的依據,但也不是毫無端倪可尋。《陳淑卿小像題辭》中說:“方悲金屋之人,捐曾似扇;尤惜金錦之物,棄不如麑”,前一句是說顧的母親本是大家閨秀,卻成了棄婦,后一句是說顧青霞應該是千金小姐,卻淪落風塵,可見其父是世家子弟,所以當顧青霞“曉窗把手淚沾巾,為說桃源傍水濱”、向蒲氏講述母親的故事時,蒲氏才會有“為尋芳跡到蓬萊,怪道佳人錦作胎”的感慨。“家居蒼樹隔,忱悃素書將”,“投珠酬柳毅,納杵囑裴航”,“勿使離魂女,空懷墮策郎”,顧青霞是因為托蒲“傳書”才將終身交付給蒲氏的,而蒲氏當時正作幕于寶應,表明“傳書”的對象即顧的父親應在寶應,“家居蒼樹隔”則說明顧青霞自己的家即母家,應與蒲氏作幕的寶應相鄰。顧青霞最喜歡唐朝詩人王昌齡的《西宮春怨》,“愛歌樹色隱昭陽”,而“昭陽”正是寶應鄰縣興化的古稱。汪懋麟詩中說顧青霞“怪底閨房多秀氣,顧家今已勝喬家”,似乎在隱諱地說顧青霞本應姓“喬”。則“顧”應為其母姓,其母的情人即顧青霞之父當應姓“喬”。
喬家正是寶應的世家大族,其鼎盛期就是在明末和清代前期。寶應喬家走上仕宦之途始于喬可聘,喬可聘為明天啟二年(1622)進士,官至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在南明福王政權滅亡后隱于家鄉柘溝(今寶應縣氾水鎮柘溝村) ① 。喬家與興化的世家大族吳家、李家均為姻親關系,喬可聘的女兒嫁給曾在明朝擔任次輔的吳甡的長子吳元萊 ② ,而吳元萊之女又嫁給喬可聘次子喬英的兒子喬崇哲 [16]229,喬英的一個女兒則嫁給與喬可聘同為明朝遺臣的史學家李清的孫子李茂竹 ③ 。興化顧家也是當地大姓,與寶應喬家同樣有來往,清初著名畫家顧符稹,后來就曾寄居喬可聘三子喬萊門下,并為其作《桃花流水圖》 ④ 。喬萊為康熙六年(1667)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 ⑤ 。喬萊與汪懋麟為至交,又是同年進士,也是姻親關系,汪懋麟的女兒便嫁給喬萊的次子喬崇讓 ① ,因此,汪懋麟對喬家的情況應當是很熟悉的,也許這就是汪對顧身世有所耳聞的原因。當明、清易代之際,喬可聘長子喬邁、次子喬英曾分別避亂于云間(即松江縣,今屬上海市)和昭陽(即興化) ② ,這與《陳淑卿小像題辭》中“王孫去其故里”的描述也是吻合的。endprint
《聊齋志異·連城》中有一首詩,取自《閨情呈孫給諫》,結合故事的內容,顧青霞之母當是女主人公連城的原型。而這個故事的男主人公喬生,蒲氏在故事末尾特別強調:“生名年,字大年。”我們知道,“邁”有年長之意,所謂“大年”即“邁”也。蒲氏在故事的末尾,毫無理由地加上這么一句話,正說明蒲氏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想告訴人們:顧青霞的父親就是喬邁。喬邁,字子卓,弟喬萊稱其“絕意仕進,治池館柘溪,博覽群書,于典故多所辨證,尤工五言詩,大學士吳甡賦詩褒美,比于范粲子孫” ③ 。也許顧青霞的名字作“粲可”,其淵源便在于此。順治年間,東南沿海一帶反清復明活動風起云涌,隱居家鄉的喬可聘結交藏身寶應的梁以樟等人,與東南海上的南明武裝暗通消息、積極策應,喬邁也投身其中 [17]。“河東漫寄鮫綃淚,十五年前滿畫箱”,應當就是在這樣的戰亂中,喬邁與顧青霞的母親結成了一段亂世中的情緣。顧青霞出生的那一年,正值喬可聘夫人、也就是喬邁的繼母潘氏去世 ④ ,喬邁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還有這樣一個女兒,顧青霞請蒲氏傳書,也許正是想讓父親來幫助自己脫離苦海。應該說蒲氏是有傳書的條件的,王洪謀《行略》中記載的蒲氏在寶應交游的“王會狀式丹兄弟”,其姑祖母王氏就是喬邁的生母 ① 。不知道什么原因,蒲氏卻將顧的“素書”藏在了“篋”中。從蒲氏對于自己這一段戀情遮遮掩掩的態度看,蒲氏對于愛情的追求,遠沒有顧青霞執著和大膽,這應是導致蒲、顧之戀以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創作了大量的愛情故事,生動地刻畫了眾多執著于愛情的大膽的女性形象,如果沒有作者的親身經歷,這是無法想象的。從蒲氏的生平經歷看,顧青霞無疑就是這些女性形象的原型。當一段刻骨銘心、魂縈夢繞的愛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實現,他就會在想象的世界中去邀游。從這個意義上說,蒲松齡的寶應之戀,正是蒲氏創作的不盡的源泉。
參考文獻:
[11](清)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遺稿(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2]袁世碩.蒲松齡與孫蕙[M]∕∕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濟南:齊魯書社,1988.
[13]路大荒.蒲松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孫啟新.也談顧青霞[J.蒲松齡研究,2012,(1).
[15](清)蒲松齡.絳妃[M]∕∕聊齋志異:卷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16](清)喬守敬.貢試硃卷[M]∕∕代硃卷集成:第369冊.臺北:成文出版社,
1992.
[17]馬晽文麗,馬俊慧.康熙《寶應縣志》喬可聘“為邑令所構”事考[C]∕∕寶應
喬氏家學研究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責任編輯:李漢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