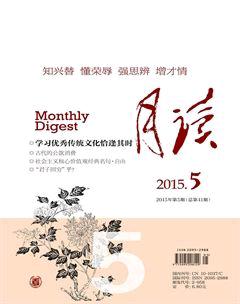狂妄自大的赫連勃勃
陳良
西晉滅亡以后,中國(guó)北方進(jìn)入動(dòng)亂年代,先后出現(xiàn)了五胡十六國(guó)。這期間,一個(gè)叫大夏(史稱胡夏)的國(guó)家應(yīng)運(yùn)而生,雖然它僅僅存在二十余年,在歷史長(zhǎng)河中只是過(guò)眼云煙,但是這個(gè)國(guó)家的領(lǐng)導(dǎo)人自我感覺(jué)特好,自以為功蓋天地,成就非凡。
這個(gè)大夏國(guó)的建立者為赫連勃勃,其姓名和國(guó)號(hào)都不同凡響,很有來(lái)頭。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鐵伐部人,原名劉勃勃,與前趙(后漢)建立者劉淵同族,系匈奴右賢王去卑的后代。他出生于匈奴貴族世家,其父劉衛(wèi)辰曾被前秦苻堅(jiān)封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部;到了前秦國(guó)內(nèi)戰(zhàn)亂時(shí),劉衛(wèi)辰擁有了朔方之地,手握三萬(wàn)八千人馬。后來(lái)北魏軍來(lái)攻打,劉衛(wèi)辰命令他兒子力俟提抗戰(zhàn),被魏軍打敗。魏人乘勝渡過(guò)黃河,攻克代來(lái),俘獲并殺死劉衛(wèi)辰。劉勃勃輾轉(zhuǎn)投奔后秦高平公沒(méi)奕于,沒(méi)奕于把女兒嫁給了他。后秦皇帝姚興封他為安遠(yuǎn)將軍、陽(yáng)川侯,讓他助沒(méi)奕于守高平;隨后又封他為持節(jié)、安北將軍、五原公。
劉勃勃身材高大,能言善辯,氣宇軒昂。姚興對(duì)他頗為欣賞,認(rèn)為他有濟(jì)世之才,可以與自己共平天下。可是,這個(gè)劉勃勃野心勃勃,不甘心屈居人下,寧肯開(kāi)墾自留地,也不愿為人種莊稼。公元406年,劉勃勃襲殺岳父沒(méi)奕于,兼并其部眾;次年,他自稱天王、大單于,獨(dú)立建國(guó),設(shè)置百官。他認(rèn)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代,故國(guó)號(hào)大夏;又認(rèn)為匈奴從母姓姓劉,不合理,帝王“東天為子,是為徽赫實(shí)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xié)皇天之意”。別看他一介武夫,改姓赫連氏卻很有創(chuàng)意。當(dāng)然,這么偉大的姓氏赫連只有大夏皇室正統(tǒng)專用,其余支庶沒(méi)有資格享用,皆以鐵伐為氏。
做了大夏天王之后,赫連勃勃連年攻擾后秦的北境。他采用騎兵倏來(lái)忽往、突然襲擊的戰(zhàn)術(shù),疲憊后秦,攻占不少地方。姚興死后,其子姚泓即位,不久被劉裕所滅。劉裕攻占長(zhǎng)安以后,匆匆南回準(zhǔn)備奪取東晉帝位,而留其子劉義真守長(zhǎng)安。赫連勃勃趁機(jī)進(jìn)駐長(zhǎng)安,于418年稱皇帝于灞上,而留其子赫連璝守長(zhǎng)安,自己仍回大夏都城統(tǒng)萬(wàn)。
都城統(tǒng)萬(wàn)是赫連勃勃征調(diào)十萬(wàn)夷夏民眾筑成的,因?yàn)樗匝浴半薹浇y(tǒng)一天下,君臨萬(wàn)邦”,所以叫“統(tǒng)萬(wàn)”。都城叫“統(tǒng)萬(wàn)”已經(jīng)夠牛氣了,更為牛氣的是,其城門(mén)名稱非常霸氣:“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yǔ),東門(mén)叫招降北魏,南門(mén)叫南面劉宋,西門(mén)叫征服西涼,北門(mén)叫掃平朔方。
都城及四門(mén)的名稱,無(wú)疑彰顯大夏領(lǐng)袖壯志凌云,氣吞山河。那么,大夏國(guó)究竟有沒(méi)有這個(gè)實(shí)力或底氣?
答案是否定的。
所謂“大夏”,不過(guò)是占地千里的“蕞爾小國(guó)”而已。赫連勃勃盡管頗有謀略,但“政刑殘虐”,橫征暴斂,民不聊生。據(jù)《資治通鑒》記載,統(tǒng)萬(wàn)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高五仞,其堅(jiān)可以厲刀斧。臺(tái)榭壯大,皆雕鏤圖畫(huà),被以綺繡,窮極文采”。如此宏大而精美的工程,自然消耗大量財(cái)力人力,筑城民工屢屢付出生命代價(jià)。《晉書(shū)》稱:“蒸土筑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筑之。”對(duì)待制作兵器的工匠,也非常殘酷,動(dòng)輒殺戮:“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
赫連勃勃本人時(shí)常攜帶弓箭,看見(jiàn)不順眼的就射殺;對(duì)待自己的臣僚也毫不客氣,總是令人膽戰(zhàn)心驚。處于戰(zhàn)亂窮困年代,赫連勃勃毫不體恤民眾,只顧貪圖享樂(lè),窮奢極欲不輸于大國(guó)帝王。赫連勃勃死后六年,北魏攻陷統(tǒng)萬(wàn),俘虜赫連勃勃父子的嬪妃、宮女?dāng)?shù)以萬(wàn)計(jì),還有馬三十余萬(wàn)匹,牛羊數(shù)千萬(wàn)頭,國(guó)庫(kù)珍寶、車(chē)旗、器物不計(jì)其數(shù)。對(duì)此,時(shí)任北魏皇帝拓跋燾禁不住感嘆:“一個(gè)巴掌大的小國(guó),竟然如此奴役人民,豈能不亡?!”
不過(guò),在大夏文人筆下,赫連勃勃是非常英明神勇的君王。赫連勃勃攻占長(zhǎng)安而返回統(tǒng)萬(wàn)以后,以為自己的事業(yè)達(dá)到頂峰,于是在舉國(guó)開(kāi)展歌功頌德運(yùn)動(dòng),并挑選其中最好的一篇文章鐫刻于石碑,樹(shù)立在統(tǒng)萬(wàn)南部,供國(guó)人瞻仰與膜拜。
這篇文章出自大夏著作郎(專職文官)趙逸的手筆。簡(jiǎn)而言之,該文大致包括四方面內(nèi)容:第一部分是序言,從歌頌遠(yuǎn)古帝王夏禹著筆,意在宣示赫連勃勃作為禹的后裔,根正苗紅,乃中原正統(tǒng);第二部分回顧大夏(胡夏)的建國(guó)歷程,記述赫連勃勃如何開(kāi)創(chuàng)基業(yè);第三部分總結(jié)立國(guó)十多年來(lái)的偉大成就,著重描述首都面貌一新和國(guó)泰民安;結(jié)尾部分是駢文詩(shī)章,以更為華麗的詞藻謳歌贊美,讓偉業(yè)傳揚(yáng)后世,永垂不朽。
文章通篇充滿了對(duì)赫連勃勃的溢美之詞,有些吹捧簡(jiǎn)直令人肉麻:“像龍一樣在北都興起,道義覆蓋九州;像鳳一樣翱翔天宇,威名傳遍八方。”“我皇天未亮就上朝,廢寢忘食,策劃謀略任用將領(lǐng),一舉一動(dòng)沒(méi)有過(guò)失。”“在內(nèi)傳揚(yáng)名教,在外鏟除群虜。教化光照四方,聲威遠(yuǎn)播九州。”諸如此類(lèi)的歌頌,俯拾即是。
想必,赫連勃勃審閱這篇文章,肯定滿心歡喜。但是,北魏皇帝拓跋燾看了,感覺(jué)它夸大其詞,當(dāng)即發(fā)怒說(shuō):“這文章是哪個(gè)小子寫(xiě)的,應(yīng)該把他揪出來(lái),立即斬首!”重臣崔浩當(dāng)即勸說(shuō):“文士就是這個(gè)德行,往往言過(guò)其實(shí);寫(xiě)這文章的也是不得已為之,討主子喜歡,混口飯吃而已,不足以治罪。”趙逸由此才僥幸逃過(guò)一劫。
今天我們閱讀這篇文章,也會(huì)為作者汗顏。文人應(yīng)把操守放在第一位,即使在威逼利誘之下,也該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而不夸大其詞。更關(guān)鍵的問(wèn)題在于,赫連勃勃并無(wú)自知之明,創(chuàng)建了一個(gè)大夏國(guó)就自我膨脹,以為立下曠世奇功,非得樹(shù)碑立傳不可。實(shí)際上,在那個(gè)特殊年代,“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一個(gè)人有了一支武裝,開(kāi)創(chuàng)一份基業(yè)并不難,難的是如何經(jīng)營(yíng)這份基業(yè)。如果你勵(lì)精圖治,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打理好,讓民眾安居樂(lè)業(yè),使綜合國(guó)力不斷增加,也許能夠成就一番大業(yè);如果你好大喜功,嚴(yán)刑峻法,橫征暴斂,窮兵黷武,窮奢極欲,最終會(huì)失去那份基業(yè)。五胡十六國(guó)君主之中,除了苻堅(jiān)、姚興、石勒等少數(shù)較為明智,多半都“不似人君”,最終難逃“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命運(yùn)。
赫連勃勃盡管有志于“統(tǒng)一天下,君臨萬(wàn)邦”,并揚(yáng)言“招魏、朝宋、服涼、平朔”,可是他在治國(guó)理政方面無(wú)所建樹(shù),其“政刑殘虐”,橫征暴斂,必然導(dǎo)致民貧國(guó)弱,大夏也只能成為貽笑大方的“意淫強(qiáng)國(gu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