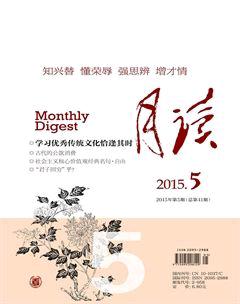王莽新政:改革失敗的反思
張國剛
《資治通鑒》講座
王莽新政:改革失敗的反思
王莽的發跡
漢成帝劉驁做太子的時候,父親漢元帝對他并不滿意,母親王政君雖是皇后也不得寵。元帝寵幸的傅昭儀和馮昭儀各生了一個兒子,元帝幾次想改立次子劉康為嗣,多虧母舅王鳳和另一外戚史高(宣帝劉詢的至親)鼎力維護,劉驁才沒有被換掉。成帝即位后,對于幾位舅舅特別關照,同日封侯。可是,這里面卻沒有王莽的父親。因為王莽的父親王曼早亡,沒有趕上王家發達的時候。王莽的幾位堂兄弟和姑表兄弟,憑借著父親或為將軍、或封侯爵的蔭庇,一個個追逐時尚,競為奢侈,“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唯有王莽“孤貧”,神氣不起來。可是王莽的社會名聲最好。
史書記載,年輕時的王莽“折節為恭儉”,是一個謙卑好學的青年。他刻苦攻讀《禮經》,拜沛郡的陳參為師,“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穿得像普通學生)”。王莽孝敬寡母,奉侍寡嫂,養育孤侄,盡心盡力。在待人接物上,他“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人緣和口碑都極好。大伯父王鳳病重期間,王莽侍湯奉藥,蓬首垢面,幾個月衣不解帶,比王鳳的兒子還孝順。身為大將軍的王鳳,深受感動,臨終前極力向皇太后和成帝推薦王莽。皇帝給了王莽一個黃門郎的小官,這一年他28歲。
王莽在后來的仕宦生涯中,繼續牢牢把握住兩條升遷秘訣,一是結名士造勢,二是傍叔父升官。叔父成都侯王商上書,請求皇帝把自己的封邑分給王莽,許多“當世名士”也都為王莽說好話,使成帝覺得王莽確實是個人才(“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前16),封王莽為新都侯。可是,他“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王莽廣散錢財,“家無所余,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①。在位的人都樂于推薦他,不在位的人也都傳播著他的好名聲。
王莽人生的真正轉折是從扳倒表兄淳于長開始的。淳于長是王政君的外甥,與成帝為姨表兄弟。王政君當初不贊成立趙飛燕為成帝的皇后,是淳于長給王政君做了思想工作。為此,成帝對淳于長頗有一份感激之情。其時,淳于長已位居九卿,地位在王莽之上。大司馬王根病重,淳于長是繼任的熱門人選。可是,淳于長為人不檢點,與被廢黜的許皇后之姊通奸,還在書信中戲弄許皇后。王根病重,淳于長自以為不久就可以接位,在外面胡亂吹噓,封官許愿,惹得王根很不高興。王莽搜集了淳于長的一切丑事,并且捅了出去,又在王根面前挑撥離間。結果淳于長吃了官司,王莽在王根的力薦下,順利當上了大司馬。
王莽的新朝
公元前7年,王莽以大司馬輔政大約一年,漢成帝因為淫欲過度,死在寵妃趙合德(趙飛燕之妹)的肚皮上。成帝無子,侄子劉欣(前25—前1)即位,是為哀帝。哀帝的祖母傅昭儀和母親丁氏家族成為新貴,哀帝的寵臣董賢為大司馬。王政君主動讓老對手一頭②,王莽也被迫下野。哀帝在位的七八年時間里,外戚傅家、丁家以及新貴董賢家族,瘋狂地聚斂財富,掠奪百姓田地,與王莽的折節下士、清貧廉潔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
哀帝崩駕,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即取回璽印,召王莽入朝。董賢被殺,王莽執政,獲得朝野歡迎。新皇帝平帝(前9—6)即位時,年僅八歲,王政君名義上垂簾聽政,實際政務操之于王莽之手。經過六年的經營,王莽依然是通過沽名造勢、討好太皇太后的老辦法,一步步掌控了朝廷權力。公元6年,他擔心日漸年長的平帝親政后,會不利于自己,乃暗中毒殺了15歲的平帝(也是王莽的女婿),自任“假皇帝”。兩年后,王莽廢漢自立,改為新朝。
新朝一共有15年的歷史。王莽執政前后,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集中在財稅(五均六筦)、貨幣、土地(王田制)等方面。如何評價這些改革,是歷來王莽評價中的重點。
王莽的貨幣改革
貨幣改革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王莽正式登基前即公元7年的事。改革的內容是在流通的五銖錢外,增發大面值新幣,包括兩種復古的刀形幣(錯刀面值五千,契刀面值五百)和一種圓形幣“大錢五十”,面值很大,分別是傳統五銖錢的千倍、百倍和十倍。可是,重量并不與之相匹,例如“大錢五十”,實際重量只有12銖,卻能當50枚五銖錢用。有人融化掉五銖錢,改鑄成新幣,獲利千倍百倍。
市場的混亂促使王莽在即位的第一年(9),進行第二次貨幣改革,廢除五銖錢和刀形幣,只流通“大錢五十”,另增加發行一銖的小錢。于是,市面上流通的貨幣的價值一下子減少了許多,出現通貨緊縮的混亂局面。
市場的錢不夠用,激起了王莽進行最為奇葩的第三次貨幣改革。公元10年,王莽改錢幣名為“寶貨”,分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說寶貨的材質由金、銀、銅、龜、貝五種材料組成,“六名”是說寶貨的規格共有金貨、銀貨、龜貨、貝貨、貨泉和布貨六種,“二十八品”是說寶貨的種類分為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貨泉六品、布貨十品,總共28種樣式。各種名品的貨幣,價值不一,最高者黃金一品,值萬錢,布錢大的值千錢,貨泉小的值一錢。如此復雜的貨幣,除了引起市場混亂,沒有任何作用。
王莽最后一次貨幣改革,發生在天鳳元年(14)。這次改革依然保留了金銀貝泉布等貨幣形式,但主要是修正過去面值與實際價值不相符的問題。由于不同材質(金銀銅布)之間的貨幣價值很難調節到位,有些措施,比如大錢五十,減為值一錢,貶值過快,平白讓不少百姓遭受巨大損失。
王莽的王田制
王莽即位伊始(9),立即推出田制改革法令。法令規定:一、全國土地改稱王田,用這種形式收歸國有,禁止私人買賣。二、丁男通常占田不過百畝,有田之家若丁男不足八口而占田超過一井(即九百畝)者,要把限額之外的土地分配給親族鄰里。三、沒有土地的家庭可以按丁男百畝之數授田。
早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對策中就提出限制占有過多土地。漢哀帝之時,師丹等人的議論,直接針對漢末土地兼并的積弊。孔光、何武等甚至根據師丹的建議,制定了一個具體的“限田”措施。但是,由于大司馬董賢和哀帝外戚家族傅氏、丁氏大量占有土地,從中作梗,便不了了之。王莽要廢除土地私有和土地買賣的制度,將土地收歸國有,使耕者有其田,缺乏起碼的操作性。
毋庸置疑,王莽的王田制,直接打擊的是大土地所有者,改變“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不否定漢代有一些類似卜式這樣善于經營的勞動致富者,但是,真正廣占良田的富人,恐怕是那些武斷鄉曲、有官府背景的豪族,或者干脆就是貪官污吏、王公貴族。武安侯田蚡曾經公然要奪取已經失勢的魏其侯竇嬰的良田,由此可見一斑。哀帝時孔光等的限田令,直接針對的就是“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但受到了抵制。現在王莽的“王田制”更為激進,沒有資料表明,王莽何德何能,依靠何種力量,能夠推動這場觸動土地私有制度的改革!
王莽的財稅改革
財稅改革即所謂“五均六筦”政策。“筦”是“管”的異體字,即管制的意思,“六筦”就是指國家對六個方面的經濟活動實行管制。王莽的詔書提到“六筦”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管)之。”①
前三筦是對鹽、鐵、酒等三種重要物品的生產和流通進行管制,國家壟斷專營。這些都是百姓日用生活品,不許私家染指。鹽、鐵專賣都是沿襲漢武帝時期桑弘羊主持的經濟政策,酒的專賣,也是武帝的政策,昭帝時期一度廢止,王莽恢復酒的專賣后,規定賣酒收入,30%抵償各種成本(原料、燃料、工具及人工費用),70%作為純利潤歸官府。
第四筦、第五筦主要是國家壟斷貨幣鑄造,并對鑄造貨幣的原材料的采集加以管制。凡民間開采的金、銀、銅、錫和采捕作為貨幣原料的龜、貝,其產品必須由政府收購,不得在市場上出售。漢武帝時期也規定國家壟斷鑄幣,但是只有壟斷了制作貨幣的原材料,政府才能真正壟斷鑄幣權。
第六筦是對于城市工商業經營和市場物價與民間金融信貸行為的規范和管制,謂之“五均賒貸”,主要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幾個大城市中實行,也旁及郡縣。負責人稱為五均司市師,由原來各城市的市場負責人(市令等,實際上政府任命各地富商擔任該職)兼任,其他郡縣的市官則稱為司市。市師之下設立掌握具體市場交易行為的官員五人,稱為均官,錢府丞一人,稱為錢府官。他們分別掌管均平物價、稅收征取和賒帳放貸事宜。
五均是武帝時平準法的發展,規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價格作基礎,按商品質量分為上、中、下三等標準價格,稱為“市平”。市場價格超過平價時,政府按平價出售商品,促使價格回落;市場價格低于平價時,則聽任自由買賣。對于五谷布帛絲綿等重要民用產品,如果滯銷,則按成本加以收購,使經營者不致虧折。
賒貸也是五均司市的任務之一。“賒”是為市民非生產性的開銷,如祭祀喪葬提供的短期無息貸款。“貸”是為小工商業者提供的生產性資金,期限較長,收取年利潤的10%為利息。
總之,所謂“六筦”(六管),就是由國家全面壟斷重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生產和銷售,壟斷貨幣發行權,控制大城市的物價波動、民間借貸等工商業活動。
改革的反思
王莽改革的初衷是什么?史稱“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①,是說王莽改革有復古主義或者理想主義傾向。
王莽利用皇太后及諸父的蔭蔽,夤緣而上,加上偽裝自己,推銷自己,追逐權力的本能引其一路向上,最后竟然成為皇帝。但是,王莽究竟有多少治國的理想,有多少理政的本事,并沒有政績給予證明。如果說有什么理想信念,也只能是《周禮》等古書中的烏托邦。
即使是虛幻的理想,王莽實踐起來,過于簡單粗暴。他以為頒發詔令就可以治國,把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國家層面,然后就不停地發布改革法令,隨意性太強,措施缺乏操作性,朝令夕改,讓人無所適從。
王莽改革的導向,似乎是為了抑制豪強,實際卻是以抑制豪強兼并的名義,為中央政府聚斂財富,普通老百姓并沒有從王莽的改革中得到真正的實惠。比如,王莽指責漢朝田稅太低,三十稅一,使大土地者多占低稅的便宜,這個話并沒有錯。但是,改革后變成十稅一,即便對豪強多征稅了,普通農民的負擔也增加了三倍。又如六筦中,過去對于名山大澤的開發及其產品,也有課稅,王莽卻進一步規定,凡從事魚鱉、鳥獸捕撈活動和從事畜牧業的底層民眾,也要像家庭副業產品者一樣,繳納所得稅(“貢”),稅率為其所得額的十分之一。從事這些經營活動的都是升斗小民,一概必須交稅,使其生活更為艱難!如果隱瞞不向政府申報或者申報不實的,產品沒收,罰服勞役一年。這哪里是為民謀福,分明是不擇手段地刻剝百姓。
王莽的改革,不僅不能解決社會矛盾,還加劇了社會矛盾;既動了上層貴族豪強的蛋糕,又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負擔;承諾的好處如王田制,由于官吏的怠工和腐敗,可以斷定得不到切實實行;增加的賦稅負擔,卻讓普通民眾的生活如雪上加霜。一次次的貨幣改革,一次次的貨幣貶值,輕率廢除已經施行的貨幣,實際上每次都是剝奪了人們既有的財富,使中產之家也瀕臨破產。“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①新莽王朝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撇開王莽個人品行和改革動機不談,王莽改革的敗局,至少給我們如下反思:改革的目標設計是否合理?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否足夠?改革的措施是否切合實際?改革的部署是否有序而堅定?改革的成果是否能讓多數民眾分享?都是決定改革成敗的重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