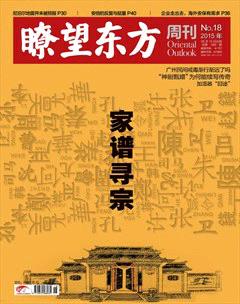重建家風的坐標
山旭
家譜尋宗
中國人的完美世界從來不在天國,而在家庭。
如辜鴻銘所稱,在中國“真正與別的國家的教會宗教里的教會相應的真正組織——是家庭”,而且“在中國的國家信仰里面,讓人、讓中國的普通大眾遵守道德行為準則的啟示之源,真正的動力是‘對父母的愛。基督教教會宗教的教會,說:‘愛基督。”
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中說:“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義,始可與言吾國中古文化史也。”
類似的意思,在國家領導人的話語體系中,則表述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雖然歷經革命與立新,但即使在傳統文化最低谷的時期,對于家庭和家風的信仰仍存在于中國人的內心底層。
如今,在物質極大豐富之后,對家庭、家族的信仰,作為中國人獨一無二的精神特征而再度得以申張和發揚,并彰顯為民族的文化特質之一。
然而傳統中國社會以倫理和家風——它在很多時候直接表現為家族法——維系,其社會基礎是宗族式家庭。如學者余世存所形容,當下中國的“家”已經從傳統四世同堂演變成二世或一世家庭。
至于陳寅恪所稱贊的“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于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之因襲”,第一,當今世界已無“士族”“家族”根基,其次,經過數十年西學東漸、國家變化,也很難有“學業之因襲”。
于今日中國生成現代家風,既是情非得已,亦是情勢使然。
現代家風,必然無法脫離中國傳統的家族、家風。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復蘇的一個表現,就是漸漸地重新燃起了對家族的認同。千百萬人奔波于華夏各地,聯絡宗親。
這種文化認同,是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之外建立的新身份認同。它又與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鏈接,完整構成了一個中國人自大而小、由國到家的坐標系。
在中國,沒有一部家譜不會牽連國運興衰、不以大時代變遷為背景;也沒有一部正在編修的家譜,會忽略祖先在國運中的角色。
中國已不太可能再回到以龐大家族為基礎的社會,中國人重建家風之路也還很漫長——僅僅20多年前,作為家族、家風基礎的家譜,還是一種禁忌。
及至今天,中國人對于家譜的認識仍然模糊。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它可能還是富庶者或名門望族的專享。
而尋根者卻似乎已在追尋與恢復家譜的艱難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不過,現代國家畢竟將法律和科學、公共教育等作為治理基礎,家族與家風則歸結至“家教”范疇,成為現代國家國民養成的重要途徑。至于在傳統文化中向無多言的“自由”、“平等”等觀點,則需要在現代家風的形成過程中被更多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