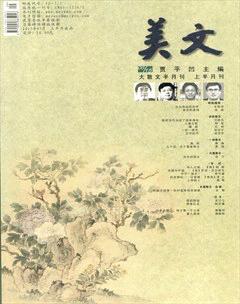毛姆與中國 (下)
羅賓·吉爾班克

整天我都在船上順流而下。就是沿這條河,張騫曾逆流而上去尋找其源頭。航行多日到一地,見女子織錦,男人役牛。他問這是什么地方,女子把她的梭子給他,并告訴他回去把梭子讓筮師嚴君平一看便知。他照做了,筮師馬上認出此乃織女之物,還說在張騫拿到梭子的那一天和那一刻,他注意到有客星犯牛郎星和織女星 。是故,張騫知道自己是到了銀河的深處……
這時,我突然感到,面前茫然觸動我心扉的就是我尋找的浪漫。此感有別于它,乃藝術引發之激情,但此生我說不清,也道不明,緣何會有這樣的奇感。
——節選自《在中國屏風上·浪漫》 毛姆 著 1922年
顯而易見,世事可憐,此女來中國是為嫁人。然而更悲催的是通商口岸的所有單身漢對此心知肚明。她身材高大,體型欠雅,手大腳大鼻子大。她的五官確實大矣,但那雙藍眼睛到是美目盼兮。或許對此她亦有那么點自知自明。而立之年的她金發碧眼,白天穿上得體的靴子、短裙,戴上寬邊帽,還是蠻有風韻的。但到了晚上,當她為了襯托自己的藍眼睛,穿上不知哪個土裁縫照著時裝圖為她剪裁的藍色絲綢連衣裙,試圖展現自己的嫵媚時,卻讓人覺得大煞風景。她對所有的單身男人百依百順。當有人談起打獵時,她顯得興致勃勃;當有人說起運輸茶葉時,她也聽得很入迷。當人們談論下周的賽馬時,她像個小姑娘一樣拍巴掌。她死纏著一位年輕的美國人跳舞,讓人家答應帶她去看棒球賽。但實際上跳舞并非她的唯一愛好(再好的事久了也會膩味),當她和一家大公司的代辦,一個單身老男人在一起時,她就只喜歡打高爾夫了。她樂意讓一個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的小伙子教她打臺球,同時也把活泛的心思花在那個和她談論銀子的銀行經理身上。她對中國人興趣不大,因為這個話題在她廝混的圈子里不吃香。但作為一個女人,她會情不自禁地為中國女人的遭遇鳴不平。
“大家知道,她們對自己的婚姻大事說不上話,”她解釋道,“一切都是媒妁之言,男人在婚前甚至沒見過姑娘的面,諸如浪漫等情懷無從談起。至于愛情……”
她說不下去了。她本性善良至極,那些單身漢不論老少,娶她都會得到一位賢妻,而她對此比誰都清楚。
——節選自《在中國屏風上·最后的機會》 毛姆 著 1922年
1920年冬,在沿長江旅行時,毛姆迷上了一個地方,那兒的古老與神奇交織在一起,密不可分。他第二次去印度的時候經過四川的這個地方,就在那兒,據說博望侯張騫乘槎泛舟不知不覺地走出了地球,來到了把牛郎和織女隔開的銀河。牛郎和織女夫妻當時在天空的位置就是西方天文學家眼中的牛郎星和織女星。毛姆對此異事完全可以不屑一顧,這可能是向導或翻譯講給他的。但他沒有,而是離開眾人回到船艙,獨自沉思這個神秘的故事。夜氣襲胸,作者的腦海里閃現出的是世界上自己游歷過的地方。在這些地方,“強烈的浪漫氣息”讓人陶醉。再次走出艙門,物是人非,心境全無。他獨立舟頭,“就像一個把蝴蝶撕碎,要找出美它在何處的人”。
《在中國屏風上》,這本毛姆有關中國的微型散文集,里面類似這種純凈、如過往煙云的寧靜瞬間頗多。對于作者而言,有些地方體現的是靈魂的升華,其碩果乃文學作品。這在猶太基督教文化中稱之為“靈地”,這里人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仿佛貼得很近,合二為一,給人一種超自然的頓悟。毛姆的高度認識富有浪漫氣息,在本質上和宗教不同。其筆端帶有一種憂郁的回潮,正如《最后的機會》一文所示,當說到外國僑民不得不玩婚姻游戲時,作者的心情跌到了最低谷。與牛郎和織女那純潔的神話戀情相比,這位可憐的女同胞沉湎于自娛,徒想釣到一位理想的外國人為夫。她的舉止甚至沒有莎士比亞筆下“黑美人”的樸實魅力。莎翁的描述是:
我也承認,我的情人舉手投足之間,
沒一點兒讓我想起天仙下凡。
——節選自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130首
從英國移植過來的東西平淡無奇,清湯寡味。若言中國人妻乃婚姻之奴隸,那這位英國女士就更加可悲,其乃前程的奴隸。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談到過毛姆在《蘇伊士之東》中對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描述。我認為在抨擊這些在異國他鄉定居者的心胸狹隘和裝腔作勢時,毛姆的主要武器是冷嘲熱諷。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對當地中國人的處理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人們不清楚他是在延續流行的東方種族原型,還是在狡猾地重構他們。他先前劇作中的瑕疵在《華麗的面紗》中依然如舊,當然這部小說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在這部作品里,他重復了《蘇伊士之東》中的三角戀情節,不過是加了些《在中國屏風上》的猛料而已。通過對這部小說和更多散文的通讀,拙作將致力于解析毛姆如何在自己的作品里把傳統文化元素與哲學糅合在一起,以及這對他的英倫創作風格有何影響。
從本質上講,《華麗的面紗》是一個有關感情錯位和復仇的故事,小說的結局完全出人意料。小說曾三次被改編為電影,每一次改編都明顯有其時代特征。最早的一部電影主演是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影片上映時距民國時代的結束還有幾年時間,影片富有東方奇景的色彩。銀幕上的兩位戀人在一座廟前約會,廟里盛大的舞龍儀式演得很是到位。但毛姆本人曾錯失機會沒有看到舞龍,他也不善于趕時髦用文字來描述畫面。二戰后的重拍(1957年)似乎更加謹慎,對兩位有私情的主人公的塑造比原作更加苛刻。出現這種道德意識上的約束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那個時候,殖民地香港已經處于共產黨領地的包圍之中,制片商不希望讓自己的對手覺得香港這塊飛地是個滋生淫亂的溫床。第三次改編是在2006年,填補了毛姆作品中的許多不足和空白。通過把故事背景從香港移到上海,影片展示出全中國人的民族躁動日益強烈,其寓意乃任何卷入中國內部事務的外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有殖民干預意向。至于影片是否有那么點超越了原作還是有爭議的。
《華麗的面紗》鋪設直白,將近而立之年的姬蒂·賈斯丁,迫于在社會上攀爬的母親的壓力,加之羞于妹妹已有了未婚夫,不得不接受了細菌學家沃特·費恩的求婚。雖然她無心于丈夫的愛,但還是陪他到香港來履職。在香港,她和風流成性的副領事查理·唐森(Charlie Townsend)鬧出了婚外戀。沃特知道她和別人上床,他給她的最后通牒是要么離婚嫁給唐森,要么隨他處置。而她太天真,從未想到自己的情人怕個人仕途毀于流言蜚語,不久就拋棄了她。她得到的“懲罰”是跟著沃特去了內陸遠方的梅德福鎮,那里霍亂流行,她丈夫受命前去救助。
事后想來,可悲的姬蒂似乎和《在中國屏風上·最后的機會》一文中那位剩女的故事如出一轍。毛姆描寫的是當時比較普遍的老處女現象。那些無法在英國找到配偶的人便不得不到英國的殖民地去尋親了。殖民地的外交工作崗位實在安全,僑民生活圈的婚姻生活讓人感到知足。作家E·M·福斯特在《印度之旅》中有同樣的描寫。他說上了年紀的穆爾太太帶著阿德拉·奎斯提德到次大陸去,就是為了看看她是否和其在當地為官的兒子能否婚配。當年英國中產階級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娶不了英國的,就娶香港的”。就姬蒂本人來說,她很清楚那兒的男人都是二流貨,要是在倫敦,她社交中來往的男人永遠也不值得被邀請參加她母親的晚會。
更為切實的是,這部小說里有濃郁的以前發表的短篇小說集里的味道。一本《在中國屏風上》在手,讀來就如同是在看描寫外國人對中國內陸有興趣的地方志。困在霍亂流行的地方,姬蒂來往的外國朋友只有兩個,一個是法國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女,一個是古怪的英國領事。毛姆先生贊揚過天主教修女們的堅韌(見《在中國屏風上·陌生人》一文),她們和自己的同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不同,選擇長年在臟亂的中國內地城市安家,而不是在酷暑到來時就躲進涼爽的山里。基督教新教鼓勵傳教士多生兒育女,這樣孩子的需求也就成了他們過幾年回歐洲休假的理由之一(見《在中國屏風上·上帝的仆人》和《在中國屏風上·恐懼》)。而天主教傳教士信奉獨身,其生涯有可能再無踏上故土的機會。毛姆描繪的法國院長嬤嬤(見《在中國屏風上·修女》一文),就是放棄了在比利牛斯的舒適生活來到了中國。顯而易見,梅德福鎮出身高貴的修道院院長就帶有這位法國院長嬤嬤的影子。
這些修女意志堅定,甚至寧愿面對霍亂帶來的死亡,也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傳教使命。毛姆對此觀察很仔細,通過一位修女的話,他注意到修道院孤兒院里做針線活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被人遺棄的。家里人遺棄她們因為養不過來,或者就因為她們是女孩子。她們在這里接受教育,信奉天主教,法語和漢語一樣流利。
這種介入可以被解釋為是一種殖民行為,因為這些遭遺棄的孩子被灌輸的是外國人帶到中國來的價值觀。《華麗的面紗》制作人在2006年的重拍中則把這演繹得更細致。當姬蒂·范尼在家里的餐桌上贊揚修女們無私的純潔精神時,沃特的反應顯得很激烈。他指責修女是在把“這些孤兒培養為小天主教徒”,其言外之意是說,孤兒對獲救的感恩最終將會轉化為對上帝仁愛的感恩。毛姆的批評從不這樣直截了當,但有兩個因素讓電影腳本覺得有必要加上這一筆。首先,這部電影的后臺是中國的官方,毫無疑問官方期望通過美輪美奐的鏡頭,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影片的拍攝地桂林去觀光。另外,為了迎合中國的標準歷史觀點,有必要想法巧妙地認可中國在“百年屈辱”時被奴役的處境。除此之外,毛姆的作品充斥著微妙的旁敲側擊,草草讀之則渾然不覺。電影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媒介,為了讓觀眾參透,必須選擇更大膽的色覺沖擊。
電影中被刪掉的(理由很明顯,雖然原作中有引用)是毛姆在旅行中見到的最具恐怖聯想的“棄嬰塔”,人們會把不想要的孩子扔到這里。在《在中國屏風上·小城風景》一文中,毛姆曾描述說洞里飄出一股令人“作嘔的怪味”,他還提到這些西班牙修女花錢讓人把孩子送到教堂,而不是拋進那死亡的深淵。毛姆厭惡的景象在別的外國人筆下也有流露。在1900年出版的《漂泊在中國》一書中,康斯坦絲·戈登·庫明女士(Constance Gordon-Cumming)描述了她造訪寧波時的情景:“(玫瑰和金銀花的)淡淡香味,掩不住到處襲人的惡臭,臭味污染了傍晚和風的清新”。她的游記提到了孩子被遺棄,埋在在塔外面,有的甚至被野狗撕咬。
漢學家瞿理斯 (Herbert Giles)不提倡弒嬰,他對此事的看法是,外國人描述這些軼事有點想制造轟動效應。在第一個例子中,戈登·庫明和其他人的描述并非是人們普遍接受的一個常態。在食物稀少的地方,孩子多的人家會把孩子讓家族其他成員或鄰居收養。他在寧波附近住了四年,得知的情形是這些棄嬰塔有人定時清理,所有被發現的遺骸都得到妥善的掩埋。他就從未聽說過有過路的人同情剛剛被遺棄的嬰兒,并帶回家撫養。
瞿理斯在演講中涉及此話題,他說在英國人們當然從未聽說過棄嬰,另當別論的只有罪犯。他沒有提到相關的法律條文,但在違反《人身保護法》(1861年)第二十七條(此法到現在未廢除)規定:任何人遺棄兩歲以下的孩子就是犯罪,最高懲處為五年監禁。回到那個時候,由于害怕被起訴,英國父母會把自己養不起的孩子送進無人監管的孤兒院,或是送給養母,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養母成了“育嬰婦”,個個心腸歹毒,收養沒人要的孩子都收費,然后又故意不管不問,致孩子于死地,以便有利可圖。時代變了,現在英國的媽媽幾乎沒有人因為遺棄孩子而受到起訴,舊法規的影響明顯還在起作用。2014年初,廣東地方政府設立了“棄嬰保護艙”(俗稱“棄嬰島”),為那些出生時有殘疾,或出生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嬰兒提供庇護。類似的東西絕不會在英國出現,因為1861年的法律依舊有效。
回到《華麗的面紗》,范尼女士不喜歡在中國不衛生和不體面的生活,但這并不妨礙她協助修女們的人道主義工作。和這些行善的人相反,維廷頓先生則相對做出一副冷漠的神態。雖然他不失同情心,但卻刻意于在自己的官位上不越雷池,裝著諳熟中國傳統文化,他給姬蒂解釋“道”就是:
道乃道行,是眾生永恒之道,但道非人為,自身為道。道是有,道是無。道演化萬物,萬物遵循道,最終歸于道。……道法是無欲無求,順其自然。
——節選自《華麗的面紗》第十章
說完這番話后是一陣自貶式的干笑,他的話雖然語意含混,但“在我喝了半打威士忌酒看星星時”倒也說得過去。盡管如此,要是這番話的確代表他的個人信條,這似乎可以解釋這個怪人為什么會在一個相對孤獨的地方存活了這么久。通過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學會了(不像《華麗的面紗》和《在中國屏風上》中的外國人)從不失望,也不動怒。即便是在小說寫到悲情的高峰,就是費恩醫生和剛剛身懷六甲的妻子達到了互信互愛時,他卻染上了霍亂,但悲傷沒有擊倒他。
不知毛姆有沒有意識到,他手頭就有密碼,可以解讀為什么除了維廷頓,大多數外國人都努力想在中國有一種家的感覺。一天午后在鄉下,精心讀瞿理斯 (Herbert Giles)翻譯的莊子,遺憾的是他感到不受啟發反受其擾:
……他的書是好讀物,尤其適合在雨天閑讀,常讓人不經意間有所觸動,遐思萬千。然眼下的想法猶如漲潮時拍岸的波浪,緩緩浸入人的意識,吸引你抵御古代莊子的思想。盡管你欲悠閑,但還是坐在了桌前……駕輕就熟,下筆如行云流水。活著真好!
——節選自《在中國屏風上·雨》 毛姆 著1922年
再往前三十年,當莊子剛被譯為英文時,奧斯卡·王爾德就提醒人們說,此書中的哲學思想將會給英國社會帶來沖擊波。這位古代哲人強調的是“無為而治,順應自然”,其思想與當今政客和說教者的理念背道而馳,他寫道:
顯然,莊子是個危險分子,在他離世兩千年后用英文出版其作品乃不成熟之舉,可能會給很多享有名望和勤奮刻苦的人帶來痛苦。修身養性也許真的是莊子的人生目的,是其哲學體系的根基,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想所需。當今世界,大多數人過于熱衷教化他人,實際上無暇修身。但這樣講是否明智呢?在我看來,要是我們一旦承認莊子顛覆性觀點的力量,我們便早該審視一下我們自命不凡的國民習性了。人一旦做了蠢事,唯一的慰藉便是對此事的自吹自擂。
——節選自奧斯卡·王爾德《中國圣賢莊子》
身為愛爾蘭人的奧斯卡·王爾德總是拿英國文化開玩笑。英國人的天性是能看到其他民族的短處,滿腦子的帝國霸權思想。盡管毛姆本人與英國的統治階級走得很近,但他流露出自己喜歡這樣的批評。《在中國屏風上》所顯出的主要技巧用一句老話來說,就是“多行不義必自斃”。殖民者過分專心于教化當地的中國人,但卻全然忽視了自身的毛病,使其膨脹得可怕。梅德福鎮的修女們內心有種自我滿足感,因為她們清楚修道院是自己徒手建起來的,幾乎不需要捐款。2006年版的電影制片人覺得應當沃特·范尼表現出一種反殖民意識,從而保留住了原作人物的自負形象。他責備當地人缺少感恩,對自己把神奇的西藥帶給他們沒有任何表示。但他卻一直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踐踏他們根深蒂固的信念,甚至是在給當地人灌輸恐懼。如為了水源不被污染,讓人家搬祖墳;要人們放棄傳統的挺尸祭奠,甚至讓全副武裝的國民黨士兵強迫人死后要立即埋葬。
除此之外,莊子給人的啟發就在毛姆的手頭,但他卻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就是能讓自己走出殖民怪圈的利器。毛姆書寫中國最有趣的一篇文章是《哲學家》,文中的對象是文弱但口出狂言的辜鴻銘,辜當時住在成都一處彌漫鴉片味的小屋里。毛姆只是聽說過他的名氣,要是毛姆先前知道辜鴻銘對他的譏刺,他就不會那么急著和辜鴻銘見面了。幾乎從一開始,辜鴻銘就認為來訪的毛姆不過是文壇的一個暴發戶,而他則是高貴的儒家學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他最讓人沮喪的話是“當你們還在居山洞,穿獸皮時,我們就已經是文明開化的民族了”。這句不祥的言論預示著后邊的話更厲害:
當黃種人也可以造出跟白人同樣精良的槍炮并射擊的同樣準確時,那你們的優勢何在?你們求助于機關槍,可最終你們將在槍口下接受審判。
——節選《在中國屏風上·哲學家》 毛姆 著1922年
中國對《在中國屏風上》的批評文章不多,其中一篇是宋淇寫的(Stephen C. Soong)。他的指責比較溫和,說尊稱一位很多中國人覺得讓人尷尬的清朝孝子賢孫為“哲學家”時應當謹慎一些(見宋淇著《我的父親與毛姆》)。我相信毛姆用這個尊稱部分原因是為了不讓辜先生難看,讓人們覺得他是整個清朝的替罪羊。在英國,稱人為“哲學家”有時候是一種挖苦的恭維。被冠于該頭銜意味著這個人的思維過于抽象,難以在當今世界茍活。或者是說雖然此人相信不切實際的空話,但卻有一定的獨到見解。
過了近乎一個世紀,辜鴻銘當時的預言沒錯。中國向西方學習,在全球的力量穩固崛起——但不像辜鴻銘想得那樣是在軍事上,而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制造和出口商品。比如,中國不再需要當年沃特·范尼進口的藥物,因為就西藥來講,中國一直在削弱其國際市場,同時卻在保護自己的傳統醫學。這些成就并不是靠恢復了辜鴻銘夢想中以前大清朝的體制,從這一點上講,老先生是落伍了。
說到底,人們會注意到毛姆和辜大師之間有奇異的相似之處。辜鴻銘盲目效忠大清,對其弊病視而不見,以至于犧牲了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可信度,留給自己的是一個凄慘的晚年。而毛姆則是毫不留情地痛斥自己的同胞,以至于永遠也不清楚自己的地位。他無法成為道德權威的化身,因為他不過是這塊人人為家的土地上的一個過客。另外,他對中國文化的接觸和駕馭都是很膚淺的,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一種機智的嘗試方法,揭露自己同胞扭曲的自我觀念。只要看一看他對辜鴻銘的警告反應,我們就可以看出毛姆思想上的困惑。在《蘇伊士之東》中,毛姆借博學但卻可憎的李泰成之口,一字一句地說出了自己的英國殖民主義觀點。說到底,像他那樣的英國人無力反擊辜鴻銘抨擊,只能墮落到在文字上惡搞其觀點,也許是嘲笑辜鴻銘的妙論。但在我心里,這不過顯示出的是錯位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