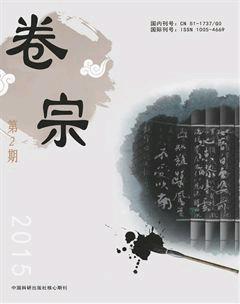談大眾媒體與文學傳播的關系
梁雪漫
媒體對文學的重要性不是一個新問題。因為表達與傳播才使文學的生命趨于完整。古代文學注重私趣,以寫作者之間的相互唱和為主要傳播機制,詩賦往還被認為是一種溝通情義交流心聲的雅事。從傳播學來說,這應該屬于人際傳播的范疇。大眾媒體興起以后,中國文學便逐漸形成了以媒體為軸心的運行機制。晚清的報刊之于小說的繁榮、民初四大副刊與新文學、現代期刊業與民間出版的興盛之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媒體的策動常常讓文壇風聲水起,也使發表成為與文學表達相伴生的重要旨趣,使作家的創作得以成為公共性產品,即敞開了與社會的聯系,近而使寫作作為一種職業成為可能。
許多現代作家1949年前一直保持著高產,有的還達到了他們文學創作的最高水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盡管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并不寬松,但現代出版制度仍在有效地運轉,文學期刊、圖書的出版流通支撐著作家的個體創作。1949年以后,以依托市場、自主經營為基本特點的現代出版制度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以強烈管制為基本特點的出版制度所取代,“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性的現象,說它重要,是基本上結束了晚清以來雜志和報紙副刊為中心的文學流派、文學社團的組織方式,文學活動被納入高度一體化的政治體制中,不單是寫什么和怎么寫要納入嚴格而統一的規范,怎么刊登也有明確的規約,導致文學傳播的空間極度萎縮,媒體自己的個性和選擇權也基本喪失,除了“同中央保持一致、”“接受和服從黨的領導”等政治原則性規定以外媒體的重要舉動如改版和社論等重要稿件的編發等都有嚴格的審批和把關制度。這時期媒體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對文藝政策亦步亦趨的服從和機械的執行上,文學傳播的運籌、規劃和操作也主要聽命于宣傳部門或文聯、作家協會這樣的文學機構。文聯和作協作為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專事文藝管理的機構,主要職能一是通過制定文藝政策或對關系到文藝政策問題的闡釋,框定文藝活動的政治方向;二是對文學思潮、文學創作進行調控,規劃文學藝術的生產;三是領導和組織各類文學活動。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學具有相當濃厚的組織傳播色彩。80年代政治和媒體的關系逐漸微妙起來,在總體訴求上,二者是相契合的,其中也不斷有媒體試圖以文學傳播彰顯個性,以至有的媒體最后因激烈的出位而走向終途。
大眾媒體時代的文學傳播,情況開始變得非常復雜。一是傳統與新興媒體此消彼長;二是各種媒體內容格局的變動均蘊藏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三是不同媒體的功能定位也時有變化,這種不確定性和變化對文學傳播的影響很大。據新聞出版署2003年5月公布的數據,2002年全國共出版報紙種數2137種;期刊總數9029種:廣播電臺306家;電視臺360家;廣播電視臺1300家:廣播人口覆蓋率94.54%。至2002年底我國上網計算機數量為2083萬臺,網站數量達到37萬個,上網用戶總人數5910萬人,占全球網民的9%。在這么大規模的傳播中,去發現文學的流量是困難的。要認清文學在各種媒體中的處境和媒體傳播文學的動力機制,必須對媒體與經典權力的關系變化保持清醒。首先,在實行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大背景下,政治權力對媒體權利開始有限的讓渡,從更大范圍來看,媒體己不再是政治權力的工具或附庸,其自身己成長為具有強大力量的體制性機構,當然這也可以從政治控鴛方式的變化來理解。二是權力的媒介與媒介的權力互相借重的過程中,媒體不僅成功地將政治權力轉化為自身的權力而且成功地成為對媒體自身的資本及文化資本的累積和展示。三是媒體既然是被鼓勵在發揮意識形態功能的同時,注重經濟效益,那它的行為的利潤趨向,就成了很自然的事,從而帶來權力資本與文化資本便捷又合法的轉化,這為大眾媒體在當今社會中的種種表現所印證。
在這種背景下、文學機構對文學生產和傳播的調控功能很大一部分已為媒體所取代,媒體從單純刊登作品的載體或傳達意義的工具又一次走到文學活動的中心。為公眾架構文學形象和有關文學的想象,同時也給出文學在整個文化和社會空間的位置,是報紙、電視作為大眾媒體通過新聞設置議題來制導文學傳播的功能表現。報紙可以分為黨報和市場化報紙,前者主要以引導輿論為角色定位;后者在把握好宏觀導向的前提下,在傳播理念上,更趨向于新聞本位,還由于它主靠自費市場發行,服務受眾的意識相對來說要強許多。報刊上的文學狀況真實地反映了整個社會對文學的態度,也即是說,文學的整體狀況可以從當時的報刊上獲得基本印象。兩類報紙在選取新聞的標準上有區別,但一般均以全面客觀報道社會生活的最新變動,提供讀者需求的各類信息為追求。
隨著報業規模的膨脹和競爭的加劇,開始了資訊過剩時代,人們對資訊由量的需求轉為對品質的挑剔,從空泛的可讀性轉而要求必讀性。在這種環境下,文學怎樣才會轉化為能吸引眼球的新聞資源呢?通過對近幾年報紙版面變動的考察可以發現,傳統的文學副刊版面急劇萎縮,在打造主流媒體、增加新聞版面的編輯方針下,曾設立過文學版面的都市報、晚報紛紛改弦易轍,首當其沖面臨撤換的就是純文學副刊版面。許多報紙或將文學副刊改為娛樂版或綜合性的文化新聞版,或者改為專登隨筆的專版。在這類報紙的新聞版中,文學信息也不受青睞,以新聞價值標準評判,文學寫作的專業化取代了公共性,而且文學圈中被大眾熟知的作家不多,與娛樂圈內的明星薈萃、萬眾矚目無法相提并論。文學信息在主流報紙的新聞版同樣難得一見。為了進一步證實這種印象,我們對2003年《中國青年報》和2004年一月、二月份《齊魯晚報》刊載文學新聞的情況進行分析。
《中國青年報》的主管單位是團中央,是國家級“八大報”之一,屬嚴肅的主流媒體。80年代它曾一度是新聞改革的先鋒,新聞報道以深度分析和理性思考見長。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張周末就誕生在這里,此后引發的周末大潮成了社會精神生活的重要動向。該報的文學報道主要集中在每周兩期的文化版中,而該版的頭條無疑是報紙作為傳播者設置的議題,在2003年共104期的頭條中,有近1/3是從文化角度觀照社會問題,比如環保、舊城改造等,以彰顯文化對現實的建構作用;其他報道則集中在文化藝術領域,文學報道只有15篇,內容有低齡寫作、文學大獎、網絡文學、閱讀時尚、著名作家訪談、小說圖文改裝、作家退會等,報道均以新近發生的事件或比較引人注目的文壇現象為由頭,而重點在于傳達對事件和現象的理性認知。在報道手法上講究全面客觀均衡,如常引征具有不同觀點的批評家或傳媒專家的意見。從傳播技巧的角度來說,中青報的文學報道把捕捉“看點”與傳達嚴肅的專業思考的結合點找得較為準確。在穩健地把握輿論導向的同時又傳達出有個性的觀點,這是它所追求的傳播風格。
《齊魯晚報》是省級大眾日報報業集團旗下的一張子報,是一張較為典型的市場化報紙。該報除設有刊發有泛文學性的生活隨感專版外,文學新聞一般出現在娛樂版組的版面上。2004年1月份共有三則與文學有關的新聞,二則為極短的作家到濟南簽名售書的消息,另一則為《2004年文學劇,吸引高素質觀眾》,介紹幾部由小說改編的新拍影視劇。需要說明的是,2004年春節就在1月份,是各家媒體為受眾精心準備“文化大餐”的時候,文化娛樂也以此時動靜最大,《齊魯晚報》上的此類報道連篇累犢,與文學的寂寂無聲形成巨大反差,當然,文學有無必要湊此熱鬧另當別論。2月份文學新聞的數量增加很多,一是山東籍著名詩人減克家的去世,它除了跟蹤式地發消息外,還策劃了一個專題,有子女追憶、學者緬懷等組成“世紀詩翁”的大標題非常有沖擊力。由一個突發事件深入開鑿出洋洋大觀的后續報道,這是市場化報紙充分利用新聞資源的慣常策略。另外還有兩篇較有篇幅的文章:《文學期刊舉步維艱》反映《山東文學》面臨財政斷奶的窘境;《文學不健康,導致受冷遇》則是一篇輕薄當代文學的“酷評”。這兩篇屬負面報道的范疇,由于讀者定位主要是市民大眾,《齊魯晚報》的文學報道與其他報道一樣,追求報道的快速及時,同時刻意用細節和語言煽情,以調動閱讀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