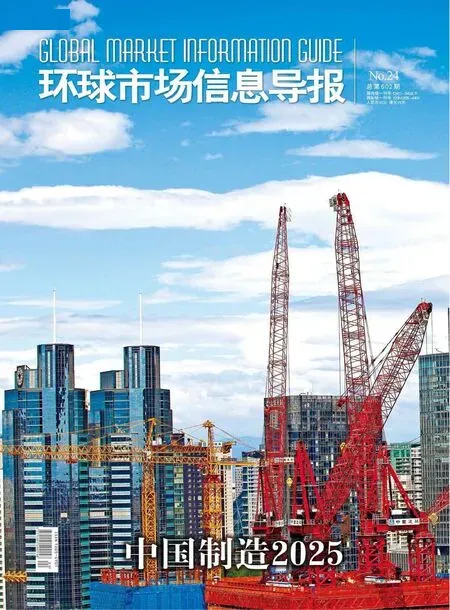世界浪潮:第四次工業革命
世界浪潮:第四次工業革命
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痛定思痛,紛紛拋出刺激實體經濟增長的國家戰略和計劃,美國制定了“再工業化”“制造業復興”“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德國拋出了“工業4.0”;日本開始實施“再興戰略”;韓國搞了“新增動力戰略”;法國也提出“新工業法國”等。

工業是德國經濟的瑰寶
“工業是德國經濟的瑰寶”,去年11月,德國經濟部長西格馬·加布里爾曾在國際場合這樣評價工業在德國經濟中地位的重要性。十多年前,當某些西方傳統工業國家歡呼進入“后工業時代”時,德國對工業的“忠實”還曾遭到某些美英政治人物的嘲笑。
但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寒意改變了這一切,對“后工業時代”的歡呼,變成了對“去工業化”幽靈的擔憂。歷史地看,作為工業現代化領域的“優等生”,德國任何一個“轉身”都不同程度地對世界經濟版圖產生過影響。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傳統工業強國紛紛推出“再工業化”戰略的當下,德國的“工業4.0”最為引人注目。
德國為何要推出“工業4.0”?為何在這波被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占得先機?德國的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2014年3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的幾組數據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從數據中可以看出,過去20多年來全球“工業足跡”發生了巨變。
在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上,西歐和北美從1991年的60%降為2011年的47%。其中,西歐從36%大幅降至25%,北美從24%微降為22%。同一時期,亞洲(不包括日本)、南美等新興經濟體從21%大幅升至40%。西歐主要經濟體中,德國是唯一一個制造業增加值在總經濟增加值中占比高且保持上升態勢的國家(從22%增加到23%),英國(從15%降為11%)、法國(從15%降為11%)、意大利(從20%降為16%),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德國史學者李工真教授認為,德國提出“工業4.0”概念,也是針對形勢的變化做出的戰略性調整。他說,德國工業化發展面臨的內外壓力是多方面的,但勞動力下降毫無疑問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簡單地說就是想把有限的勞動力用來制造機器人,由機器人來參與具體的生產,并利用自動化、信息化等高科技優勢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保持德國在制造業領域的領先優勢。

德國的經驗與啟示
歷史上德國一直都是“國家干預性功能”比較強的國家。德國是世界主要大國中最早搞壟斷的,即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由誰來組織呢,當然就是國家,這是德國歷史上曾經的發展戰略。但這種模式的結果是壟斷企業的自由放任化,導致了“攔路搶劫式的資本主義”。二戰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國家雖然也干預,但主要不是在經濟發展的具體環節中,而是在經濟、社會政策領域進行干預。
所以德國的企業“塊頭”都不大,90%以上是中小企業。不是德國人把企業做不大,而是政府不允許企業做太大。因為企業太大就會形成壟斷,而壟斷就會抑制創新。如果企業通過壟斷就能夠獲得利潤,就沒有了進行技術革新的動力。
李工真認為,在工業化轉型、升級方面,跟德國相比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就是壟斷。德國的工業能夠成功轉型、升級,最為關鍵的問題是有一個非常活躍的市場,在此前提下國家根據市場的發展及其內在的規律來不斷地往前推。德國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是教育做得比較好。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工人隊伍實力強大且比例合適,都得益于德國教育體制的完備以及教育的成功。
德國的年輕人愿意做工人,但中國的年輕人很多卻不愿意。在這一點上中德兩國差異明顯,這也是個比較“本質性”的問題。就工業化問題來說,年輕人愿意做工人這一點,就體現了德國的優勢。中國高校每年畢業的幾百萬人,如果都脫離生產第一線,當然會對工業轉型和升級產生負面影響。
當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人社會不需要時,就必然導致人才的浪費和流失。中國有2000多所高校,但工業化的發展卻沒有取得應該有的進步,原因也在于此。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法國“再工業化”效法德國
幾乎與中國發布“中國制造2025”規劃同時,法國經濟部也出臺新政,對原來的“再工業化”政策——“新工業法國”計劃進行大幅調整。“新工業法國II”出現一個值得關注的新動向:法國“再工業化”開始效法德國。
此次調整的主要目的在于優化布局。“新工業法國”計劃2013年推出時,曾梳理出智能汽車、機器人研發、新式高鐵等34個優先開發項目,近兩年來這一計劃雖取得一些成果,但廣撒“胡椒面”的弊端日益凸顯,優先項目太多,反而導致核心產業發展動能不足、方向不明。
此次調整后,法國“再工業化”的布局優化為“一個核心,九大支點”。一個核心,就是所謂的“未來工業”,主要內容是實現工業生產向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以生產工具的轉型升級帶動商業模式轉型。九大支點,包括新資源開發、可持續發展城市、環保汽車、網絡技術、新型醫藥等,一方面旨在為“未來工業”提供支撐,另一方面重在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新需求。
這一調整中,效法德國的痕跡十分明顯。首先,法國經濟部長馬克龍在官方文件中明確聲稱,法國未來工業的發展方向就是能夠與德國工業4.0平臺“自然對接”。法國經濟部也清楚寫下:與德國合作是法國工業升級的一大重點。在法國“再工業化”歷程中,這樣的表態并不多見。
其次,在具體操作上,法國政府也制定了學習德國的詳細路徑。根據經濟部計劃,2015年秋法國“未來工業”項目將正式和德國工業4.0項目建立合作關系;2016 年2月,法國將公布“未來工業”標準化戰略。對于“未來工業”的宣傳推廣,法國也將仿照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模式,舉辦類似的大型活動。
該如何看待法國“再工業化”效法德國這一新動向呢?第一,它折射出法國在工業領域奮起直追的決心。第二,從歐洲層面看,這一做法顯然將會加強法德在歐洲再工業化進程中的軸心作用,對于其他經濟體形成新的競爭力。第三,對于中國來說,既有機遇和啟發,也要正視壓力,加速發展。


戰略高地:美國“再工業化”
事實上,不只是中國,美國現在也把制造業視作必須占領的戰略高地。這既源于對金融危機前“去工業化”潮流的糾正,也源于制造業的價值被重新發現:制造業能夠幫助一個國家保持產業領先地位,同時提供實實在在的就業崗位。
在全美所有行業中,制造業提供的就業崗位排第4位,大約是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金融服務業的3倍。正是發現了制造業在政治和經濟上的乘數效應,2008年還在競選總統期間,奧巴馬就公布了自己的美國制造業復興計劃以吸引基數龐大的藍領投票者。之后,奧巴馬政府一直在細化并推進相關戰略,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建設有利于制造業復蘇的法律政策環境。7年來,美國出臺了帶資金的《美國復蘇和再投資法案》,其中7872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相當一部分撥給了制造業。此后,又出臺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先進制造伙伴計劃》《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制造創新國家網絡》計劃等。
其二,通過稅改、政策激勵等方式整頓國內市場,刺激美國制造業回流,吸引他國制造業進入。
其三,保證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美國聯邦實驗室和聯邦資助研發中心的研發量只占美國研發的10%左右,超過80%的研發是企業完成的。為保證美國的研發能力,美國政府極其重視為中小企業提供法律和公共服務幫助,而發達的金融服務業能夠敏銳發現有前景的中小企業,并提供融資機會。
美國政府重振制造業的努力,在許多時候受到政治運轉效率低下的制約。怎么提高再工業化的效率?很大程度上是靠市場自發秩序完成的。
以美國低端制造業為例,過去美國成衣品牌大多不掛“Made in USA”的標簽,這是因為根據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規定,“Made in USA”標簽的產品,幾乎所有的部件、制造過程及勞動力均須出自美國,這意味著極高的經營成本。但在美國政府改善制造業環境后,不僅通用汽車、蘋果、英特爾等高端制造業,許多制衣、造鞋、造玩具的低端制造業企業也開始回流。


美國推動“再工業化”的成效
之所以會出現制造業企業回流的這種趨勢,一方面是美國研究機構不斷發布中國等制造業大國的領先地位即將消失等信息,比如波士頓咨詢公司認為,中國制造業的領先優勢只能再保持5年。這些信息為美國制造業回流提供了參考依據。
另一方面,將業務遷回國內能夠節約管理和行政成本,還便于掌控產品質量,這消解了美國制造業在海外生產的部分成本優勢。許多美國企業還“聰明”地利用了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焦慮感,為“Made in USA”注入價值概念,包裝為良好設計、勞工待遇公平、能夠體現愛國精神的產物。比如,American Apparel的口號是“拒絕血汗工廠”,以此對沖低競爭力的損失。
美國推動再工業化的成效是比較顯著的。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也從2010年時的11%提高到了12%以上。不過,美國再工業化仍不穩定,最新數據是,美國6月Markit制造業PMI創20個月新低。這種脆弱性既源于勞資糾紛增加、制造業人才需要再度培養等因素,也源于美國制造業的資金缺口過大。為此,米爾肯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早就提出了引用公私合營的方式籌措資金等對策,但基于美國私有觀念的深入人心,難以實施。
總體來看,在政府對策層面,美國再工業化與中國制造2025規劃有許多相近之處;但在市場反應層面,有許多差異。這是因為雙方手中的制造業資源各有優劣。
專家指出,能否汲取美國去工業化的教訓,能否發揮中國自身的資源優勢,將對中國能否盡早在全球范圍內占領制造業高地起到決定性作用。

日本“再工業化”不甘示弱
德國率先推進“工業4.0”計劃,通過互聯網連接全球工廠,發起一次新的產業革命。盡管德國是這一計劃的先行者,但日本企業也不甘示弱,爭取后來居上。日前,三菱電機等約30家日本企業組建聯盟,共同探討工廠互聯的技術標準化,并爭取使其成為國際標準。
此次日本企業組成的聯盟的名稱為“產業價值鏈主導權(Industrial Value Chain Initiative,簡稱:IVI)”。成員包括三菱電機、富士通、日產汽車和松下等日本電子、信息、機械和汽車行業的主要企業。
聯盟的發起者是研究將IT技術應用于制造業的日本法政大學教授西岡靖之。聯盟的主要議題為工廠與工廠、設備與設備互聯的通信技術和安全技術的標準化。西岡靖之表示,雖然日本企業此前一直在推進自身和業界內企業相連接的網絡化,但此次將“跨越業界,構筑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工廠互聯機制”。
何謂“互聯工廠”?德國提出的目標是,不管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信息系統都實現聯網,從接到訂單開始,零部件采購、生產、配送、售后服務等所有工序爭取同時推進。這就是消除機械作業和庫存浪費的“終極制造業”的理想形態。利用大數據技術分析海量信息,由人工智能發出指示,達到生產效率最大化。
日本政府終于也開始行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擔任議長的“綜合科學技術與創新會議”在新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也加入了產官學聯合開發相關技術的內容。日本經產省也在《2015年版日本制造業白皮書》中用近1/4的頁面對工業4.0進行了分析,日本的“產業價值鏈主導權”也將為此提供援助。日本經產省的一名官員表示,“如果現在還不行動,在全球占有優勢的日本制造業可能會被反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