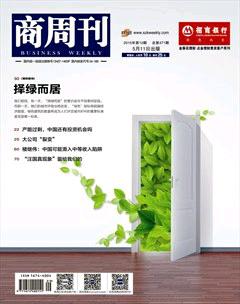湮滅無聞的失敗非洲探險
戴恩·肯尼迪
計劃這一使命的海軍官員約翰·巴洛說道,“探險任務當中再沒有比這次更加讓人悲憫、更加一敗涂地的了。”
英國在非洲探險的故事已經被講述了無數遍,我們的書架上堆滿了像大衛·利文斯通和亨利·莫頓·史丹利等著名探險家的傳記,探險書籍更是多如牛毛。無一例外,探險傳說的結局不是主人公成功回歸到“文明世界”,就是英勇就義于“最黑的非洲”。此類故事在維多利亞時期大受歡迎,到今天仍熱度不減。但是,一些重要的非洲探險卻很少得到關注,只因它們都以不體面的失敗告終,這使得“非洲在歐洲人面前不堪一擊”的說法變得不那么有說服力。因此,這些故事幾乎在歷史的記憶中煙消云散。但也同樣因此,這些故事值得重新拜讀。因為它們恰好幫助我們深入了解英國人在非洲希望達到怎樣的目的,以及為什么達成這種目的會面臨如此多挑戰。
1815年,拿破侖戰爭才剛剛結束,英國政府便派遣兩支人數眾多且資金充足的探險隊深入非洲內部。一支是海上探險隊,肩負的使命是溯剛果河航行,沖出大瀑布并盡最大可能抵達上游;另一支是遠征軍,要從幾內亞海灘向內陸行進,接觸非洲內陸國家并沿尼日爾河行駛至河口。當時歐洲仍對剛果河之源和尼日爾河之盡一無所知,一些地理學家甚至推測這兩條河實際是同一條,共享同一水體。于是他們開始希望兩支探險隊會在途中相遇。然而,非洲殘酷的現實完全擊碎了這種希望,讓當局者的投入血本無歸。
我們對海上探險隊的所知主要來源于總指揮詹姆斯·H·塔基和首席博物學家克里森·史密斯死后出版的航海日志,收錄于《一支探險隊記敘一八一六年在南非扎伊爾河(常稱剛果河)的探險》。正如當時許多海上探險一樣,這次探險被視作科學事業,探險隊出征是為了探尋更多自然界知識。皇家學會會長、科學探險主要倡導者約瑟芬·班克斯爵士參與策劃了探險:邀請哥本哈根大學校友、植物學家史密斯加入并建議博爾頓和瓦特設計建造專門護送探險隊至剛果河的蒸汽船。然而,這艘船最終沒能被建造出來。除了史密斯外,探險隊中還有來自英國皇家植物園的一位動物學家、一位地質學家、一位海洋生物學家和一名園丁。該書最后的附錄詳細列出了探險隊搜集的水文數據、自然標本和土著人信息,配上各種插圖,共同證明了探險隊在科學上的雄心壯志。
那么探險失敗的問題出在哪里呢?首先,一些非洲人對于探險隊表現出懷疑和抗拒,而探險隊卻需要這些人的配合。在剛果出海口最主要的港口博馬,奴隸商人公開稱(塔基一行人)的初衷不可能是好的,不應當允許過河。他們懷疑探險隊的目的是終結奴隸貿易。這一推測并非完全不合理,因為很多在西非海域航行的英國海軍巡邏艦正是持這一目的。塔基不得不做出保證不去阻止奴隸貿易或挑起戰爭。即便如此,奴隸貿易商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攔探險隊前進的步伐。此外,奴隸貿易還帶來了其他負面影響。探險隊的主要翻譯是當地一個恢復自由的奴隸,回到博馬與父親團聚。他陪伴探險隊繼續往河流上游前進,但他很快就扔下他們跑掉了,還帶走了四位來自博馬的行李搬運工。即便宣稱在科學上保持中立,探險隊還是不可避免地與奴隸貿易產生了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
致命的一擊則來自于當地令人生畏的疾病環境。當探險隊正費力地通過陸路繞過大瀑布時,隊員一個接一個地病倒了。于是,塔基的探險隊決定原路返回,但回程的道路要比從莫斯科撤退還艱險。他的日志變得越來越簡短,越來越不連貫,很快他便死去了。同樣獻出了生命的還有史密斯、他的自然學家團隊還有10多名軍官和船隊成員。所有人都是死于黃熱病。計劃這一使命的海軍官員約翰·巴洛說道,“探險任務當中再沒有比這次更加讓人悲憫、更加一敗涂地的了。”
(譯者:李燕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