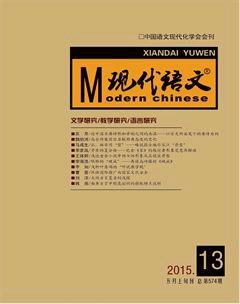空虛背后的個體狂歡
李正
摘 要:在充滿文化沖突的當下,王朔以“反叛者”的形象活躍在當代文壇,并以其諷刺的筆調批判并調侃著現實。然而在批判和調侃的背后,王朔在《頑主》中卻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失落與空虛,在反叛傳統的同時展現出強烈的精神困頓,同時將這種困頓體驗轉化成個體狂歡。
關鍵詞:空虛 語言 狂歡 精神困頓
王朔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當代文壇上掀起了一股大眾文化浪潮,他創作的一系列作品被大眾歸納和定性為“痞子文學”。在小說《頑主》中,王朔在批判與調侃的背后,通過塑造的“頑主”形象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空虛與失落,向讀者展示出強烈的精神困頓。
一、精神空虛下的個體狂歡
王朔筆下的“頑主”們既不像傳統小說中的主人公那樣為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努力,也沒有社會轉型時期青年們生不逢時的慨嘆和報國無門的焦慮,他們更多的是以一種反文化的姿態游離于急劇變化的現實生活當中。《頑主》中的三位主人公“于觀”“楊重”“馬清”聚到一起,偶然間組建起了著名的“三T”公司。他們為了發財的夢想,不惜代價助人成名、替人消災、代人赴約、替人受罵、幫人行孝。而在“三T”公司被關停之后,公司門口依然排起了長長的隊伍,有許多小市民還在要求頑主們為他們解決所謂的困難。通過這一看似荒誕的故事,王朔向讀者展示出強烈的反文化意識,這種意識在小說中“三T”公司幫作家成名這一段凸顯得尤為明顯:眾人期待的著名作家全部沒有到場,“三T”公司只好胡亂找人作替身,場面還甚是壯觀,一切都在“莊嚴”地進行著。但在這“莊嚴”的背后,我們看到了王朔對理性、崇高的嘲弄和消解。
在嘲弄和消解的同時,王朔在矛盾的情境中實現了“頑主”階層的個體狂歡。這種“狂歡”源于他心中的“文革”情結。王朔從小就很真切地接受了傳統的無產階級革命教育,并立志做一個革命事業的合格接班人。他生活在北京的部隊大院,屬于干部子弟。在那個特別看重階級出身的年代里,王朔備受重視。由于年齡小而沒有參加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但在瘋狂的“文革”氛圍中,他很自然地受到了現實的熏陶,心中充滿著“英雄夢”,渴望著革命斗爭。然而現實中的王朔只能與自己的小伙伴玩著想象中的革命游戲,對革命本身抱有的更多的是浪漫化的空想與想象。由于他未能參加實際的“革命”,所以,他只能以旁觀者的姿態樂觀、完美地理解革命,而這種革命卻是不切實際的、空想的革命。因此,由于王朔對革命有著純粹的完美想象,以至于在多年之后還對文革時代抱有一種懷念的感情。而當新時代來臨之時,王朔表現出極大的不適應,這種不適應就表現為精神上的失落與空虛。社會的革命氣氛消失了,他的精神卻找不到相應的寄托,只以書寫反叛正統,進行個體狂歡。
二、生活困頓下的言語囂張
王朔在退伍之時,由于在部隊里沒有提干,同時也沒有在恢復高考時考上大學,只好回鄉當了一名藥店業務員,然而他卻不甘這樣的命運,于是辭職經商,最后以失敗告終。對自己的這段經歷,他自己進行了這樣的總結:“我不是經商的命,倒賣東西沉不住氣。那陣兒所謂經商都是倒來倒去。這東西一倒進來,就操心,就急,怕咂在手里,就想趕緊給摔出去。每弄一次,精神上就受一次特大的刺激,承受不住。”[1]經商失敗后,王朔將精力投入到寫作上,而正是由于其內心充滿著兒時樹立的革命精神,王朔才敢于以激進、前衛的姿態來謀劃自己的寫作策略:要寫就寫最好賣的。在這位富有革命想象力的困頓者心中,好作品的標準不在于思想內容的豐富、藝術品質的高雅,而在于暢銷。因此,王朔在小說創作中經常使用“痞子話”“下流話”和“無聊話”,從而體現出“言語的囂張”。他塑造的人物多是主流之外的游手好閑之輩,這些人以顛覆傳統為能事,同時用自己的嬉笑怒罵盡情地解構崇高,并以流氓無賴自居,時常高喊著:“千萬別把我當人”“我是流氓我怕誰”“我不做流氓誰做流氓”等離經叛道的話語。如在《頑主》中,王朔這樣描寫馬青老婆對馬青的痛罵:“別回家了,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地和哥們兒神‘砍,沒準還能‘砍暈個把眼睛水汪汪的女學生,就象當初‘砍暈我一樣卑鄙的東西!你說你是什么鳥變的?人家有酒癮棋癮大煙癮,什么癮都說得過去,沒聽說象你這樣有‘砍癮的,往哪兒一坐就屁股發沉眼兒發光,抽水馬桶似的一拉就嘩嘩噴水,也不管認識不認識聽沒聽過,早知道有這特長,中蘇談判請你去得了。外頭跟個八哥似的,回家見我就沒詞兒,跟你多說一句話就煩。”從這里可以看出王朔語言的囂張特點。王朔小說《頑主》中那些自稱“頑主”或“俗人”的青年,從年齡上看都是文革中的“紅小兵”,內心或多或少對革命存有激情,向往著投身到反抗權威的革命行動中去。而他們卻自稱“俗人”,這意味著他們在謀求話語權上的優勢地位。當他們將阿Q式的自輕自賤運用到自己身上時,無形中就甩掉了沉重的道德負擔,從而在內心上變得輕松,在語言上變得蠻不講理,即使是任何極端的反常舉動也可能被“認定”為具有合理性。
生存困頓下的王朔是無奈的,他之所以選擇以囂張的言語姿態面向大眾,一方面與其反叛精神有關,而更大程度上是為了吸引大眾的關注,以達到商業炒作的經濟目的。因此,他絞盡腦汁去迎合大眾的口味,盡力揮灑著言語的“囂張”,并以此獲取觀眾的好感。
三、文化沖突下的個人調侃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催生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三種文化形態。這三種文化形態既相互沖突又相互融合,而每一種文化都試圖影響和同化其他文化,而每一種文化內部也存在著沖突。處于當代文化沖突中的王朔也備感矛盾。“頑主”們以流氓的形象出現,而骨子里卻非流氓。他們只是把自己調侃為“流氓”和“痞子”,并用這種方式來實現個體的狂歡。王朔自己曾經宣稱:“我的小說靠兩路活兒,一路是侃,一路是玩,我寫時不是手對著心,而是手對著紙,進入寫作狀態后,詞兒錚錚的往上冒。”[2]這就說明王朔的小說有兩種顯著的特色:一是“侃”,即調侃式的語言,二是“玩”即頑主形象。這種調侃的話語方式與正統的官方語言和精英獨白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王朔的調侃彰顯出他的玩世不恭。在《頑主》中,他成熟地運用反諷的手法,消解現世一切正統的價值標準。王朔自己沒有讀過大學,他筆下的主人公都是些無所事事、落拓不羈的市井小民,“頑主”們智商高而學歷低,外表灑脫而內心空虛,精力過人而無所作為。他們戲弄人生,嘲笑正統,矛頭往往指向一些知識分子,將知識分子身上一切傳統的價值觀撕裂。王朔在調侃“于觀”“楊重”“馬清”三人的阿Q式的優越感時,這樣寫道:“街上,三個人肆意沖撞著那些頭發整齊、褲線筆挺、郁郁寡歡的中年人,撞過去便一齊回頭盯著對方,只等對方稍一抱怨便預備圍上去朝臉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無一例外毫無反應,他們只一眼便明了自己的處境,高傲地仰起頭,面無表情地變線走開。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現使三人更有屢屢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覺。”這種調侃式的語言以獨特的審美形態展示了他的機智幽默、尖刻辛辣,從而使讀者于嬉笑怒罵中見識了生活中的荒唐事。這種表現方法的運用,拓展了新時期小說言語的技巧,傳承與發展了老舍那種獨具京味的諷刺風格。
注釋:
[1]王朔:《我是王朔》,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頁。
[2]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