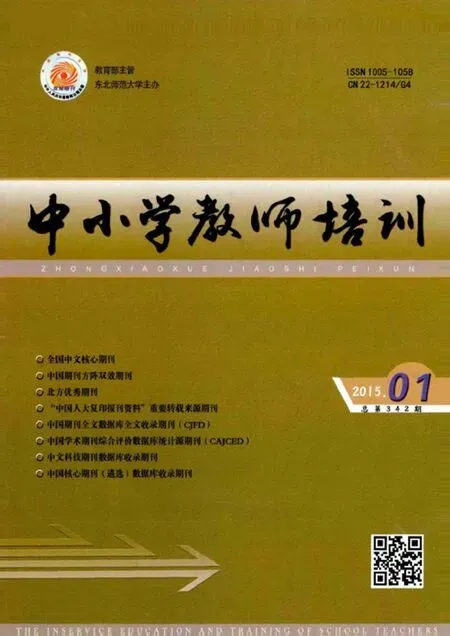從教育技術學的視角看教育要素
馬啟龍
(甘肅民族師范學院西北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甘肅合作747000)
一、引言
教育要素問題是教育學、教育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作者在教學及研究過程中發現:大多數《教育學》教材、專著只是分章探討了教師、學生、課程、教學內容等,從而間接回避了“教育要素”的論述,先后只有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編寫的《教育學》、鄭金洲教授著的《教育通論》、馮建軍教授主編的《現代教育學基礎》、石中英教授著的《教育學基礎》等著作中有過闡述;專門探討教育要素問題的論文也不多,作者通過檢索中國知網(CNKI)各數據庫發現,只有趙儒彬的《學習要素與教育要素——教育的四要素》、沈俊強的《再論“教育要素”——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背景下的重新解讀》、張國霖的《重構“教育要素”及其實踐意義》、馬前的《教育要素的矛盾視角分析》等幾篇;但在目前的幾本《教育傳播學》專著中均對教育傳播系統的要素有所論及。
總之,關于教育要素的多寡與具體內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三要素說”(即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響[1][2];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3][4];教師、學生和教材[5][6];教育者、學習者和教育資料[7];教育主體、教育內容和教育觀念[8])、“四要素說”(即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媒介和教育環境[9];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內容和教育手段[10];學習者、教育傳遞者、教育引導者和教育媒介[11];學習者、教育目的、教育者和教育影響[12])、“六要素說”(即教育主體、教育目標、教育內容、教育手段、教育環境和教育途徑[13])、“七要素說”(即教師、學生、語言、功課、教授、學習和試驗[14])。下面,作者作為一個教育技術學工作者,談談對教育要素問題的一些理解。
二、教育要素的構成分析
1.教育的定義
在考察教育要素問題時,首先必須明確教育的本質,否則連“教育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妄談教育要素是不合邏輯的。
中外教育史上,雖然對教育的界定各不相同,但廣義教育和狹義教育的雙重界定還是得到了廣泛認同。廣義教育是指一切增進人的知識與技能、影響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動;狹義的教育為學校教育,是指社會通過學校對受教育的對象所施加的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以使受教育者發生預期變化的活動。[15]
廣義教育和狹義教育的共同點是:把教育看作是一種影響人、培養人的活動,這是教育的“質的規定性”[16],是教育區別于其他社會現象和活動的根本特征。
2.教育要素
教育是一種影響人、培養人的活動,由此教育活動首先必須要有施加影響、實施培養的人及對象,作者稱之為教育者和學習者。其次,必須要有施加的“影響”,即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交流的內容,作者借用傳播學認為的“傳播內容是信息”的觀點,將之稱為教育信息。再次,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交流教育信息必須要有一定的中介,上述對教育要素認識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這個“中介”上,或直接稱之為“教育中介”“教育影響”,或稱之為“教育媒介”“教育環境”,或稱之為“教育手段”“教育途徑”,作者認為這個“中介”就是指在教育過程中運用的一切物質手段、方法技能和知識經驗的總和,這個“總和”是什么呢?用“教育中介”“教育影響”“教育媒介”“教育環境”“教育手段”“教育途徑”中的任何一個指代都有失偏頗,作者認為這個“總和”就是“教育技術”!在此,教育技術不是通常所說的教育技術學科、教育技術專業甚至教育技術領域,那是一種實然狀態下的教育技術,而作者所說的是一種應然狀態下的教育技術,即在教育過程中運用的一切物質手段、方法技能和知識經驗的總和。最后,除此之外,教育活動可能還涉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如教育目的、教育觀念、教育效果等,對此我們在考察教育要素問題時,要注意區分“要素”和“因素”。
3.教育因素
要正確認識教育的構成要素,必須區分“要素”和“因素”兩個概念:要素是指構成事物的必要因素,而因素是指構成事物本質的成分、決定事物成敗的原因或條件,這說明因素外延寬于要素。在教育活動中,影響其運行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些是必要成分,缺少這些成分就不稱其為教育;而另外一些因素屬于充分條件,條件越充分,教育活動越有效,前者可稱為教育要素,要素和后者都可稱為教育因素,即教育要素是構成教育活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或成分。基于此,作者認為教育者、學習者、教育信息、教育技術是教育活動必不可少的成分,是教育要素,而教育目的、教育觀念、教育效果、教育評價、教育反饋甚至教育干擾等等都屬于教育因素,可用圖1來表示。
如圖1所示,中心的長方形代表教育要素,包括教育者、學習者、教育信息和教育技術,圓形代表教育傳播系統,構成教育傳播系統的成分除了四個教育要素外,還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效果、教育評價、教育反饋和教育干擾等因素,最外的正方形代表社會大系統,正方形(社會大系統)與圓形(教育系統)相切代表教育系統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大系統之中,二者之間發生著控制論意義上的輸入與輸出關系,并且由于社會背景的不同、社會時代的變遷,四個教育要素的內涵及其之間的關系(圖1中的雙向箭頭)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4.現代教育中教育要素內涵的變化
(1)教育者內涵的變化
傳統教育中,教育者通常指的就是教師,教師是教學權威,是教育信息的唯一來源,處于主體地位。在現代教育中,教育者的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組成來看,教育者除教師外,還包括教學設計者、教育管理者、教材編制者等;從角色來看,教師不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者,還是學習者的導師、促進者、組織者,更是學習者、研究者;從地位來看,教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權威”,而處于一種主導地位,是學習者智能的輔導者、認知的引導者、情意的誘導者。
(2)學習者內涵的變化

圖1 教育因素
傳統教育中,一般將教育對象稱為“受教育者”或“學生”,“受教育者”意味著教育對象處于一種被動接受的位置,是“被填之鴨”,是“容器”。“學生”這個概念中的“生”字,意味著學習者在心理、生理上的不成熟。這種認識,在20世紀中葉以前是可以的,而在其后,隨著終身教育、學習型社會等思想的普及,將所有的教育對象看成是“學生”就不合適了。現代教育中稱之為“學習者”,意味著他雖然仍然是教育的對象,是教育信息的接受者,是教學的客體,處于“學”的位置,但這不表示他被灌輸。相反,他是教育信息的探尋者,在教學活動中處于主體地位。在學習方式上,他不再是無意義的接受學習,利用探究學習、自主學習、合作學習等學習方式建構知識。學習者不僅包括未成年人,還包括各類成人學習者。在信息時代,任何人都必須是終身學習者。
(3)教育信息內涵的變化
傳統教育中,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交流的內容主要是指課本上的知識,即教材,這也是有學者把教材列為教育要素之一的原因。在現代教育中,教育信息指在教育傳播系統中傳遞、交流的內容,既包括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傳授的知識、方法、技能等內容,也包括教育活動中產生的維持其活動的中介內容。傳統教育中教師是教育內容的唯一來源,師生交流信息的方式以口語傳播為主,在現代教育中,教育信息的表現方式多媒化:文字出現后有了文字教材,視聽教學中有了幻燈、投影、廣播、電視等,計算機及其網絡出現后又有了數字化教材和網絡課程。同時,教育信息的傳遞途徑立體化: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既可以方便地實現面對面的實時交流,又可以實現非面對面的交流,既可以方便地實現異地實時交流,又可以實現異地非實時交流,另外,當代教育信息還實現了處理方式數字化、存儲方式光盤化、管理方式網絡化等特點。
(4)教育技術內涵的變化
由于傳統教育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的教育都是以教師為中心的班級授課制,除了黑板和粉筆以外,缺乏其他教育技術,特別是物質形態技術的支持,所以有學者將教學手段(包括教學方法、教學環境等)這些非實體要素與教師、學生并列成為教學的要素。現代教育是以現代教育技術為主的,適當結合傳統教育技術(如黑板、粉筆等)。廣義的教育技術包括物質形態的技術(如黑板、粉筆、幻燈、廣播、錄音、電視、計算機等)和智能形態的技術(如教學設計、教學策略、教學方法等),現代教育技術是指在現代教育思想指導下,把現代教育理論應用于教育教學實踐的手段和方法體系。
三、教育要素之間的關系分析
從圖1可以看出,教育要素之間的關系有六種,分別是:教育者與學習者的關系、教育者與教育信息的關系、教育者與教育技術的關系、學習者與教育信息的關系、學習者與教育技術的關系以及教育信息與教育技術的關系。以系統論的觀點看,系統中各個要素之間特定的相互關系與作用便形成該系統的結構[17],系統的結構可分為空間結構和時間結構,這里的空間結構即為通常所說的結構,是指系統內部各要素靜態的、空間的組織和排列形式,時間結構即為過程,是指系統狀態的變化,要素的動態展開形式。[18]由此,教育要素之間的關系分析相應地轉化為教育結構和教育過程的分析。
1.教育結構分析
教育結構有宏觀、中觀、微觀之分,宏觀上指教育體制的結構,中觀上指教育管理的結構,微觀上指教學課程的結構[19],筆者重點談談微觀教育結構即教學結構。
現代教育中各要素內涵的變化必然帶來教學結構的變革,因為教學結構反映了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何克抗教授認為,由于現代化教學環境下多增加了教學媒體這個要素,所以必須把“創建新型教學結構”作為當前高校教學改革的主要目標[20],雖然作者認為古今中外的教育要素(或教學要素)的構成是一致的,即不會減少或增加某個要素,但由于時代的不同,教育要素之間的六種關系及各種關系所處的地位會有所不同,即教學結構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在傳統教育中,教育者與學習者的關系處于所有關系的核心地位,有學者將教學結構分為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結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結構和學教并重的教學結構三種[21],正是抓住了教學要素中的兩個核心——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的關系來研究教學結構的。在現代教育中,如上所述,各要素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由于教育技術(特別是現代教育技術)的凸顯,除教育者與學習者的關系外,“人技關系”(教育者與教育技術的關系、學習者與教育技術的關系)顯得更為重要,處于主導地位,因此研究現代教學結構應以其中最凸顯的因素——“人技關系”為著眼點。以“人技關系”為依據劃分教學結構,可以分為以教育者為中心、以學習者為中心、以教育技術為中心三種(在此,教育技術主要是指教育媒體),詳見表1。
另外需要說明一點,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結構并不是走向以教育者為中心的教學結構的對立面,而是在以教育者為中心基礎上的超越,在發揮教育者主導性的同時,體現學習者的主體性,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結構對教育者的要求比以教育者為中心的教學結構要高,要求教育者成為良好的組織者、指導者、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
2.教育過程分析
任何具體的教育過程都是紛繁復雜、各具特點的,但人們往往用簡化的方式把握、認識其共同點、一般規律,即用模式方法來研究,得出來許許多多的教育模式,在教育技術界曾有一番關于“教學模式與教學結構”的爭鳴[22][23][24][25][26],作者認為:教學模式(即微觀教育模式)與教學結構(即微觀教育結構)并不存在誰包含誰、誰代替誰的問題,二者屬于同一層次的教育學概念,既有差異性,又有同一性,具有辯證的聯系性,教學模式更強調教學系統的時間特征,教學結構更強調教學系統的空間特征,利用模式研究法研究教學結構既得教學結構模式,研究教學過程既得教學過程模式。由此,教育過程分析即轉化為教學模式分析。
“教育結構的研究著重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的關系”,“教育模式的研究要認識特征,合理分類”,“要抓住主要矛盾,認識基本特征”。與傳統教學模式相比,現代教學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技術環境,其主要矛盾是“人機關系”,因此研究信息化教學模式應以其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技術環境”和“人機關系”為著眼點。從技術的發展看,現代教學模式以技術環境為依據可分為視聽教學模式、程序教學模式、計算機輔助教學模式、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教學模式四種,當然每種模式中的“人機關系”也不盡相同,詳見表2。
從表2可知,每一次現代教學模式的發展,應用到教育中的新媒體技術只是表面現象,對教育技術意義更大的是每一種模式背后所隱含的媒體與教育者和媒體與學習者的關系(即“人機關系”)不同與發展。視覺教育和視聽教育中技術的本質是輔助教師的課堂教學,媒體作為一種演示工具來使用,學生處于被動觀察的地位;視聽傳播引入傳播的概念和原理,媒體的位置從單一的物質手段轉向整個教育信息傳播過程的一個要素,進而使得視聽專家不僅重視教具、教材的使用,而且轉為充分關注教學信息怎樣從發送者(教師等),經由各種渠道(媒體等),傳遞到接受者(學生)的整個教育傳播過程;程序教學在設計程序教材和開發程序的過程中,重視學習者特性的研究,并且程序教材一般是用來個別化學習的,所以程序教學模式中隱含關注學習者學的理念;計算機輔助教育中,計算機既是教師的教學工具,又是學生的學習工具,但教學工具和學習工具的涉及面比較窄:對教師來說,計算機除了可以當作演示的工具外,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幫助教師完成部分教學任務、處理教學信息等方面,對學生來說,主要是通過課件進行個別化學習;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中,媒體技術不單單是教師的教學工具、學生的學習工具,還可以是傳遞教學信息的載體、師生的交流工具、同伴間的協作工具等等,總之信息技術與課程教學的各個要素融為一體,成為課程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表1 現代教學結構分類

表2 信息化教學模式分類
四、結論
1.教育是一種影響人、培養人的活動,古今中外的教育都由教育者、學習者、教育信息和教育技術四個要素構成,諸如教育目的、教育效果、教育評價、教育反饋和教育干擾等都屬于教育因素。
2.與傳統教育相比,現代教育的要素并沒有增加,而是各要素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3.教學模式與教學結構都是反應教學要素之間關系的概念,并不存在誰包含誰、誰代替誰的問題,二者屬于同一層次的教育學概念,既有差異性,又有同一性,具有辯證的聯系性,教學模式更強調教學系統的時間特征,教學結構更強調教學系統的空間特征。
4.現代教學結構中“人技關系”顯得更為重要,處于主導地位,以“人技關系”為依據劃分教學結構,可以分為以教育者為中心、以學習者為中心、以教育技術為中心三種。
5.現代教學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技術環境,其主要矛盾是“人機關系”,以技術環境為依據可分為視聽教學模式、程序教學模式、計算機輔助教學模式、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教學模式四種。▲
[1]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教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4.
[2]全國十二所重點師范大學聯合編寫.教育學基礎[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5-7.
[3]鄭金洲.教育通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9-16.
[4]馮建軍.現代教育學基礎[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90-93.
[5][6]陳桂生.教育原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7-26.
[7]沈俊強.再論“教育要素”——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背景下的重新解讀[J].上海教育科研,2006(4):17-19.
[8]張國霖.重構“教育要素”及其實踐意義[J].當代教育科學,2007(9):9-11.
[9][14]梁渭雄,孔棣華.現代教育哲學(修訂版)[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14-137.
[10][13]柳海民.教育原理[M].第2版.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101-107.
[11]趙儒彬.學習要素與教育要素——教育的四要素[J].太原教育學院學報,2005(2):6-10.
[12]馬前.教育要素的矛盾視角分析[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213-217.
[15]張樂天.教育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
[16]王道俊,王漢瀾.教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7]南國農,李運林.電化教育學[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50.
[18][26]朱永海,張新明.也論“教學結構”和“教學模式”[J].電化教育研究,2007(2):36-40.
[19]查有梁.教育模式[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前言.
[20]何克抗.E-learning與高校教學的深化改革(下)[J].中國電化教育,2002(3):11-14.
[21][23]余勝泉,馬寧.論教學結構——答邱崇光先生[J].電化教育研究,2003(6):3-8.
[22]邱崇光.“教學結構”和“教學模式”辨析——與何克抗教授商榷[J].電化教育研究,2002(9):10-13.
[24]邱崇光.對我國教育技術學科研現狀的冷思考——從“教學結構”和“教學模式”爭論談起[J].電化教育研究,2004(7):21-26.
[25]余勝泉,陳玲.論教學結構的實踐意義——再答邱崇光先生[J].電化教育研究,2005(2):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