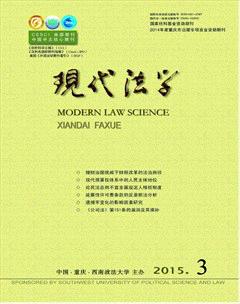論民法總則不宜全面規定人格權制度
摘要:人格權與主體制度存在明顯區別,其規定的具體性和民法總則規定的抽象性并不兼容,人格權的發展趨勢也表明其無法為民法總則的規定涵蓋,將人格權置于總則之中將影響人格權的充分保護和利用,人格權不應規定于總則中的主體制度,甚至不能全面規定于總則之中。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也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并將有利助推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與完善。
關鍵詞:人格權;人格利益;民法典編纂
中圖分類號:DF51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3.10
問題的提出自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民法典編纂的任務之后,我國立法機關開始啟動民法總則的制定工作。民法總則是統領整個民法典并且普遍適用于民商法各個部分的基本規則,構成了民法典中最基礎、最抽象的部分。總則是民法典的總綱,綱舉目張,整個民商事立法都應當在總則的統轄下具體展開。
然而,制定民法總則,需要解決一個重大立法問題,即如何處理好民法總則與人格權制度的關系。圍繞人格權是否應該獨立成編,學界爭議的核心點在于,人格權應置于民法總則中的主體制度中規定,還是應在民法分則層面獨立成編地規定。對此,學界存在一定的爭議。其中,反對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典型觀點認為,關于人格權的類型和內容的規范應該安排在總則編‘自然人項下[1],筆者不贊成此種觀點,而認為,人格權不應規定于總則中的主體制度之中,甚至不應全面規定于總則之中。下面,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人格權與主體制度存在明顯區別主張在民法總則的主體制度中規定人格權的一個重要理由在于,人格權與主體資格存在十分密切的聯系:人格權與人格制度不可分離,應當為民法典總則中的主體制度所涵蓋[2];從比較法上來看,一些國家的民法典(如《瑞士民法典》)就是在第一編“人法”中規定了自然人的人格權,即在主體制度中首先規定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然后規定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權,從而與主體制度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筆者認為,此種觀點值得商榷。
誠然,有關自然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健康等人格權是自然人與生俱來的、維持自然人主體資格所必備的權利,任何自然人一旦不享有這些人格權,則其作為主體資格的存在也毫無意義。正如我國臺灣地區學者王伯琦所言,“人格權為構成人格不可或缺之權利,如生命、身體、名譽、自由、姓名等是。”[3]鄭玉波先生也認為:“人格權者,乃存在于權利人自己人格之權利,申言之,即吾人與其人格之不分離的關系所享有之社會的利益,而受法律保護者是也。例如生命、身體、自由、貞操、名譽、肖像、姓名、信用等權利均屬之。”[4]對人格權進行保護實際就是充分尊重和保護個人的尊嚴與價值,促進個人自主性人格的釋放,實現個人必要的自由,這本身是實現個人人格、促進個人人格發展的方式。民法的人格權制度通過對一般人格權和具體人格權進行保護,確認主體對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種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權利,排斥一切“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違法行為的侵害,如此才能實現人格的獨立與發展。因而從價值層面來看,將人格權置于主體制度中規定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現代法學王利明:論民法總則不宜全面規定人格權制度——兼論人格權獨立成編然而,筆者認為,人格權制度雖然與主體制度之間存在上述密切關聯,但不可將二者等同,并因此在主體制度中對人格權制度作出規定,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將人格權制度與主體制度等同混淆了人格的兩種不同含義。“人格”一詞(英語為personality、德語為persnlichkeit、法語為personnalité)來源于羅馬法上的persona[5]。其具有兩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指權利能力,它是權利取得的資格。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人格一般包含著權利能力,并且構成抽象的從而是形成的法的概念。”[6]其第二種含義則是指基于對人格尊嚴、人身自由等價值理念的尊重而形成的人格利益,人格利益包括自然人依法享有的生命、健康、名譽、姓名、人身自由、隱私、婚姻自主等人格利益,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的名稱、名譽、信用、榮譽等人格利益。以人格利益為客體所形成的權利就是人格權。主體資格與主體所享有的具體權利之間雖然關聯密切,但人格權作為民事權利,與主體資格存在本質區別,不能相互混淆。無論是公民還是法人,作為一個平等的人格進入市民社會,就會與他人形成財產和人格上的聯系。這種人格關系顯然不是主體制度所能夠調整的,主體資格是產生人格關系的前提和基礎,但產生具體的人格關系還要依據具體的法律事實,包括人的出生、法律行為等。人格(法律人格)作為一種主體性資格,是主體享有一切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前提,從這一點上講,人格既不屬于財產權,也不屬于人身權,而是凌駕于二者之上的統攝性范疇,是人的資格和能力的確認,它理應納入民法典總則。然而,人格只是為主體享有法律權利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主體享有人格并不意味著其已享有實際權益,主體享有實際權益必須通過人格權、身份權、財產權等制度安排方能實現。尤其應當看到,在現代社會中,一些新的人格利益和人格權的出現,使人格權與主體資格的分離更為明顯。例如,在日本判例中出現了“宗教上的寧靜權、作為環境的人格權(包括通風、采光、道路通行等)”;這些人格權顯然與同主體資格有密切關系的人格權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這也表明,人格權制度的發展使得人格權的類型已不限于與主體資格有密切聯系的人格權,也越來越多地包括了與社會環境有關的人格利益,當這些利益受到侵害時,也應受到特殊救濟。因此我們在考慮人格權與人格的關系時不能僅從生命、健康、自由等傳統權利來考慮,而應當從人格權的整體發展來考慮其性質及其與人格之間的關系。這一變化表明,人格權已漸漸與主體資格發生分離,僅以生命、健康、自由與主體資格的關聯來界定人格權制度顯然是不妥當的[7]。
第二,將人格權制度與主體制度等同無法實現對人格權的充分保護。人格權僅是主體對自己的生命、健康、姓名、名譽等人格利益所享有一種民事權利,它和身份權、財產權一樣,都是人格得以實現和保障的具體途徑。人格的獨立和平等,要通過對人格權的充分保障才能實現。但將人格權制度與主體制度等同,則無法實現對人格權的充分保護,例如,某人實施了侵權行為,對他人的人格利益造成侵害,進而產生了侵害人格權的責任,這些顯然不是主體制度所能解決的問題。事實上,主體資格只是強調民事主體人格的平等和民事主體應當享有的能力,其本身并不涉及人格權被侵害后的救濟問題。由于現代民法貫徹主體平等的基本原則,不存在人格減等等人格受限制的情況,因此,行為人只能侵害他人的人格權,而不能侵害他人的主體資格,因此,要充分保護人格權,就必須將其與主體資格分離,如果人格利益不能成為獨立的權利,而仍然屬于主體資格的一部分,則侵權法就難以對人格權進行充分的救濟[8]。因此,人格權受到保護的前提是其與人格相分離,要實現這一目標,這就需要在民法典分則中確認公民、法人所享有的各項人格權,并通過人格權請求權等制度對各項侵害人格權的行為予以救濟,這也符合人格權作為民事權利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格權理應被置于民法典分則,通過主體制度涵蓋人格權制度的方式不利于實現對人格權的充分保護。endprint
第三,將人格權制度與主體制度等同無法形成人格權的利用制度。現代民法發展的重要趨勢,不僅是確認和保護權利,而且側重對權利進行利用,這與現代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有關,對資源的有效利用也在客觀上要求民法典及時確認相關的權利利用規則,從而為權利的有效利用創造條件[9]。這一點在物權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人格權法中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在人格權領域,傳統民法主要通過侵權法對人格權進行消極保護,但隨著現代大眾傳媒業的發展,人格權商業化利用的現象日益普遍,例如,名人的肖像常常被運用于各種商業廣告,從而促進其商品的銷售。使用名人肖像可以達到一種公眾對其商品質量的認可,也有助于吸引公眾的注意力,提高產品的知名度。再如,在大數據時代,對個人信息應當堅持利用與保護并舉,但更應當側重于利用,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只是對個人信息進行利用的一個限制條件。這種發展趨勢表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格權已逐漸與主體制度發生分離,僅以生命、健康、自由來解釋人格權顯然是不妥當的。主體資格是不可轉讓的,但某些人格權的部分權能可以轉讓,由此回應人格權的利用趨勢。如果將人格權制度規定在主體制度中,將導致某些人格權的部分權能不能轉讓,也就無法實現人格權的商業化利用,這顯然不符合人格權發展的現實狀況,也不能針對人格權這種商業化發展趨勢制定有效的人格權利用規則。
第四,將人格權制度與主體制度等同將存在立法技術問題。按照反對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典型觀點,將人格權制度放在主體制度中的自然人之中予以規定,這可能產生諸多立法技術上的問題。一方面,其無法有效處理法人人格權的規范問題。關于法人是否有人格權,雖然學界仍然存在爭議,但我國《民法通則》對法人人格權作出了規定,司法實踐也對其進行了保護,而且從救濟方式上看,雖然無法通過精神損害賠償對法人人格權進行救濟,但仍可適用人格權的其他保護方法對其進行救濟,這實際已經對法人人格權進行了肯定。如果在民法典總則自然人部分對人格權作出規定,則在立法技術上將無法處理法人人格權。另一方面,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其他主體也可能享有人格權。例如,合伙享有字號,即名稱權。如果將人格權在主體制度中作出規定,則在立法技術上也無法規定合伙的名稱權問題。尤其應當看到,如果在自然人和法人中分別規定人格權,不僅不能將人格權規定得比較詳細,而且這種分別規定的方法存在著一個固有的缺陷,即不能對人格權規定一般的規則,尤其是不能設定一般人格權的概念,這就必然會產生體系上的漏洞。
第五,將人格權制度與主體制度等同將無法解釋人格權的限制或克減制度,從而無法調整各種具體的人格關系。眾所周知,權利能力具有總括性、無法限制性和不可克減性,在現代法中不存在羅馬法中的人格減等。然而,人格權作為一種具體的權利,法律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維護等目的而對人格權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除了生命健康權因其固有屬性具有不可限制性[10],其他人格權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可限制性。以隱私權為例,法律需要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等方面考慮對個人隱私作出必要的限制[11],隱私權的范圍應當受到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限制,例如,一旦實行政府官員申報財產制度,則政府官員的財產信息隱私就受到了限制。所謂“公眾人物無隱私”,其實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有關人權的國際或區域性條約或公約也一般承認隱私權的可克減性。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4條就規定:“在社會緊急狀態威脅到國家的生命并經正式宣布時,本公約締約國得采取措施克減其在本公約下所承擔的義務,但克減的程度以緊急情勢所嚴格需要者為限,此等措施并不得與它根據國際法所負有的其他義務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純粹基于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出身的理由的歧視。”還要看到,人格權受到某種限制或克減并不會影響權利人的主體資格,而只是影響民事主體的具體人身利益[12]。
第六,將人格權制度與主體制度等同將無法規范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問題。從比較法上看,對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愈發受到重視,死者的人格尊嚴應受法律保護,也是為了保護生者對死者追思懷念的情感利益。因為追念前賢,感念先人,是為了激勵生者和后人。若不保護死者的人格尊嚴,不僅會導致近親屬的利益受損,損害其追思之情,而且有損社會人倫觀念。正如康德所言:“他的后代和后繼者——不管是他的親屬或不相識的人——都有資格去維護他的好名聲,好像維護自己的權利一樣。理由是,這些沒有證實的譴責威脅到所有人,他們死后也會遭到同樣地對待的危險。”[13]死者的人格尊嚴與近親屬的情感和尊嚴密切相關,如在姚貝娜事例中,媒體記者偷拍其遺體,顯然會刺激死者近親屬的情感,如果還將死者的照片公諸于世,其近親屬的感情將會受到更大的刺激。因此,侵害死者的人格尊嚴,往往也侵害其近親屬的人格利益,蔑視了近親屬對死者的追念之情,應被法律所制止。所以,人格權法有必要對死者的人格權益保護進行規定。我國司法實踐也積累了不少經驗,如著名的荷花女案、海燈法師案。需要通過總結這些經驗,從而形成制度化的規則,但如果通過主體制度規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在自然人已經死亡的情況下,其主體資格已經不復存在,主體制度難以為其人格利益保護提供必要的支持。因此,不宜在總則中規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問題。
事實上,晚近的一些民法典(如1967年《葡萄牙民法典》,1991年《魁北克民法典》等)大多將人格與人格權進行了明確區分,在一定程度上確定了人格權的獨立地位[14]。這也表明,人格權制度不宜置于民法典總則的主體制度中。
二、人格權規定的具體性和民法總則規定的抽象性并不兼容我們已經探討了民法總則中的主體制度不宜規定人格權制度,更進一步地說,整個民法總則中都不宜對人格權制度進行全面規定,因為人格權規定的具體性和民法總則規定的抽象性并不兼容。
從比較法上看,大陸法系民法典關于總則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所謂大總則模式,即《德國民法典》五編制模式下的大總則;二是所謂小總則模式,又稱形式序編模式,《法國民法典》堪稱此種模式的典范[15]。顯然,在《法國民法典》的小總則模式中,民法總則是無法全面涵蓋人格權制度的。以《法國民法典》為例,雖然其在第一編中就對“人”作出了規定,凸顯了人的重要地位,但該部分僅從人格權保護的角度對私生活(第9條)和人格尊嚴(第16條)的保護進行了規定,而未對人格權制度進行整體安排。直到當代,法國法院才從私生活受保護這一“母體性權利”出發,推導出肖像權、隱私權等一系列人格權,而其法律責任形式也都是通過援引第1382條的過錯責任來實現的。由此可見,《法國民法典》并沒有在其小總則中全面規定人格權。endprint
《德國民法典》采大總則模式,其也沒有在總則中對人格權作全面規定,而僅在第12條對姓名權作出了規定,因為姓名權是比較特殊的,其是人格的外在表現。在19世紀,雖然德國的人格權理論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人們也已經就人格權的重要性達成共識,但《德國民法典》并沒有對人格權制度作出系統性的規定[16]。《德國民法典》起草時,并沒有就生命、身體、健康等為人格權形成共識。正如民法典起草者所指出的“不可能承認一項 ‘對自身的原始權利”[17]。因而,《德國民法典》總則并沒有對人格權作出全面規定。無論是具體人格權,還是一般人格權,都是后來通過判例形成和發展的。當然,《德國民法典》主要通過侵權法規則對人格權進行保護,即在第823條第1款對“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幾種人格利益進行保護,第825條對貞操的保護,以及第826條對信用的保護。由于《德國民法典》沒有系統規定對人格權的保護,所以受到了耶林、基爾克等學者的批評。近十多年來,為了貫徹歐盟個人數據保護的指令,德國于2003年制定了《聯邦數據保護法》,其中也涉及隱私權的保護,由此可見,面對人格權保護的現實需要,德國法并沒有在《德國民法典》總則中對其作出規定,而是通過單行法和判例對其進行調整。
事實上,民法總則和人格權制度在規范性質上存在區別,不宜在民法總則中對人格權作出全面規定。民法總則是“提取公因式”的產物,它將民法典各編的共性規則提煉出來,集中加以規定,這有利于降低法律規則重復的概率。總則的設定使得民法典形成了總分結構,民法典的規則體系也呈現出從一般到個別的特點,在法律規則適用過程中,特別規則的適用要優先于一般規則,法律適用是從具體到抽象的反向過程,這就是梅迪庫斯所說的“從后往前看”的閱讀過程[18]。因此,總則的使命是規定法典最為一般性的規則,而把更為具體的規定置于分則之中,由于總則能夠適用于分則的所有內容,這必然要求總則中的規定是高度抽象和一般性的規則,不能包含特殊性或者技術性的規則。而人格權制度的規則具有復雜性、具體性和發展變動性,其中包含大量的技術性規范,這與民法總則規范的一般性和抽象性存在區別,這些內容顯然是不適合放在總則中,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作為人身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格權是與財產權相對應的,如果可以在民法總則中對人格權進行規定,那么財產權是否也應當置于總則之中,而不應該在分則中獨立成編?有學者認為,人格權對實現個人人格的獨立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應當規定于總則中。但財產權同樣對個人人格獨立和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但并未有觀點主張將財產權規定于總則中。總則雖然可以列舉各類民事權利類型,但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各類具體的民事權利作出具體規定,否則,總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
其次,人格權本身具有開放性,人格權是極富發展變動性的法律領域,不宜規定在民法總則中。為適應現代社會充分保障人格尊嚴、強化人文關懷的需要,人格利益的范圍不斷擴張,許多人格利益逐漸類型化為人格權。例如,傳統民法重點保護物質性人格權,如生命健康等權利,而在現代社會,一些精神性人格權的地位在不斷上升,如名譽權、隱私權等,各種權利外的人格利益也在不斷發展,如聲音、形象以及死者人格利益等,在大數據時代,個人數據權也越來越具有重要性,此外,為有效保護人格權外的各種新型人格利益,也出現了一般人格權的概念,它形成了一種兜底性的條款,從而適應了新型人格利益發展的需要[19]。由此表明,人格權的內容越來越豐富,相關的法律規則也更為具體和細致,民法總則抽象宣言式的規定已經不能適應人格權制度的發展趨勢,因此不宜在民法總則中對人格權制度進行全面規定。
第三,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格權制度將愈發龐雜,人格權的利用和保護可能涉及大量的技術性規范,不宜規定在民法總則中。隨著人格權制度的發展,一些人格權獨有的利用規則和保護規則大量產生,例如,有關法人名稱、自然人肖像權能的轉讓涉及合同的成立、生效的規則,生命健康權領域可能產生器官移植、代孕、人體試驗、藥物試驗等新的技術性規則。這些繁瑣、復雜的技術性規則顯然不宜出現在民法總則之中。此外,人格權的保護規則也可能日益復雜,例如,人格權關于責任構成要件、責任形式、責任競合等規定,這些內容如果作為總則的一章,顯然導致該章過分膨脹,與總則的其他章節之間不協調,損害法典的形式美感。而且總則也無法全部囊括此種技術性規范,否則將喪失總則原本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瑞士民法典》在總則中規定了人格權,并規定了人格權請求權,其具體包括請求禁止即將面臨的妨害、請求除去已經發生的妨害和請求消除影響等,同時它也確立了人格權請求權的其他相關規定。嚴格地說,這些內容顯然不應屬于總則的內容。
第四,在婚姻家庭制度回歸民法典后,其也將與人格權制度共同構成完整的人身權體系,一方面,民法典本身就是確認和保護財產權和人身權兩大權利,民法典就是圍繞這兩個權利而展開,財產權已經在分則中獨立成編,而在婚姻家庭法回歸民法典之后,身份權也獨立成編,但如果將人格權單獨置于總則中進行規定,而不獨立成編,難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國《民法通則》單設第五章民事權利,也為未來民法典分則確立了基本的體系架構,在該章之中,人格權被放在人身權之中規定,這就表明,人格權應當與身份權共同作為分則內容,這符合《民法通則》所確立的體系結構。
三、人格權的發展趨勢表明其無法為民法總則所完全涵蓋人格權是一個開放、變動的權利體系,也是現代民事權利新的發展領域。現代民法越來越強調以人為中心,彰顯人文精神,強化對人的關懷和保護。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人們認識到現代化的核心應當是以人為本,充分保障個人的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因此,人身權應該置于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現代化的過程是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面完善的過程,現代化始終伴隨著權利的擴張和對權利的充分保護。同樣,法律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正是在對個人權利的充分確認和保障,以及對人的終極關懷。而對人格權的保護就是實現這種終極關懷的重要途徑。在傳統民法的規范配置中,有關財產權的規范占據絕對統治地位,其涉及財產的事先分配、流轉和事后保護各個層面,但對人格權的規范極少;而現代民法在人格權方面經歷了一個從僅規定個別人格權的階段發展到既對人格權做出抽象規定,又對人格權進行具體列舉的階段,從民法僅在侵權行為法范圍內對人格權保護進行消極規定發展到民法在“人法”部分對人格權做出積極的正面宣示性規定[20]。 可以說,人格權制度的發展是現代民法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人格權的發展趨勢表明,其無法完全規定在民法總則中,而必須在民法典分則中獨立成編地加以規定,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endprint
第一,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推動了人格權制度的演化。一方面,市場經濟越發展,越需要強化對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的保護,這在客觀上將人格權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現代城市化生活所帶來的“個人情報的泄漏、窺視私生活、竊聽電話、強迫信教、侵害個人生活秘密權、性方面的干擾以及其他的危害人格權及人性的城市生活現狀必須加以改善。”[21]工業化的發展,各種噪音、噪聲等不可量物的侵害,使個人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安寧被嚴重破壞。從而使自然人的環境權、休息權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義,因此國外不少判例將這些內容都上升到人格權的高度加以保護,而近來外國學說與判例又在探索所謂“談話權”和“尊重個人感情權”,認為談話由聲音、語調、節奏等形成,足以成為人格的標志[22]。這些都造成了人格利益的極大擴張。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還促使了人格權商業化利用的發展,人格權的財產價值被不斷發掘,在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如日本等,出現了商品化權,不僅對一些可商品化的人格權進行保護,而且對非人格權的形象(如卡通形象、表演形象等)也予以保護[23]。而在英美法系自從美國提出公開權概念之后,對于隱私權之外的有關姓名、肖像等權利在商業上的利用予以特別保護。公開權常常被界定為具有財產權性質的權利[24]。這些都應受到人格權法的調整。
第二,人權運動的發展,以及對人的保護的強化,都促使人格權的具體類型日益增加。不僅使具體人格權的類型日益豐富,各項人格權的內容越來越豐富,而且在德國、瑞士等國家產生了一般人格權制度,例如,近一百多年來,隱私權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張,從最初保護私人生活秘密擴張到對個人信息、通信、個人私人空間甚至虛擬空間以及私人活動等許多領域的保護,不僅僅在私人支配的領域存在隱私,甚至在公共場所、工作地點、辦公場所都存在私人的隱私。人格權不僅受到國內法的保護,也逐漸受到國際條約的保護,人格權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有關人權的國際公約所確認的權利都成為人格權存在的依據。例如,《國際政治與公民權利公約》第17節中規定:“1.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通信或信件都不應受到任意或非法干涉,任何人的榮譽或信譽(聲譽)都不應受到非法攻擊。2.所有人都有權得到法律保護,以免遭受侮辱或誹謗。”這都推動了人格權具體類型和內容的發展。自“棱鏡門事件”后,尊重隱私成為了尊重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25]。
第三,高科技的發展促使人格權制度不斷發展,內容不斷豐富。在現代社會,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保護成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現代網絡通訊技術、計算機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等高科技的迅猛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但同時也改變了傳統生產和生活的形式,增加了民事主體權利受侵害的風險。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如網絡技術的發展對隱私的侵犯,基因技術的發展對人的尊嚴的妨害,都提出了大量的新課題,美國邁阿密大學的教授曾經撰寫了一篇以《隱私已經死亡了嗎?》為題的文章,其中提到,日常信息資料的搜集、在公共場所自動監視的增加、對面部特征的技術辨認、電話竊聽、汽車跟蹤、衛星定位監視、工作場所的監控、互聯網上的跟蹤、在電腦硬件上裝置監控設施、紅外線掃描、遠距離拍照、透過身體的掃描等等,這些現代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人們無處藏身,所以,他發出了“隱私已經死亡”的感慨[26]。其認為,高科技的發展,使隱私權已經變成了“零隱權”(Zero Privacy)[27]。又如,生物技術的發展、試管嬰兒的出現改變了傳統上對生命的理解,人工器官制造技術、干細胞研究、克隆技術和組織工程學的發展在為人類最終解決器官來源問題的同時,也對個人人格權的保護提出了挑戰。上述科學技術的發展,對生命、身體、健康等人格權的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需要人格權法律制度作出全面、具體的回應,在民法總則中全面規定人格權顯然無法實現這一目的。
第四,網絡環境下的人格權保護日益重要。互聯網的發展使人類進入了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使人們的溝通更為便捷,但互聯網的發展也給人格權的保護提出尖銳的挑戰。一方面,由于計算機聯網和信息的共享,使對個人信息的收集、儲存、公開變得更為容易,“數據的流動甚至可能是跨國的,最初在某個電腦中存儲,傳送到他國的服務器中,從而被傳送到他國的網站上”[28]。因此,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對隱私權等人格權的侵害變得越來越容易,且損害后果也更為嚴重。另一方面,隨著計算機網絡的廣泛應用,網絡侵權日益增多,且侵害的民事權利涉及諸多類型。互聯網空間的虛擬性也使得網絡侵權事實和侵權后果的認定較為因難,有時甚至很難認定權利主體和侵權主體。因此,網絡技術的發展對人格權的保護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挑戰,必然需要立法和司法予以應對。例如,2014年,巴西通過了《互聯網民法》,該法把互聯網環境下的人格權保護納入民法的調整范圍,對互聯網用戶和服務商就互聯網的權利、義務和保障進行了全面規范,同時規定了網絡言論自由和個人數據保護等網絡基本原則,明確了用戶、企業和公共機構在巴西使用互聯網的權利和義務,全面地保護個人信息和隱私的安全。該條規定:“在不影響對所受損害給予賠償的情況下,法官得規定采取諸如對有爭執的財產實行保管、扣押或其他適于阻止或制止妨害私生活隱私的任何措施;如情況緊急,此種措施得依緊急審理命令之。”由此可以看出,網絡環境下人格權的保護問題較為復雜,僅在民法典總則部分規定人格權顯然無法有效回應網絡環境下人格權保護的現實需要。
第五,在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的保護也應納入人格權制度的規制范疇。由于數字化以及數據庫技術的發展,對信息的搜集、加工、處理變得非常容易,信息的市場價值也愈發受到重視,對于信息財產權和隱私權保護的需求也日益增強,個人信息作為個人享有的基本人權也日益受到法律的高度重視。個人信息權雖然具有多重屬性,但其內容主要還是一項人格權,因為個人信息與個人的身份存在密切關聯,其主要是一種人格利益而非財產利益,而且多數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存在一定的交叉,由于對個人信息的平等保護也體現了個人人格尊嚴的平等性,因此,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也體現了對個人人格尊嚴的尊重與保護。從比較法上來看,有的國家(如美國)在《隱私權法》中規定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歐盟雖然制定了單獨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但仍承認個人信息權的人格權屬性。由于個人信息權的內容及利用方式較為復雜,有關個人信息權的救濟規則也多種多樣,因而難以在民法典總則中加以規定,必須通過獨立成編的人格權法單獨規定。endprint
第六,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格權的類型和內容日趨復雜,其經常涉及和其他權利的沖突問題,為此需要確立一系列解決此類沖突的規則,即有效協調人格權和其他權利的關系。例如,現代社會,報紙、電視、廣播以及互聯網等大眾傳媒在便捷信息交流的同時,也使得人格權更加脆弱,極易受到侵害。如何有效平衡表達自由、新聞自由、輿論監督和人格權保護的關系,也成為人格權法所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總之,我們在編纂民法典的過程中,不能以19世紀的圖景觀察21世紀。由于19世紀的社會形態較為簡單,其人格權內容較為確定,侵害人格權的方式也較為簡單。但21世紀是信息社會、網絡社會、科技社會、消費社會、風險社會,人格權的類型、內容處于持續發展之中,內容更為難以確定,人格權的利用與保護規則也較為復雜,侵害人格權的手段也日益復雜多樣,而且人格權的利用與保護還涉及科技發展、言論自由、商業利用、公法管制等多層次的復雜關系。這都要求我們的民法典為各類人格權提供更為充分的保護規范,人格權是一個開放、發展的體系,隨著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其所需的規范內容也將越來越多,因此,民法總則已經無法涵蓋人格權制度的全部內容,應當在民法典分則中單獨成編地對人格權作出規定。
四、人格權置于總則之中將影響人格權的充分保護和利用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編纂民法典的根本任務就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和關懷人,但如果僅在民法總則中對人格權進行規定,必然會影響對人格權的利用和保護,使民法典的價值目標難以真正得到實現。
(一)總則無法規定人格權請求權
在19世紀民法中,人格權的類型和內容較為簡單,侵害方式較為單一,因而法律無須對人格權進行細致地規范,而只需要通過侵權法對其進行消極保護。但在現代社會,人格權的權利內容與侵害方式都是多元化的,僅通過侵權法規則對人格權進行消極保護將難以充分實現對人的保護。現代社會中人格權內容的確定較為困難,其保護規則更為復雜,這就需要大量采用人格權請求權,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預防妨害以及恢復原狀等請求權,對人格權進行保護。從立法技術上說,對具體民事權利的保護規則應根據其自身特點進行設置,如物權請求權中的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等,即應當規定在物權法中。對于人格權來說,設立獨立的人格權請求權同樣必要,特別是對于那些因尚未造成實際損害的行為,即需要通過設置具體人格權請求權對其進行規制。例如,要想阻止他人擅自為自己制作肖像,權利人就必須享有停止侵害的人格權請求權,而此類請求權顯然只能在人格權制度中進行規定。人格權請求權是基于人格權而產生的權利,與人格權是不可分離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人格權請求權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趨勢,如侵害人格權的損害后果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因為在網絡環境下,侵害人格權的損害后果具有無限放大性,受眾具有無限性,因此,侵害人格權的行為一旦在網絡上傳開,其造成的損害后果是無法估計的。因此,為了充分保護權利人,應當廣泛采用停止侵害的方式,以防患于未然。例如,《法國民法典》第9條第2款對此作出了規定[29]。在最終判決作出之前,法官還可以作出預先裁決,責令行為人停止出版、禁止發行流通,或責令將出版物全部或部分予以查禁[30]。德國法也經常采用禁止令對侵害人格權的行為進行規制[31],針對一些特殊的侵害人格權的行為,法院還責令被告聲明撤回其不當言論,以防止損害后果的繼續擴大。歐洲人權法院也采用預防損害的方式對人格權遭受侵害的受害人提供救濟。例如,在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的Editions Plon v. France一案中,針對被告出版違反醫療保密義務的書籍、可能侵害法國前總統密特朗隱私的行為,法院即根據原告的申請頒發了禁止出版令,以防止損害的擴大[32]。此外,一些國家的法律普遍賦予了受害人以刪除權、請求聲明撤回等權利。這尤其表現在以言論的方式侵害他人名譽的情形[33]。上述救濟方式應當屬于人格權請求權的內容,由于此類救濟方式一般僅適用于特殊的人格權侵權類型,因此不宜規定在民法典總則中[34]。
(二)總則無法規定精神損害賠償
人格權法作為民事單行法,理所應當規定法律責任,規定侵害人格權所特有的法律責任。與侵害財產權不同的是,在侵害人格權尤其是精神性人格權的情況下,受害人常常會遭受精神損害。關于精神損害賠償責任,《侵權責任法》只在第22條對其作出了規定,規定較為簡略,因此,主要應當在人格權法中對精神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則作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01年出臺了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我國未來人格權法可以此為基礎、總結我國既有的司法實踐經驗,對侵害人格權的精神損害賠償的侵權責任作出全面的規定。對于一般的侵權責任,可以通過在人格權法中規定引致條款,借助侵權責任法加以規定,但對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而言,其認定規則非常具體復雜,無法在民法典總則中進行規定,而應當在人格權法中作出詳細規定。
(三)總則無法規定懲罰性賠償
鑒于人格權益主要是精神利益,對其侵害后果往往難以通過金錢衡量,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侵害人格權的損害后果十分嚴重。所以,應當在侵害人格權的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比較法上也開始在侵害人格權的領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例如,在德國的一個案例中,對于未經許可使用他人音樂作品的人,法院判決行為人要支付相當于許可使用費兩倍的金額[35]。在著名的“卡洛琳訴德國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也采納了懲罰性賠償,判決被告賠償九萬三千歐元[36]。而且從法律上看,在人格權侵權中,行為人的惡意更應當受到制裁,如對于惡意毀損他人名譽、泄露他人隱私的行為,更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37]。此外,行為人在侵害他人人格權時往往有牟利的故意在其中,而現行法對此種行為的制裁受到局限。因此,對侵害人格權的行為而言,懲罰性賠償不僅有利于有效制裁加害人,而且有助于解決實際損害與獲利的證明困難問題。這些規則屬于侵害人格權所特有的規則,一般不適用于人格權之外的民法領域,因此不宜規定在民法典總則中。endprint
(四)總則無法規定人格權之間以及人格權與其他權利的沖突解決規范
如前所述,人格權在行使中常常與其他權利發生沖突。如實踐中常見的人格權與財產權、隱私與新聞自由、名譽權與輿論監督等權利的沖突。人格權在行使過程中,有可能會與公權力的行使發生沖突。還應看到,人格權自身相互之間也可能發生沖突,從而需要在人格權法中確立解決沖突的規則。例如,當生命權與財產權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保護生命權;當肖像權與肖像作品著作權發生沖突時,優先保護肖像權。而侵權責任法不能解決權利行使和權利沖突的問題。此外,為了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等,在法律上有必要對于人格權作出一定的限制,這些限制規則不能在侵權責任法中規定,而只能由人格權法加以規定。例如,對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人格權權利不得濫用、人格權與言論自由的關系等。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格權法的獨立成編,也可以起到和侵權責任法相互配合的作用。
(五)總則無法規定人格權的利用規范
如前所述,在現代社會,不僅應當關注人格權的保護,還應當更多地關注人格權的有效利用,人格權制度是由確認、利用和保護三類規范共同組成的。隨著近幾十年來人格權商品化的發展,人格利益如姓名、肖像、聲音、隱私等,在傳統上被認為是財產之外的沒有價格的利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權利越來越具有財產屬性,可以轉讓、允許他人使用。例如,在美國出現了公開權制度,在歐洲出現了所謂的“形象代言人權利”,甚至一個人的聲音、筆跡、舞臺的形象等人格權益都可能成為商業化利用的對象。現代各國法律確定個人對其信息所享有的支配權,目的之一就是促進個人對信息的利用,對信息的保護和利用構成個人對信息所享有的權利的兩個支柱。由此表明,現代社會中,對人格權的主動利用趨勢日益突出和普遍,人格權的內涵在逐漸擴張,利用方式和適用范圍也不斷豐富,但是,由于人格權自身的特殊屬性,使得對于人格權的利用,應與物權、知識產權等財產權有所區分,因此,有必要構建一套以保護人格尊嚴為基礎的人格權利用制度。
五、結語:民法典體系應當有所創新有所發展民法典編纂的關鍵在于確立科學的體系結構。確立我國民法典體系結構應當從中國國情出發,以我國民事立法經驗為基礎。具體來說,民法總則和人格權編的制定,應當在《民法通則》和2002年的《民法草案》的基礎上進行,而《民法通則》將人格權置于民事權利體系中加以規定,并與物權、債權相并列,本身就表明《民法通則》已經確認人格權是與物權、債權具有同等地位的基本民事權利,而且應當與物權、債權一樣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所以,在未來的民法典中,人格權獨立成編是與《民法通則》一脈相承的,而2002年《民法草案》第一稿在第四編中專門規定人格權法,其中共設七章,包括一般規定、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信用權和隱私權。雖然該編僅有二十九個條文,但基本上構建了人格權法的框架和體系,也表明我國民法典已經采納了人格權法獨立成編的立法建議。該草案實際上是立法機關在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基礎上作出的立法判斷,凝聚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因此,該體例結構應當為未來民法典編纂所繼續采納。毫無疑問,在總則中對人格權作出概括性、宣示性的規定,是可行的,但是人格權法作為一項整體制度不宜在民法總則中全面規定,而應獨立成編。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而不應當完全照搬《德國民法典》的經驗,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21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優良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也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并將有利助推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與完善。ML
參考文獻:
[1]鐘瑞棟.人格權法不能獨立成編的五點理由[J].太平洋學報,2008,(2).
[2]梁慧星.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大綱(草案)·總說明[G]//梁慧星.民商法論叢:第1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800.
[3]王伯琦.民法總則[M].臺北:中正書局,1994:57.
[4]鄭玉波.民法總則[M].臺北:三民書局,1998:96.
[5] Gert Brüggemeier, Aurelia Colombi Ciacchi, Patrick OCallaghan.Personality Rights in European Tort Law[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7.
[6]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46.
[7]馬海霞論人格權在未來我國民法典種的地位[J].天中學刊,2004,(19).
[8]李中原.潘得克頓體系的解釋、完善與中國民法典體系的構建[G]//陳小君.私法研究:第2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9]劉守英.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實施[J].法商研究,2014,(2).
[10]楊成銘.人權法學[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121.
[11]張新寶.隱私權的法律保護[M].2版北京:群眾出版社,2004:16.
[12]曹險峰.人格權法與中國民法典的制定[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3).
[13]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M].沈叔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120.endprint
[14]徐國棟.人格權制度歷史沿革[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1).
[15]Vgl. Motive zu dem Entwurfe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d.Ⅰ, 1888,S. 274
[16]霍爾斯特·埃曼.德國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權制度-論從非道德行為到侵權行為的轉變[G]//邵建東,等,譯.梁慧星.民商法論叢:第23卷.香港:金橋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413.
[17]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M].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14-516,527.
[18]Basil S.Marksinis. Protecting Privac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36-37.
[19]張新寶.人格權法的內部體系[J].法學論壇,2003,(6).
[20]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體系[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48.
[21]姚輝.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1.
[22]荻原有里.日本法律對商業形象權的保護[J].知識產權,2003,(5):62-64.
[23]Michael Henry. International Privacy, Publicity and Personality Laws[M]. Reed Elsevier ( UK), 2001:88.
[24]謝來.網絡時代,如何保衛國家“隱私”[N].國際先驅導報,2013-10-08.
[25]A. Michael Froomkin. Cyberspace and Privacy: A New legal Paradigm? The Death of Privacy?[J]. Stan.L. Rev.,2000,(52):1461.
[26]A. Michael Froomkin. Cyberspace and Privacy: A New legal Paradigm? The Death of Privacy? [J]. Stan.L. Rev.,2000,(52):1461.
[27]Raymond Wacks:Personal Informa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205.
[28]美國霸權遭質疑 中國經驗受關注[N].浙江日報,2014-05-12.
[29]考茨歐,等.針對大眾媒體侵害人格權的保護:各種制度與實踐[M].余佳楠,等,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170.
[30]BGHZ 138,311,318.
[31]Editions Plon v. France. Application No. 58148/00.
[32]考茨歐,等.針對大眾媒體侵害人格權的保護:各種制度與實踐[M].余佳楠,等,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284.
[33]崔建遠.絕對權請求權抑或侵權責任方式[J].法學,2002,(1).
[34]BGHZ 17,376,383.
[35]OLG Hamburg,NJW 2870,2871.
[36]Pierre Catala. Avantprojet de réforme des obligations et de la prescription[M]. 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 2005:182.
[37]Richard C. Turkington & Anita L. Allen. Privacy Law, Cases and Materials[M]. West Group, 1999:2.
Abstract: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sonality right and principal system, in which the specificity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abstract feature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 of Civil law. The evolutionary trend of personality right indicates that it cannot be fully covered by the general provision. The inclusion of personality right in the general provision will have adverse effect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 Therefore, it is better not to include personality right into either principal system or the general provision. The independent compila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 is not only strongly theoretically supported but significantly guiding the practice. Furthermore, it suits the development from civil law to 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and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code mechanism.
Key Words: personality right; personality interest;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