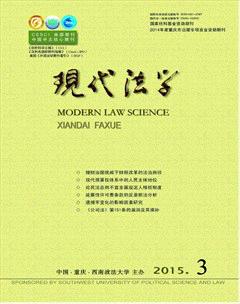我國刑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研究
摘要:我國基于刑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在發回重審的條件和發回重審的程序上都存在明顯的問題,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處理好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及效率價值之間的關系。我國應該以兼顧程序公正、實體公正、效率三種價值的實現為指導思想,重構基于刑事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制度。
關鍵詞:刑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程序公正;實體公正;效率
中圖分類號:DF73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3.20
引言原審法院的違法判決一般采用發回重審的方式予以處理另一種主要處理方式是自行改判,但自行改判主要針對實體錯誤,而發回重審主要針對程序錯誤。,但違法事由存在實體違法與程序違法之區別,因此之故,發回重審也可相應地分為基于實體違法的發回重審與基于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基于實體違法的發回重審主要是原審法院錯誤認定事實或者因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原因所致,而基于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則主要在于刑事訴訟中的公共權力機關違反程序規則或者因為違反證據規則等所致。
基于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是一種重要的程序違法制裁與救濟措施,它對于維護公正審判、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實現程序的獨立價值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受“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影響,我國對基于刑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這一問題并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與重視。理論界對發回重審的研究也主要側重于對基于實體違法的發回重審的研究,專門對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研究較少。(參見:陳衛東,李奮飛.刑事二審“發回重審”制度之重構[J].法學研究,2004,(1):132-144;史立梅,劉林吶.我國刑事二審發回重審制度的反思與重構[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4,(3):60-67;葛琳.刑事訴訟程序回轉現象之反思[J].西部法學評論,2010,(6):84-94.)2012年對1996年《刑事訴訟法》做了較大的修改,修改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通過設立程序違法的制裁機制來促進程序獨立價值的實現。在此背景下,展開對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問題的專門研究,很有必要。
一、我國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關于因程序違法所致的發回重審,在我國1979年、1996年、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均有相應規定。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138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正確判決的時候,應當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從該規定可知:原審程序違法是否會有發回重審的結果以是否影響正確判決為標尺,如果可能影響正確判決的就發回重審,反之則不發回重審。該規定以程序工具主義為出發點,對實現程序的獨立價值并無益處。而1996年《刑事訴訟法》在第191條中卻做出如下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回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從該規定看,在基于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問題上,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1979年《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兩點修改:一是改變原有概括式規范方式,而用列舉具體程序違法(第1、2、4項)的方法明確了發回重審的情形;二是對于沒法列舉的程序違法而須發回重審的判斷標準由可能影響正確判決修改為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第3、5項),兩點修改將具體與原則結合,既使操作性增強,又兼顧了對程序公正獨立價值的重視。
現代法學袁錦凡:我國刑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研究——反思與重建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內容中,不僅完全保留了1996年《刑事訴訟法》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相關規定,而且擴展了發回重審的程序范圍,這主要表現為在審監程序和死刑復核程序中也增加了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規定。關于審監程序中的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第242條規定:“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四)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關于死刑復核程序中基于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詳見第350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六)原審違反法定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裁定不予核準,并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此問題的修改,將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適用程序從第二審程序擴展延伸到了審監程序和死刑復核程序,進一步擴大了發回重審這種程序違法制裁的適用范圍及可以適用的審理程序,這對于維護審判程序的公正性和實現程序的獨立價值,無疑大有裨益。
但是,盡管如此,我國在基于刑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上仍存在明顯缺漏,這可以概括為發回重審的條件和發回重審的程序兩個方面。
在發回重審的條件上,要有以下問題:
1.法律對符合直接發回重審條件的程序違法事由列舉不全
根據我國法律的規定,并不是所有的程序違法都會導致發回重審,而是只有屬于五種情形之一的程序違法才會導致發回重審,這五種情形實際上包含了發回重審的兩種條件:一種是直接發回重審的條件,只要存在該違法情形就直接發回重審,具體包括違反公開審判、違反回避制度、審判組織不合法三種程序違法情形;另一種以“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為條件,依此條件,程序違法需要進一步判斷是否可能對公正審判形成影響,其要求在司法實踐中,法官應對程序違法的程度做相應判斷,若是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則發回重審,反之則不用發回,此種違法主要包括剝奪或限制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以及其他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之所以將違反公開審判、審判組織組成不合法、違反回避制度作為直接發回重審三種列舉式條件,其主要原因是這幾種制度是構成公正審判最本質的元素,一旦受到破壞,將使公正審判根基動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列舉式條件明顯過窄,只是關注到司法機關的需求而漠視了對當事人權利的保障。endprint
2.對于“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判斷標準不明確
除了屬于列舉式直接發回重審的情形之外,若是存在其他程序違法是否也要以發回重審的方式解決錯誤?對此,2012年《刑事訴訟法》把其他情形列入“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范疇,若與1979年《刑事訴訟法》設定的可能影響正確判決標準相比較,此標準更為抽象。如果說“影響判決標準”還有判決作為基本參照物的可能,則“影響公正審判標準”已然沒有具象的可能。應該如何理解此標準是適用發回重審最為棘手的問題,縱觀2012年《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似乎皆沒有予以明確說明,如果任由法官裁量,見仁見智、異人異判將導致司法混亂。
3.發回重審條件過于單一
“以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為發回重審的條件原本無可厚非,但若是沒有其他程序性條件相輔助,可能導致發回次數過多。如果當事人明知自己有針對程序違法的異議權,法律也有明確規定,但是其“懈怠”行使該權利,則法院可否裁量即便程序違法也不予發回重審?比如對于回避,《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詳細的申請與異議程序,對于非法證據的排除,《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詳細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但是有些當事人基于某種考慮,故意不在原審中及時提出,而是在原審結束后再在后續審判中提出,這不僅導致程序違法不能及時得到糾正,而且導致訴訟費用的增加、訴訟效率的降低。有學者在調研中發現,司法實踐中出現過被告人在一審程序對非法取證只字不提,且認罪態度良好,卻在二審中突然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主張。(參見:陳衛東,等.“兩個證據規定”實施情況調研報告[J].證據科學,2012,(20).)對這樣的情況,有權發回重審的法院應該如何做出決定?
4.幾大程序(二審、審監、死刑復核)對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標準不同可能導致法官無從取舍
2012年《刑事訴訟法》規定,幾大程序均可以程序違法為由發回重審,但是在不同程序中卻無同一的發回重審標準。在二審程序中有直接發回以及“可能影響公正審判”兩種判斷標準,但是在審監和死刑復核程序中,卻只有“可能影響公正審判”一種判斷標準,該非同一的判斷標準會使得三大程序在適用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相關規定上有不相協調之處,其可能導致的結果是:同一個程序違法事由會在不同的程序中產生不同后果。以列舉式違法事由為例:違反公開審判、回避制度、審判組織不合法如果發生在二審程序中,只有一種結果:直接發回重審;但是,若是發生在審監或者死刑復核程序中,則法官必須進一步做出是否“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判斷。
在發回重審的程序方面,也存在以下四個問題:
1.有權重審法院的單一性使重審的公正性受到影響
現行法律規定只有原審法院有權重審。由原審法院重審,既符合審判管轄原則的要求,也可促使原審法院在重審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在發回重審的審理中,法律明確規定原審合議庭應當回避,必須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庭審。但是,由于我國審判組織對案件的決定權有限,特別是經由上級法院發回重審的案件,合議庭是否有足夠的裁判權或者還是延續審判委員會集體討論的方式,或者原審法院是否有足夠的勇氣直面原審錯誤并做出正確裁判,皆充滿相當多的變數,這些因素會使重審的公正性飽受質疑[1]。
2.法律沒有規定發回重審的裁定效力
《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程序違法,應當裁定發回重審,但是對于裁定要記載什么內容法典沒有進一步規范。最近幾年,為了使法院之間的監督關系良性發展,避免因上級過多干預致下級法院無所適從的情形發生,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于規范上下級人民法院審判業務關系的若干意見》,在此意見中明確第二審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發回重審時,不能僅僅作結論性的表述而應當在裁定書中釋明發回重審的理由及相關的法律依據。即二審法院若是以一審裁判程序違法發回重審時,應在重審裁定中表明是哪個程序違法,這種明示而非曖昧意指的做法對規范二審法院的發回重審行為有意義;此外也使原審法院明確了解程序錯誤所在并有針對性地予以糾正。但是,此規定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中沒有得到相應體現,現行法律沒有對二審法院發回重審裁定的效力予以規范,也即盡管有上級法院明確指出的錯誤存在,但原審法院在重審時還是會出現不按照該裁定所闡明的程序違法理由進行審判的情況,從而導致案件在一審二審之間反復流轉,既影響了訴訟效率,也不利于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監督與指導。
3.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性規定
發回重審的案件,均是適用一審程序進行審理,由此,所作的裁判為一審裁判。控辯雙方針對重審后的裁判,依法可以再次上訴、抗訴,為避免之前刑事司法實踐中出現數次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數次上訴抗訴的不經濟審判,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發回重審次數予以限制,但是該限制僅限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的情形,而不包括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情形,也即因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情況不在二次限制次數之列。
4.發回重審的選擇權缺失可能致被告人在重審中的不利歸己
刑事司法中的程序違法是專門機關在實施訴訟行為中出錯,所以因程序違法而產生的負面后果理應由專門機關承受,而且,在正當程序國家,被告人往往還因此從中獲利。但是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所顯現的情況較為復雜,每一次審判對被告人而言無疑增加一次不利益的風險,被告人在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中,有可能出現最后不利歸于自己的負面結果。盡管對程序違法的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則應有內涵,但是對被告人而言,其關注的重心往往在結果的正義而不是程序的正義。如果訴訟權利受損但是沒有達到影響判決的地步,發回重審不會導致結果變化,被告人會認為發回重審沒有意義。“如果因程序瑕疵所提起之第三審上訴獲得撤銷原判之結果者,則此種上訴之意義并不大。因為在新的、不再犯形式錯誤的審判程序中,通常也還是會得到相同的審判結果” [2];另外,發回重審會使審判周期延長,如果被告人處于羈押狀態,則羈押期限也相應延長,因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對被告人處境而言并無益處,容易造成法院犯錯,卻由被告人來承受不利后果的不公平現象[3]。最后,如果上訴是被告方提出程序違法導致二審發回重審,被告也當然擔心原審法院是否會對其不利。由此,在各方權衡之后,盡管被告人對程序違法有異議,但是為了明哲保身,往往對形式性的訴訟權利予以忽略而希望追求實質效果。但即便如此,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也并不認可被告人的此種選擇。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國二審實行全面審查,上訴法院對實體程序問題一并審查,不管被告人有無提出;二是法院發現程序違法符合法律規定可以直接做出發回重審的裁定,無需取得被告人同意,被告人對程序違法的發回只有被動接受而無選擇權。endprint
二、建構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的指導思想——公正、效率刑事訴訟的根本價值是公正價值與效率價值,公正主要通過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來實現,二者應當在根本上滿足社會對于正義的需求;而效率則要求司法投入與產出比是經濟的,在刑事訴訟法律體系中,建構與評價皆以此為基點;基于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制度,也應緊密圍繞公正與效率來設置,由于基于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制度主要包括發回重審的條件的設定與發回重審的程序設定的內容,由此,若要建構該發回重審制度,必須以兼顧實體公正、程序公正、效率價值的實現為指導思想,來設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條件和程序。
(一)在發回重審的條件上,必須甄別程序違法對公正的影響
關于對程序公正的影響,由于程序規則本身的紛繁復雜與類型多樣,有些程序規則事關被告人的重要訴訟權利,違反它們,會影響程序的公正性;而有些程序規則只是一些技術性、操作性規定,無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違反也不會影響程序的公正性;即使有些事關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規則,也并非被違反就會侵害被告人的權利、影響程序的公正性,有時候雖然形式上違反了規則,但實質上這些規則所要保障的利益并沒有因此而受損。比如,如果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應該在起訴書中記載控方全部證人的情況,而檢察機關遺漏了部分證人的情況沒有記載,但是在庭審前主動將這些被遺漏證人的情況告知了被告一方,那么雖然該程序規則與被告人的權利有關,但是該規則所要保障的利益實際上并沒有受到損害。
而在影響實體公正方面,程序違法也并非都會影響實體公正。比如,法官在庭審中允許傳聞證人出庭作證,但在判決中并沒有以該證據作為裁判的依據,在這種情形下,程序雖然違法了,但是并沒有影響實體公正。
在程序違法既不會影響程序公正又不會影響實體公正的時候,發回重審顯然沒有實際意義。并且,由于發回重審對國家來說要耗費更多的訴訟資源,對被告人來說要增加訴訟成本與風險,因此發回重審必定會損害效率價值的實現。“程序不公平并不必定導致錯誤的結果。因而有人會懷疑,如果并無錯誤,基于程序理由而撤銷判決究竟合不合理……但由于重新審判直接成本不小,所以如果上訴法院認為程序錯誤不影響結果是一種無害的錯誤,則有權維持原判。”[4]
(二)在發回重審的程序方面,發回重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因此必須保證重審在程序和實體上都不背離公正性的要求
為此,不能將重審的法院僅僅限定為“原審法院”,而應該根據審理的需要做相應變通。另外,為了防止頻繁發回重審導致影響效率價值的實現,應該明確發回重審裁定的效力、限定發回重審的次數、尊重被告人對是否發回重審的選擇權等。
由于公正與效率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價值,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是據此來建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這在發回重審制度的核心內容,即發回重審的條件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各國將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實質條件均規定為程序或實體視角的有害錯誤,即程序違法嚴重影響程序公正或者可能影響實體判決。
就德國而言,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程序違法屬于法律規定的絕對上訴理由,一個是程序違法對判決產生影響。屬于絕對上訴理由的程序違法包括:不公開審理之理由不充足;法院越權行使管轄權;應出庭者缺席;不合適(該回避或撤換)的法官參審案件;法庭非法決定并明顯限制辯方權利;沒有在法典第275條所規定的時限內簽署書面判決等。這些理由都屬于特別重大的程序違法事由,不需要判斷其是否會影響判決而直接發回;按照德國學者的解釋,這是因為這些程序違法顯示該訴訟程序的法治國家基礎已全然未受維護,也就是說這些程序違法導致程序不具有基本的公正性[2]。
根據德國法院的解釋,對于程序違法對判決產生影響是,指只要法院的程序錯誤對定罪或量刑有可能有影響,該判決就是基于程序錯誤做出的,即是說,一項錯誤只有當審判法庭犯與不犯這一錯誤做出的判決在邏輯上都不可能有所不同時,才被認為是無害的[5]。
而在美國,程序違法是否發回重審需要接受無害錯誤規則的檢驗,程序違法屬于無害錯誤的,不需要發回重審,只有程序違法屬于有害錯誤的,才會導致發回重審,因此程序違法達到有害錯誤的程度就是發回重審的條件。而判斷程序違法是否屬于有害錯誤有兩個判斷標準:一個是嚴重影響程序公正性標準,一個是影響判決標準。嚴重影響程序公正性標準,按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說法就是“這種錯誤影響審判程序的建構框架,它剝奪了對被告人的基本保護,沒有這些保護,刑事審判不可能可靠地履行其作為確定有罪或無罪的工具的職能,而且任何刑罰都不可能被認為是基本公正的。”Neder v. United States,527 U.S. 1.8-9(1999).換言之,已經出現的程序錯誤直接影響到訴訟公正的根基,就如同一個殺人行為,我們并不首先探究其殺人的原因,而是直接否定殺人行為的合法性質一樣。因此無需進行無害錯誤的檢驗,而是直接作有害推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顯示這種錯誤是憲法性錯誤中的影響訴訟結構的錯誤,主要包括下列情況:對被告人的辯護權予以全面剝奪;法官和律師在訴訟中有利益沖突;法官沒有被賦予權力但是其主持選擇了陪審團;巴特森錯誤和大陪審團遴選方面存在種族歧視;對陪審團排除不適當;不允許被告人行使自我辯護權;不允許陪審團參與審判;法庭對合理懷疑做出錯誤指示;法庭拒絕快速審判或公開審判;不允許被告人選擇律師等[6]。
影響判決標準是指“如果一個人不能相當確定地說,在考慮了所有情況之后,該錯誤在陪審團做出裁決時沒有產生重大的或者損害性的效果或影響,那么該錯誤就是有害錯誤。”[6]364根據該標準,只有程序違法對判決有可能產生實質性影響,才屬于有害錯誤,才需要發回重審。該標準主要適用于除憲法錯誤中結構錯誤之外的其他程序錯誤。
在日本,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理由是出現了法律規定的絕對控訴理由和相對控訴理由的程序錯誤。絕對控訴理由是違反法定程序的重大錯誤,該錯誤無論是否對判決有影響,均必然致原判決自動被撤銷并被發回重審。絕對控訴理由包括7種情形:錯誤管轄;不適當的法官參與審判;判決法院組成不合法;違反審判公開;對公訴的違法受理與不受理;判決懈怠與越權判決;缺失判決理由或理由自相矛盾。而對相對控訴理由,法律原則性規定為其他明顯影響判決的程序錯誤。明顯錯誤是判斷相對控訴理由范圍的關鍵。從日本的判例來看,錯誤是否明顯給判決帶來影響,取決于如果不是因為訴訟程序違反法令,就可能做出與現在判決完全不同的判決 [7]。endprint
我國臺灣地區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前提條件是:程序錯誤屬于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以及對判決產生了影響。而其他程序錯誤,只有在對原判做出產生影響時,才會導致原判撤銷并被發回,發回與否是基于程序錯誤與判決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8]。
另外,由于發回重審會影響效率價值的實現,因此為了盡量限制發回重審,許多國家和地區規定發回重審除了前述條件之外,還需要滿足程序違法原則上已經在原審被提出過異議——即當時異議規則。
美國為了防止被告人懈怠行使訴訟權利而后又濫用訴訟權利,對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條件在無害錯誤規則之外,還在程序上作了限制性規定:即被告人應在原審法院對程序違法予以提出,若是在原審中沒有提出,原則上喪失在上訴法院提出的權利,如果在上訴中才提出程序違法尋求救濟的要求,上訴法院不能將案件發回重審,此被稱為“當時異議規則”或“未提出視為放棄規則”[6]267。在德國,立法及判例均也體現了這一點。立法上,可詳見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38條有關法庭組織不合法以及有關回避作為上訴理由的規定。例如,若以回避申請權受限制為由上訴,應當要求“因為偏袒之虞法官、陪審員被要求回避時,申請或者被準予或者被錯誤地駁回后,該法官、陪審員參與了判決”。判例上,依照聯邦最高法院的一向見解,認為如果法院并未依《刑事訴訟法典》第238條第2項做出裁定,則對一錯誤的案件指揮命令表示不服的法律救濟程序的權利也不存在,例如審判長對一證人不予宣誓時,只有當被告人或其辯護人在審判程序中對此表示不服,且曾請求法院裁判時,才得以此提出第三審之上訴[2]596。再比如在法國,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05-1條規定,除終局確定的移送裁定書排除的無效原因之外,以法庭辯論之前進行的程序有其他無效原因提出的抗辯,必須在審判陪審團一經最終組成時即予提出,否則,因逾期而喪失權利。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規定,對當時異議也有要求,如在輕罪案件中,如果無效事由并未在上訴法院提出,那么在最高司法法院便不得援用一審程序中發生的無效事由,即是說在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的依據必須在上訴法院被提出或者在上訴法院出現了該程序違法事由。
在發回重審的程序方面,也非常明顯受到公正效率價值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其一,其他法院可以作為重審法院——在日本、德國均有發回重審除原審法院外,其他同級法院也可作為發回重審法院的規定。詳見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54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413條。
其二,為了保證違法經過重審能夠得到及時糾正從而提高訴訟效率,規定發回重審的裁定對下級法院具有法定約束力。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58條規定接收發交案件的法院,在作裁判時應當將撤銷原判決時所依據的法律評斷作為依據。而日本法律直接規定上級審法院的判斷,在該案件的范圍內對下級審的法院有約束力。所以,接受發回重審的法院在重審中應當按照撤銷判決的內容來履行程序。一旦據此作出裁判,其反過來對上訴法院也有約束力,當然這個裁判是在遵守上級或最高法院撤銷判決時所為的法律判斷基礎上作出的 [7]231。
其三,發回重審只有一次,重審后仍有違法的,則只能自行改判。比如法國《司法組織法典》第131-4、131-5條規定,如果第二次提出的上訴依據的理由與第一次上訴時援用的理由相同,并且涉及的是以相同資格進行訴訟的相同當事人,那么,第二次提出的上訴應當由“最高司法法院全體庭”直接裁判。
縱觀各國有關規定,基本圍繞影響公正效率的相關元素設置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在條件與程序的具體規范中也較完整、周全地考慮了影響公正、效率的方方面面。
三、我國刑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的理性重構我國現行的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基本體現了實體公正、程序公正、效率價值。比如將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條件規定為直接發回和可能影響公正審判兩種,就體現了立法者兼顧上述價值的期望。但是,現行的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并沒有很好協調實體公正、程序公正、效率三種價值之間的關系,這種矛盾在立法司法上皆有體現。比如在發回重審的條件上,由于法律列舉的直接發回重審的情形不全以及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判斷標準不明確,導致不利于實現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價值;由于法律沒有將發回重審的程序違法限定為在原審中被及時提出過異議的事由,導致不利于實現效率價值;再比如在發回重審的程序上,由于法律將發回重審的法院限定為原審法院,導致不利于實現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價值;由于法律沒有對發回重審裁定的效力、發回重審的次數等做出規定,導致不利于實現效率價值等。
針對我國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存在的問題,為完整體現刑事訴訟的公正、效率價值,亦應該從發回重審的條件和程序兩個方面重構我國的基于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
(一)重新合理設置發回重審的條件
2012年《刑事訴訟法》針對程序違法發回重審所設定的條件包括直接發回與可能影響公正審判兩種,直接發回因屬列舉式所以非常確定,但是可能影響卻有賴法官根據違法情形予以判斷,不管哪一種方式,都表現出立法者希望公正與效率兼顧的立法理念,但是僅就立法本身而言,由于所列舉的違法事由太過狹窄,也由于可能的判斷標準非常不明晰,所以欠缺對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問題的準確定位。
重構我國發回重審的條件,應當從下述三個方面入手:
1.列舉式違法事由的范圍應當進一步擴大
很顯然,正當程序、公正審判所要求的程序要素遠遠超過合法的審判組織、回避制度、公開審判幾種情形,從各國的經驗來看,至少還有下述程序違法會從根本上傷害審判的基本訴訟結構:如案件管轄權錯誤(但此點在實踐中可能較難實現,原因在于我國刑事訴訟中并無有關管轄權異議的規定);關鍵出庭證人缺失;判決的說明理由不充分等。若是具有這些事由之一,也應當直接發回重審。此外,對于當事人重要訴訟權利的剝奪限制也應該作為列舉式范疇而不應交由法官裁量是否“可能影響公正審判”,如被告人的辯護權被限制剝奪,使被告人喪失自我保護的權利很明顯不是可能影響公正,而是必然會導致不公正(特別是程序不公正),現行法把這類事由作為“可能影響”的情形很不嚴謹。endprint
如果立足我國現行法規定來化解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困境,則如何判斷“可能影響公正審判”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列舉式程序違法只要存在就發回,法官無需再行判斷,但是我國還有大量程序違法需要法官判斷與公正審判的關系,所以重構我國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關鍵在于明確“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判斷標準。上文對德國、日本、美國的相關介紹可以為我國重構提供借鑒:判斷其他程序違法是否影響公正審判主要是看該程序違法行為是否對原判決有影響,如果有影響則發回重審,如果沒有影響,有無程序違法原判決都一樣,則不發回重審。
但是如何判斷程序違法行為是否對原審判決產生影響呢?有關此點,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有因果關系標準和正確結果標準之分。如果程序違法與判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則是因果關系標準——即在程序違法條件下做出的判決,與沒有程序違法做出的判決如果不同,那么很明顯原判決受到了程序違法的影響,該案件就應發回重審,反之,就不予發回;德國、美國、我國臺灣地區采用這種判斷標準。
而正確結果標準則是將程序違法所產生的證據剔除,再審查其余證據對原審判決做出是否足夠支持,能夠支持的,程序違法便沒有影響原判,反之,便是產生了影響。1979年《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可能影響正確判決”便是出自這種理念。
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因果關系標準對程序違法持非常嚴苛的立場,法院裁判盡管正確,但是只要程序違法影響到了該裁判的形成,都是對公正審判造成了影響,所以就構成發回重審的理由;此標準對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價值的關系給予了較好的平衡。而正確結果標準完全以結果的正確與否作為度量,是標準的程序工具主義思維。只要結果正確,程序違法可做無害處置,就不影響公正審判,對程序違法可以持寬容甚至認可的態度,當然,如果結果有誤,也可以因程序違法發回重審。
考慮到我國刑事司法中長期存在“結果正義”的觀念,“正當程序”理念較為薄弱(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的有關改革任務對正當程序有較積極的立場),如果仍然以正確結果標準來抹煞程序違法帶來的權利侵害,將直接損害司法公正;所以在判斷程序違法“是否對原審判決產生影響”上,應明確確立因果關系標準。
2. 發回重審標準應當統一
為了程序違法發回重審制度內部的協調,應當規定在二審程序、審監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中,針對程序違法行為,有關法院均可根據法律規定以直接發回的標準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標準作出相應處理,由此,可以避免同一程序違法事由在不同程序中可能出現不同結果的情況。
3. 當事人應在原審中針對程序違法提出異議
該條件主要要求當事人在刑事訴訟中應當積極主動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如果在原審程序中當事人已經明知程序違法但卻不提出異議,而是在原審結束后再上訴,則理應予以必要程序限制。所以,應將發回重審的程序違法限定為“原則上已經在原審中被及時提出過異議的”事由。
不過,為了維護程序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對該規定須有兩點例外:一是對于一些明顯的重大的程序違法,即使被告人沒有在原審法院及時提出異議,二審法院出于維護程序公正的考慮,也應該以其為由發回重審。這里的重大程序違法主要是指那些屬于公正審判不可缺少的要素從而可以直接推定為影響公正審判的事由;二是對于沒有辯護律師幫助的案件,即使被告人沒有在原審中對程序違法及時提出異議,二審法院也應該以此為由發回重審,只有在有辯護律師幫助的情況下卻沒有在原審中對程序違法及時提出異議的,二審法院才不能以此為由發回重審。之所以做此種限制是因為被告人能否及時對程序違法提出異議取決于其是否有能力及時提出異議,而程序是否違法屬于專門性的法律問題,大多數被告人并不具備該法律知識,因此如若沒有辯護律師的協助,以被告人一己之力很難發現程序違法,因此為了維護對被告人的公平性,應作為例外。
(二)合理設置發回重審的程序
發回重審程序主要圍繞重審法院范圍擴大、明確效力、次數限制、被告對重審有選擇權來設置。
第一,法律應當允許除原審法院,其他同級法院也可收受審理發回重審案件,這對于公正審判無疑會產生積極影響。
第二,重審的法院對上級法院所表明的理由應該完全遵照執行,尊重上級法院對發回理由的法律評判。
第三,發回重審的次數應該與其他情形發回重審的同步,如果重審仍做出和之前無異的裁判,上級法院不得再發回重審。
最后,在我國的刑事訴訟再審模式下,考慮到被告人極有可能在再審中獲得不利后果,可以規定有權發回重審的法院在做出發回重審裁定前,征求被告人意見,允許其選擇是否發回,但是該選擇只在“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程序違法情形中適用,對于重大程序違法,已經直接影響到訴訟公正的程序違法,被告人沒有選擇權。ML
參考文獻:
[1]陳衛東,李奮飛.刑事二審“發回重審”制度之重構[J].法學研究,2004,(1):115-132.
[2]克勞思·羅科信.刑事訴訟法[M].吳麗琪,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52.
[3]汪海燕.論刑事程序倒流[J].法學研究,2008,(5):129-138.
[4]邁克爾·D·貝勒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M].張文顯,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78-79.
[5]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事訴訟程序[M].岳禮玲,溫小潔,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6]約書亞·德雷斯勒,艾倫·C·邁克爾斯.美國刑事訴訟法精解:第2卷·刑事審判[M].魏曉娜,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367.
[7]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訴訟法:下卷[M].張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229.
[8]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269.
Abstract:The practice of remanding judgment caused by criminal procedural violation in China has some problems in retrial conditions and retrial procedure. The principal reason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ocedural justice, substantive justice, the efficiency of value is not properly handled. It is urgent to reconstruct the remanding system based up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procedural justice,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criminal procedural violation; remand; procedural justice; substantive justice; efficiency
本文責任編輯:周玉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