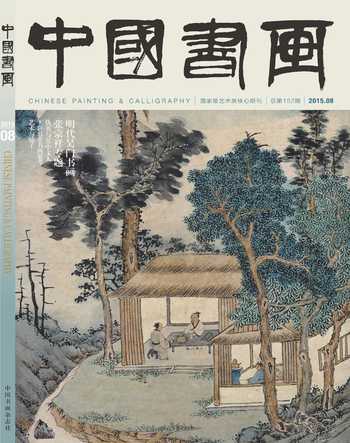“四山”摩崖刻經的人文品格
紀學艷
當代書法看似繁榮,其實繁榮的表象下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所在就是文化性的缺失。
當下書法創(chuàng)作在技術層面上達到了一個相對的“高度”。無論是章法的安排、結構的經營、筆觸的豐富性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除卻這些外在的表現(xiàn)之外,卻再難以找到文化層面的支撐。簡而言之,當下書法創(chuàng)作“空有一副好皮囊”,毫無文化感、厚重感。另外,當F的書壇是書風橫向復制的時代。這種書風主要以“技術流”“精細化”為表征。拼接、染色,千篇一律,人們也逐漸對這種境遇表現(xiàn)出了視覺疲勞、審美疲勞之感。
當我們審視古人書作的時候,總能體現(xiàn)出作者的那種精神境界,以及藝術的真誠感。書家的深厚哲學、美學底蘊總能流淌于筆下,映現(xiàn)在觀者的眼前筆者呼吁,書法家們在書法取法上要更加多元化,更加富有“正大氣象”,更加富有“人文內涵”,要在作品中體現(xiàn)書家的思想和審美追求,要有厚重的文化之感。鑒于此,鄒城“四山”摩崖書法石刻給了我們一個絕佳的參考。
“四山”摩崖刻經書法產生于北朝時期。它的出現(xiàn)和宗教、文化、政治息息相關。
魏晉以降,至于南北朝,佛教得到快速發(fā)展,影響到中國文化藝術豹所有層面,書法藝術最為顯著。北朝更是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亂的時代,同時也是文藝和宗教蓬勃發(fā)展的一個時代。北朝處于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一個關鍵時代。由于政治上的動亂,導致這個時代的藝術不拘一格、天真爛漫而變化多端。對于書法藝術而言,更是如此。北朝石刻如繁星一般在藝術的天空之上熠熠生輝。在這些藝術品之中,而北朝摩崖刻石則屬泰山金剛經、鄒城“四山”摩崖等最為神妙。
在北朝,佛教共經歷了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滅法事件,讓信仰佛教的僧俗人眾對此深有憂患:“以為縑緗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所以,僧侶們把目光投向自然的大山大川,寄希望于佛家經義永垂不朽。鄒城尖山刻經的《石頌》亦有“縑竹易銷,金石難滅,托以高山,永留不絕”之詞句。“四山”摩崖刻經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四山”摩崖刻經整體的藝術風格,追求刻于大山、大川上的經文與整個大自然環(huán)境渾然一體,同時,也與人的心靈渾然一體,創(chuàng)出一個有生命的自然整體。“走向自然”的哲學底蘊在這樣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詮釋,從而更加顯現(xiàn)出歷史是公正的:北朝“滅佛事件”雖然對佛教的發(fā)展產生了劇烈的影響,卻也使書法藝術沖出雅室殿堂,走向大自然。這是天、地、人在書法藝術精神的真正合一之作,是對書法史的巨大貢獻。
在“四山”摩崖石刻中,鐵山的文字刻經場面最為博大,氣勢恢宏,也是四山中最受推崇的作品。在該山摩崖中,佛經書法以隸為主,并參以楷法,結構奇特,雍容有度,開張險峻,寬闊空靈,創(chuàng)造出書法史上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崗山摩崖刻經書法藝術風格與鐵山刻經差異較大,《佛說觀無量壽經》以隸意為主,樸實豐茂,圓腴敦厚,神韻飛動。《入楞伽經·請佛品》則楷意結體、方正規(guī)矩。散刻《入楞伽經請佛晶第一》則隸楷相間,筆鋒外露,奇譎瑰麗,富有變化。葛山刻經隸楷相間,立意奔放,富有神韻,與鐵山刻經筆意相通。
在這樣的作品面前,我們能感受到書家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的那種對天地自然的敬畏,對宗教信仰的虔誠之心。這是藝術創(chuàng)作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也是文化性的魅力所在。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四山”摩崖刻經,多是擘窠大字,佛號、佛名更以橫空出世之奪人氣勢刻出巨壯之字。由于字大,寫手水平高,加之四山巖石載體略軟,刻工未以刀工掩筆法,這樣就為摩崖書跡傳達出神來之筆意創(chuàng)造了條件。楊守敬稱“四山”摩崖石刻:“云峰山鄭氏諸碑尚覺不及,自非古德,命世英才,安能有此絕詣哉。”康有為稱其書“通隸楷,備方圓,高深簡穆,為擘窠之極軌也……安開隋碑洞達爽開之體”。
當我們佇立在四山摩崖石刻之下看到的是其的點畫、結體、風貌的震撼人心的效果。其書法藝術隸楷相間、方圓兼?zhèn)洌艠阈蹨啠P斷意連。再加之刀法的修飾、風雨的侵蝕,自然條件的影響,使摩崖書藝術的效果欣賞起來別有一番風趣。自清代以降,書家們在書法創(chuàng)作開始強調“金石氣”,“四山”摩崖石刻的“金石氣”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具學習楷模必要的摩崖刻石之一。
佛法的感召之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書丹者對書法的虔誠,對宗教的虔誠,也能看出那種萬法無定、能合能離的迷離空有之感。那種大氣磅礴、寬仁大度,不拘細節(jié)的心胸躍然石刻之上。面對山體構思時的物我兩忘,面對蒼天揮毫時的若入無人之境,目空一切的氣魄、不計工拙與后人評藻的無欲之感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就是人文品格在書法作品中的具體顯現(xiàn)。
在20世紀80年代的“書法熱”興起一直到90年代末,對“四山”摩崖的取法—直存在于書壇,并涌現(xiàn)出了很多佳作。然而,自ZI世紀初期開始流行的“二王”帖系書風占據(jù)主流,以摩崖刻石為代表的書法受到了輕視。筆者認為,重新審視、整理“四山”摩崖刻石的書法藝術價值,將為促進當下書法均衡發(fā)展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