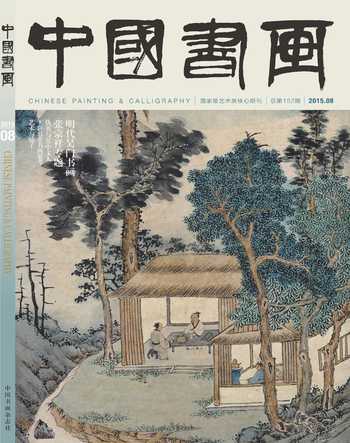藝術與鏡子
彭鋒

將藝術視為鏡子,是一個典型的歐洲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然而,這個觀念背后蘊含的深刻意義,卻被哲學家從一開始就遮蔽了。柏拉圖從將藝術視為鏡子的觀念中,看到了藝術是現實的影子,從而形成了主導西方藝術理論的模仿說或者再現說。藝術與現實,看上去一樣而實際上不同,因為藝術只是制造現實的假象,目的是欺騙小孩和愚人,因此柏拉圖號召將藝術家從他的理想國中驅逐出去。這當然是柏拉圖的一廂情愿,沒有多少人拿它當真。文藝復興時期將藝術視為鏡子'突出的是藝術對現實的認識功能:藝術是對現實的真實反映。這種看法,—直影響到今天。然而,它從._開始就錯了。其實,只要任何一個用過鏡子的人稍微反省一下自己使用鏡子的經驗,就能立即明白它的錯誤所在。
人為什么要用鏡子呢?當然是為了認識自己,而不是認識世界。我們舉著鏡子向內照自己,而不是向外照世界。柏拉圖從一開始就將鏡子的方向顛倒了。那種將藝術視為轉動著鏡子映照周圍事物的看法,實在是荒唐可笑。只有瘋子和無聊透頂的人才會舉著鏡子到處照人。我們睜開眼睛就可以看見周圍世界,舉著鏡子映照世界簡直是多此一舉。如果藝術真是像鏡子那樣,是對現實的映照,那么它們就真的是毫無用處,完全可以將它們從理想國中驅逐出去。我們之所以需要鏡子和藝術,因為需要認識自己。
認識你自己,這是一句古希臘箴言,也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座右銘。人的目光天生向外,能夠看見外部世界,但無法看見自己,這就使得認識自己變得尤其困難。為了解決這個困難,人類發明了鏡子。當人最初通過反射看清自己的時候,可以想象他會有多么吃驚!傳說中美少年納西斯因為看見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不能自拔,茶飯不思,最后憔悴而死。由此可見,習慣認識外物的眼睛,一旦認識了自我之后,是多么的狂喜!柏拉圖錯過了藝術作為鏡子這個隱喻背后的這層含義,是多么的可惜!也許由于柏拉圖是男性的緣故,不屑于使用鏡子對于鏡子的作用沒有多少心得。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就嘲笑過那些成天涂脂抹粉的女人,認為那是騙人的小把戲。哲學要探究真相,不應該沉湎于假象之中。鏡子能夠幫助我們認識自己,但我們在鏡中看見的自己,是真實的自己嗎?
當我們將藝術視為鏡子的時候,強調的就是藝術對現實的忠實反映。如果我們將鏡子轉向自己那么鏡像也就是自己的忠實反映了。柏拉圖已經發現,鏡中的映像跟現實是兩類截然不同的東西。兩千年后,拉康發現鏡中的自己,其實并不是真實的自己,而是自己的影像。嬰兒最初在鏡中辨認出自己的時候,實際上是將自己等同于一個他者。從這一刻起,人就是根據他者來不斷地建構自我。
當我們認識到像鏡子一樣的藝術,其作用并不是認識世界,而是認識自我的時候,內心的狂喜何等地難以自制!但是,當我們認識到鏡中的自我并不是真實的自我之后,先前的狂喜就會煙消云散。如何才能認識自己呢?如果認識自己就像“對鏡貼花黃”那么簡單,它就不會成為一個哲學難題。
到這里,我們面臨了一個困境:將鏡面朝外,自然無法認識自己;將鏡面朝內,雖然能看見自己的映像,卻又無法得到真實的自己。沒有比這再讓人苦惱的了。讓我們來檢查—下,問題究竟出在哪里?緣何認識自己是如此艱難?盡管我們將鏡面轉向了自己,但并沒有改變認識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說,我們仍然像認識世界一樣去認識自己,仍然將自己當作一個對象,當作一個他者。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通過鏡子看到自己的影子這個影子并不是自己'而是一個他者。
我們不能用認識他者的方法來認識自己,否則即使認識到了自己,也是一個他者。那么,是否還存在別的認識自己的途徑?20世紀的哲學觸及這個問題,為我們認識不可認識的自己提供了啟示。
海德格爾曾經感嘆,關于存在的追問,最終得到的答案都是存在者。存在不能成為認識對象,只能自行顯示。由此,存在的意義永遠沒有顯現的窗口,因為一旦存在被言說,說出來的就是存在者。借用《道德經》中的話來說,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但是,人是一個特殊的存在者,人不僅存在著,而且還知道自己正在存在。我們可以將這種“知道”稱為良知,它只指向自身,而不指向對象。由此,人的存在在無需對象化的情況下能夠被人領會,這是存在的意義得以昭示的唯一窗口。梅洛一龐蒂所說的“身體感知”,波蘭尼所說的“默識認識”,杜夫海納所說的“前理解”,實際上都是指一種非對象化的領會方式。人只能在存在之中領會存在,傾聽存在,明白存在,而無法將存在作為一個超出時間之流的對象來打量。
在昭示存在的意義方面,藝術比哲學更優越。盡管哲學家認識到哲學的目的是追尋“事物本身”,但用哲學的方法無法獲得“事物本身”,因為哲學總是反思性的。在反思的哲學中,事物總是第二次出場,是再現而不是呈現。藝術的魅力,就在于它通過制造某種場景,某種氛圍,讓事物于其中出場。《紅樓夢》并沒有分析林黛玉的性格,它只是讓林黛玉自行出場。當然,藝術也存在再現的成分,但是藝術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總能讓某種東西發生,一種甚至連藝術家自己都無法預測和控制的東西,一種海德格爾和阿多諾意義上的“真理”,杜夫海納意義上的“造化”,本雅明意義上的“靈光”。藝術之所以在認識無法認識的自己方面具有特殊的優勢,原因就在于它能夠迂回地讓事物出場。藝術不說自已是什么,也不說自己不是什么,而是讓自己親臨現場。
由此,我們有了三種形式的藝術:一種是將鏡面朝外反映世界的藝術,一種是將鏡面朝內反映自我的藝術,一種是舍棄鏡子親自登場的藝術。前兩種藝術都是再現型的藝術,只有后一種藝術才是呈現型的藝術。在機械復制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只有那種讓事物出場的呈現型藝術,才能避免被機器取代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