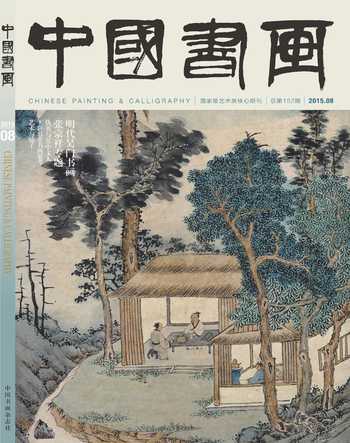生命的寫真
卓今



中國水墨畫里的規定性和偶然性的特征,要求畫家必須有扎實的基本功,才能很好地完成程式化動作,還要求畫家有高妙的藝術天賦才能理解和把握水墨成分里的流動感。需要有把兩種以上對抗的要素融成一個藝術整體的提煉能力和審美高度。陳鈺銘很早的時候練就了_一身扎實過硬的基本功,他不追名逐利,不浮躁,勤奮高產博采眾長,在自己認定的那片藝術天地里精耕細作,無怨無悔。
陳鈺銘的藝術特征非常突出,“可辨識度”很強,尺寸巨大的畫面,撲面而來一股激情奔放的陽剛之氣,大氣磅礴的構圖和造型,極富穿透力的情感力度。用筆樸素、扎實,不驕情,不做作。題材涉獵很廣,有反映軍人生活的軍事題材,有宏大的現實和歷史敘事,也有普通人的日常瑣碎。更難能可貴的是,在當代中國水墨人物畫家中,陳鈺銘是少有的長期在創作主題上注重底層關懷,懷著悲情和憂患,對人性做深刻探索,對生命意識不懈追問的畫家。
陳鈺銘的每一幅創作背后都有許多傳奇,藝術家探索藝術的過程本身醞釀著偉大和痛苦,勞作的同時產生靈感和想象。他常去的那些地方環境惡劣,條件艱苦。有一次在黑峪口寫生,春季黃河改道,人們拽著繩子過河,河水冰涼,河中央浪大水急,上游不時有石頭沖下來,陳鈺銘凍得失去了知覺,冰冷僵硬的手下意識地抓著繩索,一會兒工夫手腳就不聽使喚了,眼看著就要被湍急的河流沖走,旁人使勁地喊他才醒過神來。黃河是他的藝術源泉,也是他的精神家園。他只想把黃河的真正內涵通過黃河人的形象用藝術表現出來,用一些簡單樸素的畫面揭示黃土高原的內在美。寫生的過程也會偶然遇到讓他激動的素材。有一個畫面困擾了陳鈺銘多年,他—直想畫這幅畫,畫的題目都想好了,就叫《母親》。有一年,陳鈺銘到黃河岸邊寫生,天已經黑了,有一群人從船上抬下一副擔架,趟著水到岸上,擔架上躺著一位老太太。陳鈺銘看不清老太太的面孔,只看見被子里露出幾縷白發。這個畫面觸動了他的靈魂,讓他淚流滿面。后來他專門到黃河邊上的叢羅峪古鎮,想找到這樣一位飄著白發的老太太以及她家人的形象,后來又跑到呂梁、太原、鄭州、商丘、沂蒙等地,這個理想的形象—直沒有出現。
成長環境造就一個人的藝術氣質和價值取向。陳鈺銘從一開始就懷著一種悲憫,從現實人手,從人本身去思考,關于人性、精神靈魂、生命意識等主題貫穿陳鈺銘的整個創作。在軍事題材上,早期作品《霜月》 (1987),天空高遠,月掛寒霄,幾個小兵在苦寒之夜蜷縮在一起互相取暖,一位哨兵堅挺地站立著,被風蝕和流水切割的黃土高原浩蕩地向遠處延綿,戰士們所守護的土地家園被象征化、符號化。憂郁清冷的基調,深沉而響亮的色彩,恰好反襯出人物內心宏大的理想和積極的向往。對歷史性軍事題材,陳鈺銘有他獨到的理解。1992年創作的水墨人物長卷《歷史的定格》,篇幅巨大,人物眾多,造型復雜,個性突出。畫面以沖撞減壓式的結構,撇開表面的瑣碎,不玩花招,不耍技巧,對人物進行高度的概括,皴擦點染一切隨人物真實的“情”和“形”出發,呈現出強勁的穿透力,表現出歷史上慘絕人寰的一幕,屠刀和鐵蹄下的死者屈辱的遺體,生者悲憤哀傷的眼神,侵略者意猶未盡的兇惡嘴臉和嗜血本性,生命被肆意地蹂躪、踐踏,整個畫面以鋪天蓋地的氣勢磅礴而來,直逼靈魂,具有超越時空的震撼力,讓人警醒。畫家蘊含著巨大的精神能量,以浩蕩的才情、酷烈的氣息完成了這個鴻篇巨制,激情癲狂之時在精勾細染之間來一點任意揮灑和寫意潑墨,流動中有間歇,有很強的節奏感和韻律感。
現實題材和畫普通人是陳鈺銘最為得心應手的,也是表達悲劇情懷和生命意識最廣泛最深刻的題材類型。有對生命、家園、土地的宏大敘事,如《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二月二龍抬頭》《天籟》等。《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與《二月二龍抬頭》均以恢宏的氣勢表達黃土高原人民的精神風貌,早期的畫有許多是以濃墨重彩來表達人物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和歡慶喜悅的心情。篇幅巨大,人物眾多,以不同的筆墨突出每個人物的個性,內心包藏不住的高興,以及歡喜得近乎悲傷的樣子。夸張的面部表情,肢體的動作幅度很大,整個畫面呈現出跳動奔流的氣勢。
悲情和傷感色彩最濃的要數都市題材。畫家對市民社會相當熟悉,城市小人物是畫家最親近的一個群體。畫家顯然在追求一種單純本色的人類生活,對違背人類天性的東西產生一種天然的反判和對抗。有一些都市題材畫得很出色,有很強的現實批判意義。如《京西六月》《記憶·碎片》《月掛城東》《走出冬季》等。2000年《月掛城東》《京西六月》在深圳國際水墨雙年展展出,雖然那時流行實驗水墨,但寫實手法也一樣受到追捧。這幾幅水墨都市畫從主題上講真正地表達了都市人的內心混亂,精神焦慮,工業文明帶來的人的異化,以及現代性的根本困擾。摩天大樓、機械、廢墟、擁擠的空間,焦灼、沮喪、無所適從的人群,水墨的暈染在寫實的人物和空間上蔓開,從而加厚加重了這種無秩序的混亂的表象,讓人的內心亂象叢生。風格上稍微有那么一點后現代和立體主義的味道。尤其是《走出冬季》,人物凝重的表情,總給人一種走不出這漫長的冬季,走不出無邊的哀傷的感覺。《記憶·碎片》更接近立體主義,水墨的特征,活性、流動、難以把握,有極大的偶然性,用這樣的材料來表達冰冷僵硬的幾何機械圖案,對畫家來說是一個挑戰。人物特征被模糊、抽象,感情被抽空,機械零部件發出寒冷的光,每個部件的背后包含著故事,悲慘的、溫情的、壯烈的、齷齪的,誰又說得清呢?這也許就是都市的真相。
陳鈺銘在大量軍事和歷史題材繪畫中,試圖用現代人的眼光去理解把握人物和事件,避免表面化、概念化,注重對軍人精神靈魂的挖掘和對戰爭做人性、哲學上的思考。這些年來,陳鈺銘通過各種探索完成了個人風格,創立了一套獨特的繪畫語言。他吸收了李伯安的“重”、“黑”、密體、加法,柯勒惠支的悲憫主題、厚實的塊面和疏朗明快的線條,盧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的懷疑、探索,以及粗澀的筆法,基夫的思想者繪畫,用陰暗和遼闊揭示事物深處的美,把感情符號做到極致,倫布朗的明暗、虛實、神秘性和用筆概括,蘇里科夫的宏大構圖和批判性寫實。畫畫到了一定的境界,怎么畫都有道理,如今陳鈺銘已經拋開了技巧,筆墨收放自如,思想自由馳騁。在他的筆下線條表達的是高度概括的對美的信仰,色彩里流淌的是現實、人性的大主題,構圖中包含的是責任感,皴擦點染中蘊藏著的是生命意識和悲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