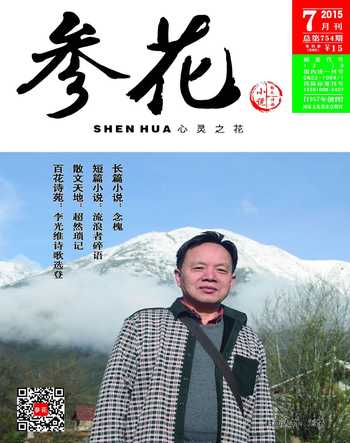曹植樂府詩的文人化傾向
司若蘭
建安時期軍閥割據,戰火不斷,國家不幸詩人興,這一時期也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重要階段,詩歌創作由樂府詩轉向文人詩。曹植是樂府詩文人化轉變的關鍵人物。
一、體裁的創新
建安時代,曹操獨樹一幟,首先以樂府舊題為題,按照兩漢樂府詩歌的風格作詩,之后以三曹為首,文人紛紛效仿。三曹所寫的樂府詩,大部分是不入樂的。曹植也放棄了應曲當歌的作法,并且因情定題,不再受樂府舊題的體裁約束。他極端自由主義的性格促進了這樣的創新。在曹丕稱王之前,曹植雖然也隨父出征,感受過天下的動蕩與不安,但在曹操的庇護之下,他過著優游宴飲的貴公子生活,飲酒作詩,養尊處優,最終形成了放蕩不羈的性格。賈斯榮評價說曹植是一個“浪漫不羈的天真性格的人”。自由的人有著更活躍的思想和更卓越的創造力,曹植能突破樂府固定的曲調,嘗試詩歌新體裁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題材的轉變和形象的塑造
曹植樂府詩內容的轉變促進了樂府體裁的發展。宋人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將其分為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等十二個門類,樂府詩以現實主義的詩風和敘事的手法表現社會,達到了一定的藝術高度。而曹子建在原有的寫實基礎上,將自己的際遇與情感雜糅入詩歌當中,展現了更高的審美價值。
《上山采蘼蕪》以及《孔雀東南飛》在漢樂府中是重要的表現棄婦題材的敘事詩。《上山采蘼蕪》中,棄婦偶遇故夫,兩人的對話敘述了事件經過。以故夫的喜新厭舊突出棄婦的悲劇性,批判了不合理的父權制度。曹子建前期有《棄婦篇》,較《棄婦篇》用詞文雅許多。開篇寫院中石榴綠葉隨風飄動,花紅如火的景象,以光彩琉璃之色形容石榴花開的盛景,運用比興手法,開花未結果的石榴樹是劉勛妻子的化身,而前來撫冀、悲鳴的鳥則是古代社會千千萬萬的棄婦,在父權社會她們沒有地位,無法反抗,被丈夫拋棄后也只能默默哭泣。《棄婦篇》從主旨上看,秉承漢樂府的敘事性,又因為有了具體的詩歌背景,情感哀怨深沉,表達了曹植對其有著不幸遭遇的棄婦們的同情。
由此可以看出,曹植已經不再滿足于簡單的敘事,向表達個人化的情感邁進。他在《七哀詩》中以浮沉對比表現思婦的纏綿情誼,實則表達對兄長的不滿以及被排擠的抑郁與哀傷。
三、表達形式的擴充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詩賦欲麗”,肯定了詩賦嬌麗清峻的語言美。魯迅先生說:“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謂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詩歌亦然。
在建安時期,樂府詩逐步由民間采歌到文人創作,漢樂府詩歌語言質樸,平實率真,敘事清晰即可,而曹植用字精當,意象奇特,想象瑰麗,將樂府詩歌由口語化推向美化和雅化。
曹植的想象瑰麗奇特。在《鰕鱓篇》中,以“鰕鱓”和“燕雀”比喻爭權奪利的淺薄小人。“泛泊徒嗷嗷”化用屈原的詩句“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將執政者比喻為水中隨波逐流的鴨子,只會嗷嗷呼叫。曹植意指曹叡不恤國事,只保全自己名利,同那些庸庸之輩一樣,只知“潢潦”與“藩柴”,不去想世界之寬廣,沒有志士的遠大理想和寬廣胸懷。“長歌正激烈,問者壯之。”這樣壯麗雄奇的想象在漢樂府中是少有的,而曹植將之發展為自己的風格。
此外,曹植還善于利用豐富的意象表現心中的憤憤之情,把充沛如江海的情感通過別出心裁的意象表達出來。“天才所直觀看到的是一個迥然有別于其他人所看到的世界。”天才就是指有著超凡的智慧和清楚認知的人,如果把曹植定義為“天才”,那么曹植眼里看到的事物就不再是表象那般膚淺,他在詩歌中使用的意象也具有更深刻的內涵。
曹植樂府詩中使用的意象豐富,例如“轉蓬“、“桂樹”、“少年”、“黃雀”、等等。在《七哀詩》中,創造的“明月”、“高樓”、“思婦”一組意象成為后代詩歌的范本。以《野田黃雀行》為例,曹植以豐富的意象暗示自己的無助感。“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悲戚的風欺凌高樹,又攪亂海水,樹與水卻又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 兇惡的鷂捕食柔弱的黃雀,黃雀驚惶失措不小心落入網內。高樹、海水還有黃雀都暗示著曹植現在困苦的處境,曹丕欲殺其親信丁儀、丁翼,曹植被曹丕放逐并且打壓,失去了立身之本,自己都無法保證自由,又有什么能力救助友人呢,只能把想象中的少年當成救世主,拔劍砍斷羅網,救助黃雀使之轉危為安。“籬間雀”喻指被禁錮的自己和親友們,無法擺脫被束縛的命運,賦予了眾多意象的新內涵。
曹植也不是一概的標新立異,追求奇絕意象,他繼承了《離騷》中的香草美人和漢樂府中美人喻君子的傳統,在《美女篇》中寫道,“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表達他懷才難遇的憤憤之情。
建安時期,樂府詩的文人化傾向與當時文人的審美標準有密切聯系,曹植的樂府詩也對后世詩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創新與拓展使得漢樂府詩歌逐步轉變為文人詩。
參考文獻:
[1]叔本華.叔本華思想隨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3]黃節.黃節注漢魏六朝詩六種[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責任編輯 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