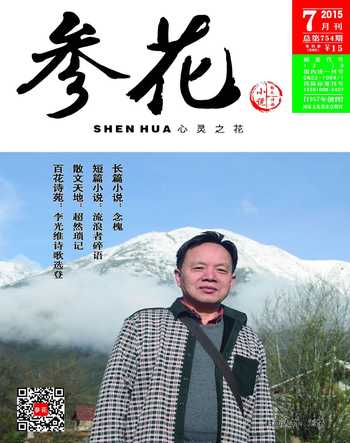繪畫與精神的關系
韓晶晶
用命運多舛來形容柯勒惠支的一生最合適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柯勒惠支18歲的兒子陣亡在沙場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柯勒惠支的孫子又如她的兒子一樣。柯勒惠支悲痛欲絕,她的整個余生都在強烈地憎恨戰爭。她從心底反抗當時社會的黑暗,這也使得她的早期作品塑造了一個個痛苦、悲憤、抗爭、窮困、沉悶的藝術形象。
1931年初,魯迅先生在上海主辦了木刻講習班,課上他拿出柯勒惠支的版畫供學員們觀賞學習。學員們都被柯勒惠支的人物形象、畫面形式所征服;被她所呈現的底層勞苦大眾的困苦、悲痛、絕望所震撼;被版畫黑白分明、看似簡單但又不乏韻味所吸引。從此,柯勒惠支這個名字便鐫刻在了中國版畫家的心里。尤其是在革命美術運動時期影響極為深遠,無論是從創作思路還是表現手法,都借鑒了柯勒惠支的風格,可以說他們間接的都是柯勒惠支的學生。而那次講習班,也成為了新興木刻的開端。后來的八年抗戰,全國都籠罩在戰爭的陰霾下,與柯勒惠支當時的德國形勢不相上下。當時的中國版畫家,承受著在生活上、精神上、創作上的重重壓迫,但他們不畏強權,用刻刀做武器,以柯勒惠支為榜樣創作出了一批批優秀的作品。
柯勒惠支以她博大的慈母之愛,用刻刀做畫筆,創作出了無數幅舉世聞名的佳作,那個悲慘的混亂的時代使她的個人經歷凄慘傷感,但也締造了這么一位了不起的大師。她雖為一個柔弱的女子,但是她的創作卻充滿了男性的陽剛之氣。她選擇了版畫這種表現形式,運用版畫黑白分明的獨特的語言,來訴說人類的災難,她的畫面簡潔概括、情感濃烈、形象剛勁挺拔。她的“剛”不僅表現在畫面上,還隱喻出廣大勞動人民不畏強權展現出勞動人民的“剛”。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動蕩,中國傳統的國畫和油畫,因昂貴的顏料和紙張材料,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失去了它們的光彩,而木刻版畫就自然的蘊育而出。魯迅曾說“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一張木板、一把刻刀、一桶油墨就可以從一幅作品變為無數張,來作為各種刊物和活動宣傳資料。中國新興木刻就是伴隨著革命出生,在一開始它就作為武器來運用。
隨著魯迅的大力倡導扶持和培養,新興木刻就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興起。大批有志青年加入了版畫隊伍中,用一幅幅作品來記錄社會的悲慘,人民的絕望,來抒發對資產階級的痛惡和對無產階級的熱愛。他們以大眾勞動人民為對象,引導啟發大眾,與中國的革命事業緊緊相連,積極推動革命的發展。他們以柯勒惠支為榜樣,披露現實的殘酷,在形式上表現“力之美”,這種藝術語言滲透到了每一位版畫家,形成了初期木刻的總體風格。
中國的版畫,經歷了這三個重要的階段。第一是中國古代時期,當時的版畫完全是為了復制而生。第二是20世紀的新興木刻,這個時期的版畫是與革命相依偎,是革命戰爭造就了它。第三是在建國之后社會主義初期,當時的版畫事業得到政府大力的扶持。隨著我國經濟、政治的不斷發展變化,藝術市場也受到了市場經濟的沖刷。版畫不僅僅局限于木刻,銅版、石版、絲網版畫、麻膠版、數碼版畫等多種綜合版畫出現給版畫藝術增添光彩。版畫也不單單作為宣傳的力量,而是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去接受社會的選擇與評價。
在如今這個藝術多元化,復雜化的時代,藝術品本身也受到了重重考驗。版畫作為歷史悠久的中國藝術,在國內卻并不受青睞,在藝術品市場和國畫、油畫有著很大的差距。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收藏家們覺得版畫是“復制”的缺少“唯一性”,沒有多大價值。另一方面,是現在的很多版畫家過多地注重技法和紋理,出現了許多作品但是很少可以打動觀者。就如中國美協版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張遠帆所說,中國版畫發展到現階段的問題主要是,一些作者仍然停留在對技術、個人風格等層面上,作品制作精良卻不動人。
繪畫中的理想與時代的聯系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時代擁有不同的繪畫精神,正應了“時代造就英雄”的這句老話。戰爭時期,創作題材較單一,版畫大多作為宣傳的工具,傳達著勇于向前、不畏強權的積極向上的理念。和平時期,版畫作為純藝術的存在,加上科技的發展有了更多的技法來創作,題材層出不窮,版畫界有了各種各樣的作品,偏于紋理和技法,也使得有些作品給人感覺缺少點“神”。
參考文獻:
[1]張澤賢.民國版畫聞見錄[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6.
[2]中國新興版畫80年流變[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
*基金項目:西南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型科研項目《繪畫與精神的關系——淺析柯勒惠支版畫與新興木刻時期版畫的關聯》(項目編號CX2015SP277)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學藝術學院學生;研究方向:美術學)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