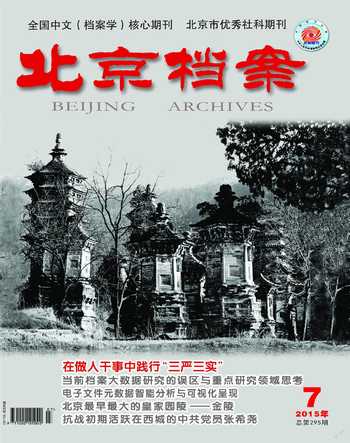抗戰初期活躍在西城的中共黨員張希堯
韓春鳴
張希堯是遼寧省西豐縣人,東北大學理工學院化學系(以下簡稱“東大”)學生,曾經擔任校學生會主席,深得當時校長張學良的器重。九一八事變后,張希堯與大批東大學生流亡到北平。當時,東北大學秘書長介紹給他一份薪水頗豐的工作,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拒絕了,全力以赴投身于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的斗爭中。
張希堯到達北平之后,臨時住在西單舊刑部街12號奉天會館內。在他的請求之下,很快得到了張學良將軍的接見。他與其他學生代表一道向張學良提出要求,立即出兵抗日。同時,提出以流亡北平的東北青年為基礎,成立東北學生軍,訓練抗日骨干力量。張學良表示,要出兵“得聽從中央,當下還要忍辱負重”;但對于成立東北學生軍之事則表示同意。張學良說:“有愿意投筆從戎的,請先行報名,以便將來我和你們一同抗日。”張學良當即決定,將宣武門外的江西會館借給東北學生軍使用,還答應在教官、給養、武器、彈藥、馬匹等方面給予支持。
在張希堯具體組織和領導之下,東北學生軍很快便由最初的四十幾人擴展為二三百人。這支隊伍雖然不帶番號,但按照軍隊建制,編為一個連,下設班、排,由東北軍派出兩名教官負責軍事訓練。學員們身著軍裝,吃的是粗糧,睡的是地鋪,每天一大早兒就進行軍事訓練,訓練的內容包括射擊、投彈、肉搏技術、爆破技術等。此外,張希堯還邀請閻寶航等著名社會活動家作抗日救亡報告。經過嚴格訓練后,這些學生軍大多潛回東北,投身到抗日斗爭的最前線。
1931年9月27日,在高崇民、閻寶航、車向忱等人倡議下,流亡北平的各界人士聚集在舊刑部街奉天會館“哈爾飛”劇場(西單劇場舊址),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簡稱救國會)。由張學良資助30萬元予以支持。救國會的活動宗旨是“抵抗日本入侵,共謀收復失地,保護主權。”張希堯出席了成立大會,并擔任“救國會”執委會委員,在閻寶航領導下的宣傳部(后改為政治部)工作。
“救國會”成立之初,從東北前線過來的人們絡繹不絕,有的要求支援彈藥、物資繼續作戰,有的因為部隊解散來這里尋求出路,還有大批抗日家屬亟待解決流亡生活中的困難。張希堯除了負責東北學生軍的日常工作以外,還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處理和解決這些問題。他每天從早忙到晚,積勞成疾,結果引發肺病,不得不在1932年2月到香山慈幼院進行短期治療。待病情稍有好轉,他便在香山召集有關人員分析和討論時事。一次,為了紀念犧牲的抗日烈士,張希堯和幾十名青年聚集在香山一座塔下,大家流著熱淚寫下:“國事千鈞重,頭顱一擲輕”的誓言,決心用“鐵和血”收復東北失地。為了表達“勿忘淪陷家園”的心情,每個到場的人都吃了家鄉的“高粱米”,喝了“黃連苦水”。
1933年,張希堯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中共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東北大學特別支部工作。同年3月,他與車向忱等人率“東大”慰問團50余人和十多輛滿載慰問品的汽車,前往長城古北口前線慰問抗日戰士。在前沿陣地上,慰問團員們組成救護隊,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用擔架運送傷員,他們的勇敢行為受到前方將士的敬佩。5月,張希堯再次與車向忱代表“救國會”,前往張北前線慰問抗日將士。在那里,他結識了馮玉祥、吉鴻昌等愛國將領。
1934年,張希堯的妻子和孩子也來到了北平,張希堯以“生意人”為掩護,將家安在西城什剎海附近鴉兒胡同15號,一個獨門獨院內。從那時起,這個小院就成了中共北平組織的一個秘密聯絡站。每當地下黨的同志們來家中接頭或者開會時,張希堯就讓妻子龍若蘭帶著兩個孩子到胡同口去“望風”。孩子在胡同口玩,龍若蘭則手拿著針線坐在門口的石頭墩兒上“放哨”。
就在這一年11月,吉鴻昌不幸在天津法租界被捕。消息傳到北平,東北抗日救國會在地下黨組織的支持下,先是設法經濟營救,總共籌得5000多銀元,結果沒有奏效。后來得到消息,說戴笠奉蔣介石命令,要將吉鴻昌從天津押解到北平軍事委員會審理。東救會決定想辦法劫持吉鴻昌。于是,閻寶航特派徐靖遠和張希堯趕到天津,與地下黨組織接頭,計劃在押解途中營救吉鴻昌。但因火車上軍警把守嚴密,特務又給吉鴻昌化了裝,導致計劃未能實現。后來,他們又獲得情報,說敵人計劃就地處決吉鴻昌。閻寶航緊急決定,由徐靖遠負責,實施“劫持法場”行動。他們從北平西山抗日干部訓練班中挑選精干人員,使用張學良去歐洲前留下的精良短武器,準備在敵人行刑前動手。結果,敵人放出的刑場地點和執刑日期是假的,營救計劃失敗,吉鴻昌最終遇害。
就在吉鴻昌遇害不久,張希堯在街上以共產黨嫌疑分子罪名突遭逮捕。當天,憲兵隊闖入其鴉兒胡同家中進行搜捕,把住在他家里的張金輝和王洗塵,以及恰好來訪的寧匡烈等七人全都抓走,憲兵還蹲在家里監視,準備來一個抓一個。張希堯先是被關押在宣武門內國民黨市黨部,后來又被轉押到北平警察局。張希堯毫無懼色,高聲斥責國民黨的投降路線和不抵抗政策,被關在同獄室的難友楊秀峰在他大腿上掐了一下,暗示他要注意斗爭策略。
在獄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敵人多次提審張希堯,甚至給他上電刑,強迫他跪鐵絲網,使其身體遭受到很大摧殘。后來,由閻寶航親自出面,利用他在國民黨新運總會的職務,一直找到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才將張希堯等七人釋放出獄。事后,陳立夫在給閻寶航的復信中寫道:“彼等在吾兄領導之下,即在吾黨領導之下,彼等今后的行止,一切應由吾兄負責處理。”
此時,張學良已從歐洲歸來一段時間,他出于對東北流亡學生的同情和愛護,指示每月從邊業銀行撥1000元交給張希堯,讓其負責救濟流亡學生。
在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下,張希堯和寧匡烈等人向閻寶航建議,從流亡的東北青年中挑選出100多人,由閻寶航擔任班主任,在西山臥佛寺秘密舉辦“西山干部訓練班”,對外則以“學生夏令營”的名義作為掩護。培訓的內容有時事政治、游擊戰術、爆破技術等。張希堯負責訓練班的組織和日常生活安排。
訓練班學員一般分兩組上課;如果進行專題討論,則分成更多的小組,以便縮小目標,易于掩護。由于訓練班的主要任務是培訓潛回東北抗日的秘密工作人員,班上有嚴格的保密規定,如學員之間不準相互打聽真實姓名。即使“救國會”其他核心領導成員,也不知道訓練班的具體內容。訓練班結束后,由張希堯等負責將大部分學員派往東北抗日義勇軍、抗日聯軍,還有一些人被派到冀東一帶的根據地,進行抗日救國活動。
張希堯在大學學的是化學專業,懂得爆破技術的基本原理。當時在燕京大學上學的黃華(原名王汝梅)抗日熱情很高,經常與他聯絡。張希堯曾教他制作簡易的手榴彈,他們用裝香煙的鐵皮罐子做外殼,里面放上炸藥和鐵釘、碎玻璃等,中心空出個小洞,插入一根雷管,是觸發式的,遇到猛烈的撞擊,就會發射出火星,將手榴彈引爆。一天,他們兩人拿著土制的手榴彈,來到燕大附近的圓明園,找到一個無人的地方,將手榴彈投了出去,手榴彈著地后發出巨大的爆炸聲。當他們離開時,看守園子的老頭兒贊許地說:“唔,還真是挺響的啊!”
1935年三四月間,中共北方局在北平建立了中共東北特委,由彭真同志直接領導,張希堯先任群運委員。5月底,因李向之被捕,由他接任書記工作。當時,“東特”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哪里有東北軍和東北集團的社會關系,就在哪里開展工作。為了加強對東北流亡學生抗日活動的領導,完成黨的工作任務,張希堯特意邀請在上海地下黨工作的孫達生介紹開展地下黨秘密工作的經驗。孫到北平后,張希堯陪同他到天津會見了北方局軍委特科負責人南漢宸,后又與李雪峰聯系,研究如何深入到駐扎西北的東北軍內部開展工作,最后決定由張希堯負責在北平分批將中共地下黨員和“民先”隊員派遣到西安,再由孫達生將他們安插到東北軍中,爭取共同抗日。張希堯通過東北軍王以哲軍長的支持和幫助,從1936年2月起,分三批將50多名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派到東北軍中。其中,第一批有20多人,由劉日升領隊,被安排到王以哲屬下的六十七軍教導團。第二批有十幾個人,被安排到董彥平旅的軍士連。后來,萬毅109師新組建一個團,主動要求向該團派一些進步學生,于是張希堯又組織第三批學生共18人,由傅季剛領隊,全部加入到萬部。這三批學生參加東北軍后,加強了黨在東北軍中的力量。
對于往東北軍派遣進步學生的活動,引起了南京國民黨的警覺。當第一批人到教導團不久,南京軍政部即電告東北軍各軍長:“北平共黨張希堯派遣大批共黨分子潛入東北軍,務望嚴密搜查”,同時附上這些人的名單。王以哲將這份電報拿給孫達生看,孫說:“張希堯是‘九一八前你在沈陽的老熟人,是與‘東北甘地車向忱一流的人物,怎么成了共產黨?咱家鄉學生為抗日投筆從戎,學習軍事,怎么也成了共產黨?!”經他這么一說,王以哲松了一口氣,認定這是特務在使離間計。為安全起見,他讓這些學生更名改姓,并很快將他們分散下去。
1937年“二二”事件,王以哲將軍被害,東北軍內部矛盾愈發尖銳,這對中共地下黨的工作帶來很大困難。東北軍中共工作委員會領導人朱理治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建議:“用東北民眾的統一戰線,來推動東北軍的團結”,“重新組織東北民眾救亡會,用群眾的力量來鞏固內部的團結。”
朱的這一建議,得到中共中央批準,周恩來親自部署,將這任務交給劉瀾波和張希堯。周恩來指示,要在東北人中選擇有影響的人士,促使各東北抗日團體聯合起來,以人民群眾的力量推動東北軍抗日。
當時,北平大約有16個東北救亡團體,團體代表聚集到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經過兩次討論,對于建成統一東北民眾救亡團體達成共識,定名為“東北救亡總會”,簡稱“東總”。
周恩來對“東總”籌建工作十分關心,做出具體指示:“先在上海開籌備會議,再去北平開成立大會。”據此,張希堯與高崇民、劉瀾波等人于四月專程從北平前往上海,會同閻寶航、李杜、李延祿等人在八仙橋青年會召開了東北救亡總會籌備會議。會議由高崇民主持,有200多人參加,確定了“東總”關于擁護國共合作,共同抗戰;營救張學良將軍;聲援東北抗日聯軍等三項任務。會后,印發了《告東北同鄉書》。
1937年6月20日,經過多方努力,“東總”在北平西城崇元觀5號東北大學禮堂召開成立大會,到會者近千人。經過選舉,張希堯任該會常務委員和組織部副部長。會上,許多代表還在一塊以東四省地圖為背景、上面寫著“打回老家去”的布上簽名,表示共同抗日的決心。為保證“東總”能夠按照中共組織的指示開展抗日工作,在“東總”成立同時,還建立了中共東總黨組,由劉瀾波任黨組書記,張希堯、趙濯華、宋黎、栗又文、王一夫、于毅夫等為黨組成員。
“東總”成立后不久,就爆發了七七事變,北平失守。在中共北方局指示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將干部疏散到魯西北、冀南、太行等地,繼續與敵人進行斗爭。張希堯作為領導人之一,具體負責包括確定疏散人名單、寫介紹信、安排日程等項事宜。
為了避人耳目,張希堯先后將家搬到德勝門內高井胡同(門牌號不詳)和西直門內牛角胡同2號等處。同時,為了安全起見,還規定了來人接頭的聯絡暗號。例如,安全時即在院門兒旁邊戳一根竹竿,遇到情況就將竹竿拿開。
中共北方局指示東北特委,將工作重點轉向北平郊外,組織力量進行武裝斗爭。此時,國民抗日軍的趙同找到張希堯,希望能幫助組織人力,補充到他和高鵬、紀亭榭在京郊(現昌平西白羊城村)組織的隊伍中。張希堯與高鵬是東北大學同學,與紀亭榭和趙同也早有交往,他明確表示支持他們組織抗日武裝隊伍,先派地下黨員閻鐵、徐明兩人到這個當時只有二十來人的隊伍中了解情況。同時聯系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由張希堯具體聯絡,選派汪之力、史進前、張如三等地下黨員,以及民先隊員和從東北軍撤退回來的學生兵等十幾人參加國民抗日軍,分批由紀亭榭帶出城。臨行前,張希堯向紀交代:一要保證這些人的安全;二要給予工作上的方便;三要安排適當的職位。所以,派出去的這些人到部隊后先后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如汪之力當時擔任國民抗日軍的軍政委員會秘書長),發揮了骨干作用,使這支隊伍在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下,真正高舉起抗日旗幟。1937年8月底,國民抗日軍出奇兵夜襲德勝門外第二監獄,共繳獲四十多支槍,營救出二三十名政治犯和數百名“犯人”。獲救者除老弱病殘外,大多數參加了游擊隊。1937年底,隊伍奉命西進齋堂,而后與在蔚縣的楊成武所領導的八路軍會師,繼而到阜平,接受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軍區的整訓,此后改編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五支隊,在平郊的西山開辟平西抗日根據地。新中國成立時,從這支隊伍中走出了一大批我黨高級干部和開國將軍。如曾經擔任北京市市長的焦若愚,總政治副主任史進前、海軍航空兵參謀長紀亭榭等。
張希堯則在1950年11月,因積勞成疾,不幸在沈陽逝世,終年45歲。黨和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