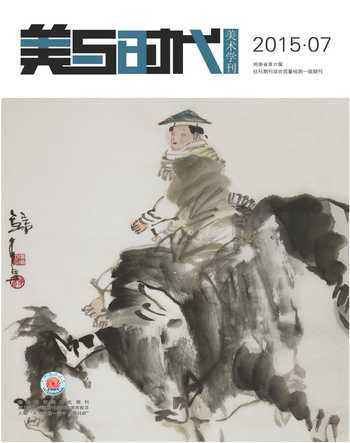山水畫中點景人物的功用
摘 要:點有點綴修飾之義,點景人物作為在整幅作品中起到點綴作用的人物,占具了極少部分的篇幅,但卻是畫面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它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和在作品中的作用。點景人物不僅可以為作品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同時借助點景人物的活動也可以為畫面營造出可游可居的藝術效果,讓原本缺乏靈氣的山水畫增添一絲生活樂趣和隱逸情懷、畫家可以將自身的情感通過點景人物很好的表達出來,對于自己仕途的郁郁不得志,對于社會動蕩的不安,對于安逸生活的向往以及對于周游列國的渴望,等等一系列的情感,在點景人物身上都有很強烈的個人映射,點景人物一方面為整幅作品服務,另一方面又承載著畫家自身的個人情感。
關鍵詞:山水畫;點景人物;點景人物;營造效果;情感傳達
一、經畫家之手“點”作品主題
《芥子園畫譜》中對于點景人物的功用有這樣的描述:“今將行立坐臥觀聽侍從諸式,略舉一二,并各標唐宋詩句于上,以見山中之畫人物,猶作文之點題。一幅之題全從人身上起。……以待學者觸類旁通耳。”[1]從點景人物的身份,穿著打扮,以及人物所處的活動之中可以看出整幅畫的主題,起到了很好的點題作用。比如隋朝展子虔《游春圖》中,用山上騎馬的游人,水中乘舟的婦人,這些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就很明朗地表現出了游春的這一主題,再加之與山石樹木的相輔相成,既豐富了畫面,又以人物活動來增添山水畫的趣味性,讓原本有些寂靜的大自然增添了一絲生命力和悠閑的生活氣息。人與自然景物的完美結合,既可以很好地烘托游春這一主題,又可以讓畫面生機勃勃,為作品營造出了一種輕松愉快的舒適體驗,帶著觀者一起暢游在作品之中。
再如唐朝李思訓的《江帆樓閣圖》(此畫今已被認定為宋人手筆),清代安歧曾對此畫中的點景人物有過這樣的評說:“……具唐衣冠者四人,內同游者二人,殿內獨步者一人,乘騎于蹬道者一人,仆從者有前異者,有肩酒肴之具后隨者,行于桃紅叢綠之間,亦可謂游春圖。”[2] 這幅作品中的人物,不論是人物的神態,面貌,衣飾都比展子虔的《游春圖》有了很大的發展空間。較之隋代的點景人物也有了新的變化,畫工更加精細,人物的形象也更加生動,既有在大自然環境下的人物,也有在殿內獨步的人,自然環境中的人物活動也更加豐富,有游人,有挑著酒肴餐具的人,一行人出現在整幅作品中,讓整個畫面都熱鬧了起來,這一行人就很好地襯托了江帆和樓閣這兩大主體,起到了很好的點題作用。如果畫面中單單只有江帆和樓閣,就會造成畫面的空曠和蕭條感,就樣不僅和畫家想要表達的恬淡閑適的主題相背離,也會令畫面失去生機和活力,熱熱鬧鬧的一行人,輕輕松松地出游,畫面生動、有趣、自然、豐富。
宋代的山水畫是山水畫發展的較為成熟的時期,其中的點景人物簡練且生動。李唐的《清溪漁隱圖》整幅作品中雖然只出現了一位村翁垂釣江葦間,但是卻足夠點明主題清溪釣魚,輕輕松松的幾筆便勾勒出一村翁垂釣的動態,用筆極其簡練,人物生動形象地躍然紙上,這幅畫作雖然是李唐晚期的作品,但對于南宋及后來的明代浙派的繪畫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以點景人物的活動營造可居可游的效果
點景人物的活動也是十分廣泛的,比如春游、山間行旅、溪水邊小憩等等,這些活動一方面可以點名作品的主題,另一方面為作品營造出可游可居的藝術效果。人物活動將整個畫面貫穿起來,使畫面整體氣息變得通暢。圍棋講究留住“棋眼”,畫面也要留住“畫眼”。畫面構圖過于擁擠便會造成畫面氣息的堵塞,這也是為什么在山水畫中繪制的小路要讓人能感覺可以走出去的原因。暢通的山間小路也是點景人物可以靈活出現的地方,懸崖峭壁上的茅草屋里三兩個人團團圍坐,令人感覺這間茅草屋能夠在山間站穩腳,人物豐富的活動令觀者身臨其境。想要在作品中來一場視覺暢游,任何一個點景人物都是經過畫家深思熟慮才畫上去的,多一個人、多一筆可能就會破壞畫面整體效果,少一人、少一筆可能又會造成畫面內容的缺少和空缺。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有對畫作營造出的可游可居效果的精確評述:“世之駕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為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為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3]
點景人物的活動所營造出的可游可居的效果在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圖》中有極好的體現。崇山峻嶺間有一隊騎旅從右側山間穿行而出向遠山行進,南方一位騎者身著紅衣乘三花黑馬正準備過橋,嬪妃則著穿著胡裝戴著帷帽,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從山路中穿行,也正是因為在山路上有這一行旅人,觀者們才可以感受到如此崎嶇的山路是可以通行的,縱然山路難行,但這一行人仍然決定從中經過,定是為了如畫的風景和大好的山河。人可以通行的地方也往往是適合居住的,這便可以稱之為可游可居了。
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對于點景人物的活動營造可游可居的效果也有良好的表現。在崎嶇的山路上出現了一支商旅的隊伍,路邊有一灣溪水正在流淌,同時還有山間瀑布,正是因為這山上飛流直下的瀑布,使觀者們仿佛身臨其境,流水聲、人行聲、馬啼聲,也正是這些生動的點景人物為畫面營造出可游可居的藝術效果。商旅的隊伍在山間緩緩前行,為畫面增添了趣味性,原本枯燥的樹石之間有幾個點景人物的出現,給觀者以可活動感,縱使跋山涉水不辭辛苦,商旅們不屈不撓的精神還是值得歌頌的。不僅如此,生動的人物形態與堅硬的樹石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畫面中剛柔相濟,高處的樓閣和近處的山間商旅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也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山間商旅的不辭辛苦的運送商品也是范寬自身的映射,為了達到藝術上更高的造詣來到這深山中細心專研繪畫,足見他本人對于藝術的熱愛。
三、情感傳達的載體與主觀情感的表達
點景人物作為山水畫中的點睛之筆,它也是山水畫作品中畫家情感表達的一個重要載體,畫家將作品中的點景人物比作自己,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去,通過作品中的點景人物來幫助自己實現美好的愿望,以達到點景人物來承載自身情感寄托的作用。點景人物的題材形式多樣,主要以人們的日常生產勞動、生活起居、外出郊游等等作為個人情感依托的主要內容,在生活之中吸收點景人物的素材,通過繪畫的方式將個人的情感從中表現出來。畫家們樂于表現人們當下的個人情感和生活狀態以及社會環境對人們的影響,從多方面、多角度來映射出當下社會環境的基本狀況,以達到畫面整體更加生動豐富且充滿感情色彩的目的。
當然,因為不同時期的社會環境的不同,畫家們寄托的情感也會有所不同。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說:“至如李(成)與關(同)范(寬)之跡,……前不藉師資,后無夏繼踴,借使二李(李思訓、李昭道)三王(王維、王熊、王宰)之輩復起,……亦將何以措手于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4]在宋代的社會環境影響下,宋代出現了層出不窮的優秀山水畫家,他們除了學習前人的優良傳統之外,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創新,他們引領了整個宋代的新浪潮,也正是因為這樣,他們對于點景人物所寄托的情感也有所不同。比如荊浩的《匡廬圖》,這幅圖中是以深山作為依據且加以豐富所創作出來的。這幅作品采用全景式構圖,從不同角度的景色取材然后重新組合到一幅作品里,近岸石坡前有舟想要靠岸,礬畔設有—長堤,長堤上接有一板橋,有一個人騎馬經過,觀賞著山間景色,悠閑情感油然而生。一人一騎山間賞景也正是荊浩所向往的恬淡生活,為了能更好地創作荊浩隱居深山,這樣的舉動也是很多畫家所不能及的。
再如董源的《瀟湘圖》,安歧對該畫有這樣的評價:“《瀟湘圖》卷……山水以花青運墨,不作奇峰峭壁,皆長山復嶺,遠樹茂林,一派平淡幽深,具蒼茫渾厚之氣,其遠近明晦處,更無窮盡。”[5]整幅作品采用平遠法構圖,圖卷下方用淡墨色凸顯出蘆狄,坡岸有蘆叢伸出,左邊有二姝穿著紫紅色衣服,有一位宮女在前方為她們引路,并時不時地回頭和她們相望,這一行人緩緩的向岸邊移動前行。岸邊有五位樂者,正在演奏音樂并且向著江心眺望,江中有一艘小船,船中間坐著一位穿著紅袍的人,紅袍人旁邊有一個人擎蓋,船前方的一個人跪啟,后方的一個人待從,在舟頭有—個人撐篙,在船尾有一個人搖梧,悠然向岸邊駛來,船上的人和岸上的樂師們相呼應。在水邊有捕漁者十人,只等著捕到魚后上岸,整幅作品中的點景人物就有二十處之多,形態各異,這些點景人物承載了董源對于這樣安逸生活的向往,江邊泛舟,身邊有幾個隨從服侍著極其愜意,累了還可以閉目養神靜靜欣賞音樂。不僅僅是董源,很多文人墨客應該都會向往如此怡然自得的生活,遠離紛爭,遠離喧囂的鬧市,全身心地投入到繪畫事業中去,這也終將是古代的一些藝術家們一生所奮斗的目標。綜上,山水畫中點景人物不僅可以為作品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同時借助點景人物也可以為畫面營造出可游可居的藝術效果,讓原本缺乏靈氣的山水增添一些生活樂趣。對中國山水畫的表意達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芥子園畫譜[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2]黃廷海.歷代名家山水畫要析[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3]俞建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
[4]傅敏慧.中國古代繪畫理論解讀[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劉玉喬,渤海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2013級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美術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