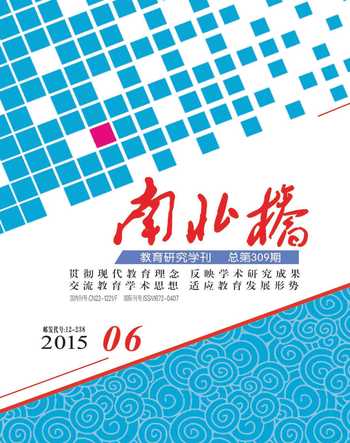明代濟顛故事的口頭傳播
游嘉
【摘 ? ?要】濟公在中國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法名道濟,因一些瘋癲的行為而被稱為濟顛。他的故事盛行于明代,本文將對明朝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探尋濟顛故事的口頭傳播情況。
【關鍵詞】濟顛故事 ?口頭傳播 ?說話
中圖分類號:G4 ?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6.057
濟顛,法名道濟,百姓尊稱為“濟公”,是南宋初年確有的一位僧人。在宋元時代,濟顛故事的傳播主要依靠口頭流傳。由于宋元時代有關資料的缺失,已無從考證濟顛故事具體的流傳情況,但可據現存的資料推斷,濟顛故事已經是藝人們常常表演的內容。在藝人的生花妙口之下,一步步豐富。口頭傳播的方式主要分為兩種:民間街頭巷尾的談論和藝人們的表演。
一、街巷叢談
居簡禪師在譜系上是濟顛的師侄,晚年住持凈慈寺,他的《湖隱方圓叟舍利銘》是最早的最可靠的有關濟顛的記載,文中形容濟顛時說:
狂而疏,介而潔,著語不刊削,要未盡合準繩,往往超詣,有晉宋名緇逸韻。信腳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臺、雁宕、康廬、潛皖,題墨尤雋永。暑寒無完衣,予之,尋付酒家保。寢食無定,勇為老病僧辦藥石。游族姓家,無故強之,不往。
濟顛的性格狂放不羈,有魏晉名士風度。他衣著襤褸,酷愛飲酒。這些都與對普通僧人的規范相去甚遠,因此得了“顛僧”的名號,《舍利銘》下題“濟顛”,便是由此而來。他為孤苦的老僧辦藥石,體現出他悲憫的情懷。濟顛圓寂之后,“都人以湖隱方圓叟舍利晶瑩,而聳觀聽”,眾人這才知道濟顛乃圣僧。濟顛因此名聲大振。于是“邦人分舍利,藏于雙巖之下。”
《西湖游覽志馀》卷二十五《委巷叢談》說:“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茍毀,道聽途說,無復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目睹。”濟顛本身獨特的個性使他具備了成為人們談資的可能。愛談論奇怪之事的杭城人使濟顛故事在眾口相傳中,不斷豐富和神化。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三云:“濟顛乃圣僧,宋時累顯圣于吾杭湖山間,至今相傳之事甚眾。”“相傳之事甚眾”,說明濟顛故事在明嘉靖年間的流傳度,傳說的內容是有關濟顛顯示神通的故事。
二、藝人表演
濟顛故事富于傳奇性,又有一定的民間基礎,自然是藝人表演的極佳素材,于是,濟顛故事進入到了勾欄瓦舍。
(一)濟顛陶真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馀》卷二十《熙朝樂事》記載: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瞿宗吉過汴梁詩云:“歌舞樓臺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華。尚余艮岳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其俗殆與杭無異,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也。
這是明朝唯一一條確切記錄濟顛故事口頭流傳的資料。從這則材料可看出,濟顛故事是經過“陶真”這門技藝傳播的。
明嘉靖辛丑(1541)年進士晁瑮《寶文堂書目》子雜類著錄有《紅倩難濟顛》一本,已佚。很多學者推斷田汝成記錄的唱演濟顛事很可能就是《紅倩難濟顛》。濟顛事沒能保存下來,紅蓮、柳翠事卻在話本小說中得以保存,即保存在《清平山堂話本》中的《五戒禪師私紅蓮》和《喻世明言》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這兩篇敷衍的都是和尚和妓女的故事。根據這相似的名目,周純一推斷:“明代嘉靖辛丑進士晃傈其家藏書目《寶文堂書目》子雜類有登錄一本《紅倩難濟顛》,諸后世學者莫解其真相,大抵似譚正璧以‘知此等話本明時固盛傳解釋之,其性質當與話本相當。”所以,田汝成提到的濟顛很有可能就是紅倩和濟顛之間的故事。
宋朝佛教受“一切現成”思想的影響,越加世俗化。南渡后,杭城物阜年豐,人們日漸沉迷在享樂中。士大夫們狎妓飲酒,詩酒唱和。僧人們結交王侯士人,頻繁出入社交場合。許多名僧的詩作也沾染上了脂粉氣。《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記錄圓悟克勤呈給法演禪師的一首詩偈:
金鴨消香錦繡幃,笙歌叢里醉扶歸。
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從這詩歌的內容來看,完全無法想象他的作者竟是個僧人。所以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將濟顛與煙花巷柳聯系在一起,寫出一段故事,不是不可能的。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想象,在明代卓有姿色的盲女或在街頭村陌,或在深宅內院,一邊彈著琵琶一邊用七言韻語講唱著濟顛和紅倩的故事。
(二)濟顛說話
關于明代的濟顛說話沒有任何直接的資料可考。隆慶三年(1569)刊刻的《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卷首題“仁和沈孟柈敘述”。這“敘述”二字暗示了沈孟柈極有可能是個說書藝人。話本小說的刊刻與這種說話的發達程度是有密切的關聯的。這也說明了在明代是有藝人講濟顛故事的,而且民眾已經滿足不了只在茶坊聽,而要買回來細細品味。
既然名為“說話”,在表演形式上,與陶真的以唱為主有明顯的不同。《清平山堂話本》中所收錄的宋代話本都以散言為主,同時嵌入詩詞作為敘事言情的輔助。宋代的部分舊本在詩詞前標注了曲調,比如《刎頸鴛鴦會》中將“商調醋葫蘆”反復使用了10次,并加入“南鄉子”1次。后來的《京本通俗小說》中收錄的宋代話本《西山一窟鬼》將“念奴嬌”使用了15次,《碾玉觀音》使用“鷓鴣天”3次、“蝶戀花”1次。說話,以說為主,以唱為輔,一般是用一首曲調(曲牌)兼加入其他曲調來演唱的。再后來,說話演變為只說不唱的形式。《醉翁談錄》中敘述小說伎藝說“曰得詞,念得詩,說的話,使得砌”,唱的部分徹底消失了,話本中的詩詞都只用念誦了。隆慶三年(1569)刊印的《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同樣羼入了大量的詩文,與以往話本中詩詞只做輔助之用不同,加入的詩文都與故事情節相關聯。比如趙太守要砍伐凈慈寺門外兩旁的松樹,濟顛呈上律詩兩首令太守改變主意,松樹得幸免刀斧。這些詩文都不標注曲調,亦說明是用念誦的。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敘述了濟顛一生的言行事跡,保留了宋代說話的痕跡,這說明明朝濟顛說話的內容延續了宋代的情節,又有所增改。
明代濟顛故事的口頭流傳為其進入大眾文學領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