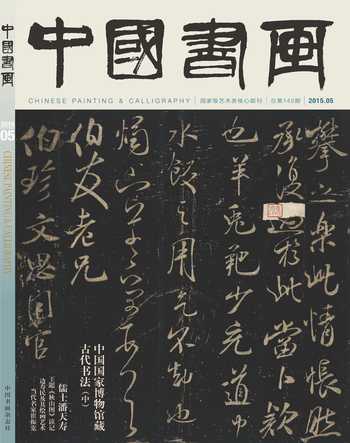象與顯
彭峰
德國美學家澤爾(Martin seel)近來以“美在顯現(xiàn)”的主張贏得了美學界的關注。所謂“顯現(xiàn)”(appearing),即是事物在我們的審美經(jīng)驗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一種活潑樣態(tài)。當我們用無利害的態(tài)度來關注對象時,對象就會處于一種完全開放的活潑樣態(tài)。這種活潑的狀態(tài)體現(xiàn)為一種動態(tài)的過程,澤爾稱之為“Erscheinen”。為了體現(xiàn)它的動態(tài)性,英文譯者用動名詞“appearing”來翻譯它,而不是用現(xiàn)代美學中的常用術語“semblance”(外觀)來翻譯它,也沒有用名詞“appearance”(表象)來翻譯它。我把它翻譯為“顯現(xiàn)”而不是“外觀”或“表象”,目的也是為了突出它的動態(tài)和過程的特征。鑒于“顯現(xiàn)”有時候也會被理解為名詞,用單字“顯”來翻譯它也許更為合適。
我們可以對照兩個概念來說明“顯”的特征:一個是“being-so”,為了突出它的不變性,我把它譯為“確在”:一個是“appearance”,可以譯為“表象”。事物的“確在”,就是一般人樸素地認為事物確實存在的樣子。事物的“確在”,可以用概念來描述,從而形成關于事物的命題知識。事物的“顯現(xiàn)”則不同,它不能用概念來描述,不能形成關于事物的命題知識。事物在未被我們認識的情況下可以說是“確在”,事物透過概念顯現(xiàn)出來就成了“表象”或者知識。“顯現(xiàn)”處于“確在”與“表象”之間,是事物在被概念固定為“表象”或知識之前的活潑狀態(tài),是事物“顯現(xiàn)”為“表象”的途中。正因為“顯現(xiàn)”是在途中,因此它是動態(tài)的過程,而不是最終的結果。“確在”和“表象”都可以被當作結果,但“顯現(xiàn)”總是處于幻化生成之中。“確在”和“表象”,都可以不依賴觀察者而存在,但“顯現(xiàn)”依賴觀察者的在場。一旦觀察者缺席,事物的“顯現(xiàn)”就蛻化為“確在”或者“表象”。總之,澤爾在西方一分為二的本體論區(qū)分中間劃出了一個新的地帶,這個地帶既與對象的存在有關,也與主體的在場相連,這個地帶就是“顯現(xiàn)”。
澤爾的顯現(xiàn)概念,對于習慣于一分為二的本體論區(qū)分的西方哲學來說,算得上新的發(fā)明。但是,在中國哲學中,它就有些似曾相識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論區(qū)分不是“一分為二”而是“一分為三”。中國形而上學將實體劃分為“道”“象”“器”。根據(jù)西方形而上學中的標準區(qū)分,我們可以勉強將“道”歸結為抽象對象或心理對象,將“器”歸結為具體對象或物理對象,但這種標準區(qū)分中沒有“象”的位置。“象”在這里不能像我們通常理解的那樣被理解為形象、形式或者輪廓。“象”不是事物本身,不是我們對事物的知識或者事物在我們的理解中所顯現(xiàn)出來的外觀。“象”是事物的兀自顯現(xiàn)、兀自在場。“象”是“看”與“被看”或者“觀看”與“顯現(xiàn)”之間的共同行為。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我們可以說“象即顯現(xiàn)”。
讓我借用王陽明的一段對話來對象即顯現(xiàn)做些具體的說明。《傳習錄》記載:先生游南鎮(zhèn),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王陽明與他的朋友之間的對話似乎相當奇怪。在我們?nèi)粘I钪校炔粫小芭c汝心同歸于寂”的花,也不會有“顏色一時明白起來”的花。我們的認識功能自動地將概念賦予給所看到的花,給花命名,將它視為比如桃花、梨花、菊花、芙蓉花、杜鵑花等等,這些都是在王陽明和他的朋友們游玩的山上容易見到的花。
讓我進一步假定王陽明和他的朋友們看見的花就是芙蓉花。現(xiàn)在,我們有了三種不同的芙蓉花:“與汝心同歸于寂”的芙蓉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的芙蓉花,以及有了“芙蓉花”名稱的芙蓉花。這里,我用有了“芙蓉花”名稱的芙蓉花來指稱芙蓉花的顯現(xiàn)結果,也就是我們依據(jù)概念或名稱對芙蓉花的再現(xiàn)或認識。我們可以將這三種芙蓉花簡稱為“芙蓉花本身”、“顯現(xiàn)中的芙蓉花”和“再現(xiàn)中的芙蓉花”。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美學,審美對象既不是任何芙蓉花本身,也不是任何再現(xiàn)中的芙蓉花,而是所有顯現(xiàn)中的芙蓉花。
這三種不同的芙蓉花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區(qū)別?簡要地說,芙蓉花本身是一種樹木。比如說,它有三米高、眾多的枝椏、綠色的葉子、粉紅色的花瓣等等。我們可以去數(shù)它的枝椏的數(shù)目,觸摸它的樹干的硬度,嗅它的花的香氣,如果愿意的話還可以嘗嘗它的葉子的滋味。無論我們是否知道它是芙蓉花,我們在芙蓉花本身中都可以發(fā)現(xiàn)眾多的諸如此類的特征。這種芙蓉花可以存在于心外,可以處于“寂”的狀態(tài)。
顯現(xiàn)中的芙蓉花是在我們知覺中的芙蓉花或者正被我們知覺到的芙蓉花,也就是王陽明所說的“顏色一時明白起來”的芙蓉花。王陽明主張“心外無物”,他想說的也許是:我們只能有在心上顯現(xiàn)的芙蓉花,而不能有芙蓉花自身。王陽明的這個看上去相當奇怪的主張實際上并不難理解,因為如果我們不能感知某物就無法知道它是否存在。不過,這里的顯現(xiàn)中的芙蓉花不能被理解為主觀臆想的產(chǎn)物。“心”在這里如同“鏡子”或“舞臺”,借助它芙蓉花顯現(xiàn)自身,這是我們在禪宗文獻中很容易發(fā)現(xiàn)的隱喻。因此,在許多方面,顯現(xiàn)中的芙蓉花都十分類似于芙蓉花本身,它們之間的唯一區(qū)別在于前者是知覺中的對象,后者是物理對象或自然對象。
實際上,王陽明并沒有取消芙蓉花本身,他只是將它轉變成了顯現(xiàn)中的芙蓉花。在我們的日常經(jīng)驗中,我們可以相當確定地擁有芙蓉花本身,因為我們可以去看它、摸它、嗅它、嘗它。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一般人的普通看法跟王陽明的深刻洞見之間有何區(qū)別?在王陽明眼里,一般人心目中的芙蓉花本身并不是真正的芙蓉花本身,而是芙蓉花的再現(xiàn)或幻象。我們通常將某種再現(xiàn)中的芙蓉花當作芙蓉花本身,比如,我們今天就容易將科學對芙蓉花的再現(xiàn)當作芙蓉花本身,因為科學在今天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科學對芙蓉花的再現(xiàn)并不是芙蓉花本身,它只是關于芙蓉花的現(xiàn)代植物學知識。我們還有對于芙蓉花的其他再現(xiàn),還有關于芙蓉花的其他知識,比如,中國傳統(tǒng)中草藥學知識。從不同的觀點出發(fā),我們可以得到不同的芙蓉花知識。享有統(tǒng)治地位的再現(xiàn)或知識,通常就會被誤以為事物本身了。
顯現(xiàn)中的芙蓉花與再現(xiàn)中的芙蓉花之間又有何區(qū)別?關于顯現(xiàn)中的芙蓉花,王陽明只是說它的“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他并沒有說他看見了不同的顏色或者不同的樹。我們假定在某一時刻我們看見的顏色是一樣的,比如說粉紅。王陽明看見的顏色與植物學家或中草藥學家看見的顏色并不是兩種不同的顏色,比如前者看見了粉紅后者看見了橘紅,而是同一種顏色的不同樣態(tài),即在顯現(xiàn)之中的粉紅和不顯現(xiàn)的粉紅,前者是我們對粉紅的感受,后者是我們對粉紅的知識。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不顯現(xiàn)的粉紅”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來沒有進入感知的粉紅,一種是曾經(jīng)進入感知而現(xiàn)在不在感知之中的粉紅。讓我們暫且撇開前一種粉紅。“正在感知之中的粉紅”與“曾經(jīng)進入感知而現(xiàn)在不在感知之中的粉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是活潑潑的“象”,后者已衰變?yōu)樗腊灏宓摹爸R”。在活潑潑的象的狀態(tài),我們的感知處于逗留之中,并不立即提交或上升或抽象為知識。我們得到的是象還是知識的關鍵,不在于觀看的程度是否仔細,而在于觀看的態(tài)度是否松弛。王陽明的觀察不一定有植物學家或中草藥學家那么仔細,但王陽明能夠看見花的象,而植物學家或中草藥學家只能得到花的知識,因為王陽明在“游”南鎮(zhèn),“游”讓王陽明的感知擺脫了概念的束縛。
藝術的靈魂就是“象”或者“顯”,就是處于途中的正在“顯現(xiàn)”的活潑潑的“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