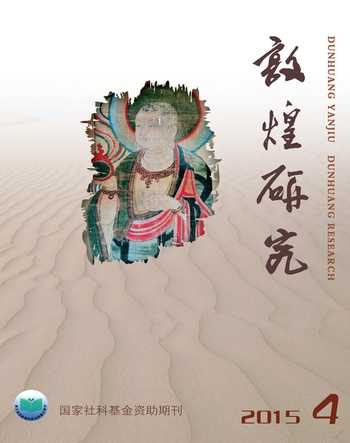《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儀仗樂隊樂器考
朱曉峰



內容摘要:本文以莫高窟第156窟主室南壁及東壁南側下部所繪《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中的儀仗樂隊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儀仗樂隊的功能、樂器屬性等方面的歸類,考證了晚唐時期歸義軍節度使統軍出行儀仗樂隊的編制、樂器以及樂舞配置,重點分析了出行圖中出現的各類樂器的沿革、形制、材料和演奏形式,并結合相關史料,對歸義軍時期的音樂機構進行了合理地推論,以期在上述諸方面得出一定的結論。
關鍵詞:張議潮統軍出行圖;鼓吹前導;伎樂方隊;樂器;歸義軍;音樂機構
中圖分類號:J63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5)04-0025-10
A Study on the Ceremonial Band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Outing Scene of Zhang Yichao”
ZHU Xiaofe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On the south and east walls of the main chamber in Mogao cave 156 is a painting of the“Outing Scene of Zhang Yichao,”the subject of which was the governor of the Gui-yi-jun (Return-to-Allegiance Army) in the later Tang dynasty.This paper present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band formations, and arrangements of musicians and dancers by classify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ceremonial band and various items in the “Outing Scene of Zhang Yichao.” This analysis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forms, materials, and performance types of various musical instruments based on relevant documents.
Keywords: “Outing Scene of Zhang Yichao;”leading trumpeters; square team of musicians and dancers; musical instruments; Gui-yi-jun; music institu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莫高窟第156窟位于莫高窟南區崖面的南段第四層,為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開鑿的洞窟。其主室南壁及東壁南側下部繪有《張議潮統軍出行圖》,榜題全文為:“河西節度使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張議潮統軍□除吐蕃收復河西一道(出)行圖”;北壁及東壁北側下部則繪有《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其榜題為:“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根據敦煌文書記載,張議潮于咸通二年(861)攻占涼州,之后被授予“檢校司空”一職①,所以第156窟的始建應該在861年。另外,賀世哲先生考證第156窟完工應在咸通六年(865),而且“第156窟甬道壁畫又是以張淮深的名義畫的……據此推斷,第156窟前室和甬道繪壁的主持人應該是張淮深”[1]。本文將沿用以上觀點進行論述。
兩幅出行圖作為晚唐時期精美的供養人圖像,為我們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儀仗、兵制、音樂、舞蹈等諸多方面的社會信息,使我們對歸義軍時期的樂舞文化和音樂機構有了更加確切與翔實的認識。2013年10月,筆者赴敦煌莫高窟實地調研第156窟,并結合文獻資料和壁畫圖像,對《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中樂隊的編制、樂器、樂舞以及歸義軍時期的音樂機構進行了相關研究,欠缺之處,敬請指正。
一 ?《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儀仗樂隊的編制
敦煌文書P.3773V記有唐代景云二年(710)所寫《凡節度使新授旌節儀》一文,從中可以看出唐代節度使新授旌節出行儀仗的規定:
1. ? ? ? ?凡節度使新授旌節儀
2. ? ? 天使押節到界,節度使出,先引五方旗,
3. 后鼓、角、六纛,但有旗、幡,不得欠少弓箭,
4. 衙官三十,銀刀官三十,已上六十人,并須衣服
5. 鮮凈錦絡縫褶子。盧帕頭五十,大將
6. 引馬,主兵十將,并須袴帑、襪額、玲瓏、纓
7. 拂、金鞍鐙,鮮凈門槍、豹尾、
8. 彭排、戟架。馬騎、射鹿子人,悉須(袴)帑、襪(額)、
9. 纓拂、玲瓏,珂佩。州府伎樂隊舞,臨
10. 時隨州府現有,排比一切,像出軍迎候。
……[2]
上述儀仗與《張議潮統軍出行圖》所描繪的儀仗基本一致,其中樂隊分前后兩部分,前部分是鼓角前導,后部分為伎樂隊舞,二者均屬于前部儀衛序列。《凡節度使新授旌節儀》并未詳細說明鼓角前導和伎樂隊舞的編制情況,但在《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中可以明確看出樂隊的具體編制。出行儀仗的鼓角前導為鼓吹8人,分左右列隊,每列4人,前兩人敲擊大鼓,后兩人吹奏大角。伎樂隊舞在衙官隊列之后,分為舞伎方隊和伎樂方隊。舞伎8人,分左右列隊,每列4人,呈舞蹈行進狀態;伎樂方隊共12人,其中大鼓1對分列左右最外側位置,1人背鼓,1人敲擊,另8名樂伎分前后列隊,每排4人,手持樂器,呈演奏行進狀態,如圖1。
李正宇先生在研究歸義軍樂營的結構與配置時,根據榆林窟第12窟北宋供養人題記《齋糧記》中“樂營石田奴三十余人”的記載,認為《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中的樂舞“無疑應屬樂營人員,即所謂‘衙前樂部。壁畫所繪,當然只是歸義軍樂營的一部分,不可能把樂營人員全部畫出。故上舉數字不過略示其事,并不足判斷歸義軍樂營的規模”[3]。
《隋書》卷15對宮廷儀仗中角的規定為:
長鳴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駕,三十六具供皇太子,十八具供王公等。次鳴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駕,十二具供皇太子,一十具供王公等。[4]
成書于開元二十六年(738)的《唐六典》卷16對唐代行軍儀仗中鼓角的使用有明確規定:
諸道行軍皆給鼓角,三萬人以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面;二萬人以上,大角八具,大鼓十四面;萬人以上,大角六具,大鼓十面;萬人以下,臨事量給。其鎮軍則給三分之二。[5]
在《張議潮統軍出行圖》的榜題中,張議潮時任官職明確記載為“河西節度使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被唐朝政府授予“檢校司空”一職的時間距《唐六典》頒行已逾百年,而出行圖中前導儀仗的大鼓為4面,大角為4只,可見出行圖中鼓吹前導的編制大體與當時的儀仗制度相符合,對于歸義軍樂營的規模,《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可能正如李正宇先生所言只是“略示其事”而無法判斷。但論及具體的出行儀仗編制,出行圖應該是歸義軍時期的真實反映。據此推測,晚唐時期節度使行軍儀仗中鼓角編制應與出行圖所繪編制相同,即大鼓4面,大角4只,同時也證明張議潮所統治的河西地區盡管遠離唐帝國的中心,但其任節度使期間壁畫圖像所用儀仗并沒有僭越當時的儀軌。
二 ?《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儀仗樂隊的樂器
出行圖儀仗樂隊所演奏的樂器共計19件,包括打擊樂器、吹管樂器和彈撥樂器三類,分別置于鼓吹前導和伎樂方隊之中,以下將對每件樂器按所在方隊加以分析考證。
1. 鼓吹前導
鼓吹前導為8人編制,包括打擊樂器大鼓4面,吹管樂器大角4只,分兩列排列。
(1)鼓,原始社會就已出現,早期的鼓便是以獸皮蒙面振動發聲的。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鼓身開始采用不同材質,如銅鼓、木鼓等。根據圖像分析,出行圖前導鼓吹中的大鼓鼓身為木制,鼓面蒙以獸皮屬儀仗用鼓,外形、敲擊及固定方式均近似今日流行于西北地區的太平鼓。鼓身通體呈棕紅色,無花紋裝飾,鼓面土黃色。鼓置于鼓手身體一側腋下,鼓手持長約60厘米的木制鼓槌,鼓槌前端較粗,鼓手體態呈敲擊狀,如圖2所示。至于此類鼓的具體名稱,莊壯先生和鄭汝中先生將此鼓稱為“軍鼓”[6,7],之所以稱為“軍鼓”,一方面前導鼓吹屬于軍樂,另一方面是為了與出行圖中伎樂方隊的大鼓加以區別。二位先生的提法不無道理,但鑒于《唐六典》將此類鼓稱為“大鼓”,故本文仍沿用《唐六典》之稱謂,以下大角同。
(2)角,在《說文解字句讀》中的解釋是:
羌人所吹角,屠■,以驚馬也。[8]
最早作為樂器的角,應源自西北羌族等游牧民族,以獸角制成,漢代傳入中原。由于其發聲渾厚悠長,可以起到警醒震懾之作用,故被應用于軍樂儀仗前導之中。
《舊唐書》卷29記載:
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長二尺,形如牛角。[9]
唐代段成式著《觱篥格》云:
革角,長五尺,形如竹筒,鹵簿、軍中皆用之,或竹木或皮。[10]
這些記載說明,角在發展過程中,其材質也從最早的獸角演變為金屬、竹木或皮革,而且形制開始逐漸增大。隨著發聲體體積的擴大和材質的變化,角的音色趨于渾厚,音量變大。出行圖中的大角,長約1米左右,體形較大,外觀作棍棒狀,與獸角已有明顯差異,相比之下更接近喇叭。其用途應為朝夕的報時、軍中的號令、鹵簿的威儀[11]。大角的表面裝飾有古樸的幾何紋飾,通體呈土黃色,據此推測,應為竹木或皮革所制。吹手騎于馬上,一手扶持角的中后部,另一手把握吹嘴,鼓腮引頸,作吹奏狀,見圖3。
出行圖明確展現出鼓吹前導系馬上樂,屬于軍樂范疇。早在西漢時期,根據不同的使用場合,就將鼓吹樂分為了鼓吹與橫吹兩大類,宋代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云:
有簫、笳者為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有鼓、角者為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12]
可以肯定出行圖中鼓吹前導即橫吹樂,但從歷史上鼓吹樂和橫吹樂所使用的樂器以及場合來看,鼓吹與橫吹的界定并非十分明顯,尤其是隋唐時代,鼓吹樂與橫吹樂被統稱為鼓吹樂,這在《樂府詩集》卷21橫吹曲辭的解題中可以明顯看出:
自隋己后,始以橫吹用之鹵簿,與鼓吹列為四部,總謂之鼓吹,并以供大駕及皇太子、王公等。[12]
從歷史上鼓吹與橫吹使用的樂器來看,鼓角均為二者兼用的典型儀仗樂器。劉懷榮先生曾考證說:“角本是橫吹曲的主要樂器,但在鼓吹曲辭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角這種樂器……在橫吹曲辭中提到‘笳、‘簫、‘鐃等鼓吹曲主要樂器的詩篇則比比皆是,有些詩篇還顯示出橫吹曲簫、笳、鐃等多種樂器與角合奏的特征……鼓吹、橫吹又都被稱為鼓吹,并都用于鹵簿,這種變化當然并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由于二者之間從根源上均屬于軍樂,在后來的發展中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3]所以,筆者將《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中的鼓角樂隊稱為鼓吹前導,從鼓吹樂具有曲辭以及使用簫、笳、鐃等樂器來看,鼓吹樂在出行儀仗中是具有旋律的,且應該朝著世俗娛樂的方向發展。但出行圖中的鼓吹前導僅有鼓、角兩種樂器,而這兩種樂器均不適宜演奏旋律。據此推測,如果說出行圖是當時出行儀仗的真實刻畫,那么歸義軍時期用于出行儀仗的鼓吹前導就應該以表現軍容威儀和導引出行為主要功能。
2. 伎樂方隊
出行圖中伎樂方隊由12名樂工組成,共11件樂器,樂工分兩個聲部,呈“[”形排列,如圖4。
第一聲部屬低音聲部,由前置的2面大鼓組成,每面大鼓由1人背負,1人敲擊,分別站在左右最外側。鼓身通體土黃色,材質應為木制,蒙皮。鼓手雙手各持1支木制鼓槌,外形細長。相對于鼓吹前導中的馬上大鼓,此鼓體形較大,故音色較前者更加低沉。但鼓吹前導中的大鼓為單槌敲擊,而此鼓為雙槌敲擊,且鼓槌明顯體形較小,證明在行進演奏時,鼓點節奏比鼓吹前導中的大鼓明顯復雜。如果鼓吹前導中的大鼓以簡單的行進式鼓點來突出震懾和引導的作用所說不謬,那么伎樂方隊中的大鼓則以承擔緊隨其后8件樂器的低音和節奏為主要功能,其演奏的鼓點可能更具旋律性。在通常的樂隊配置中,鼓作為低音和節奏樂器,一般置于樂隊后部,但出行圖伎樂方隊中,2面大鼓被反常地安排在樂隊最前部,證明樂隊演奏的樂曲屬于進行曲類,而且旋律應極具節奏感,只有這樣,方能與統軍出行的性質相契合。
第二聲部為旋律聲部,由9件樂器組成,分前后兩排。前排左起,樂器分別為:拍板、橫笛、豎笛、琵琶;后排左起依次為:箜篌、笙、雞婁鼓、鼗鼓、腰鼓。
(1)拍板,從具體的樂器分類來說,屬于體鳴式拍擊樂器,類似今日說唱之快板。敦煌壁畫中,拍板數量之多,居所有樂器之首。從唐代壁畫開始,拍板在樂隊中出現的頻率和地位日漸突出,尤其在五代、宋、元時期的壁畫中,拍板的數量達到頂峰。
宋代陳旸撰《樂書》記載:
拍板,長闊如手掌,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胡部以為樂節,蓋所以代抃也。唐人或用之為樂句……圣朝教坊所用六板,長寸,上銳薄而下圓厚,以檀若桑木為之,豈亦柷敔之變體歟。[14]
拍板在樂隊演奏中“以為樂節”或“用之為樂句”,故其首要的作用應是打擊節奏。另外,陳旸認為拍板在樂隊中地位猶如柷、敔,是西周就已出現的典型木屬樂器,分別用于雅樂的起樂和止樂,所以拍板在樂隊中的另一作用即為指揮整個樂隊。另外,從敦煌壁畫中拍板在樂隊的排列位置來看,一般置于樂隊排頭的最左側或最右側,從中也可以看出拍板在樂隊中所起的首要作用。
出行圖伎樂方隊中的拍板,通體呈絳紅色,木制,長尺余。由于壁畫今已比較模糊,無法判斷板數。根據《樂書》推測,此拍板應為大拍板,為9塊木板。畫面中的樂工雙手持拍板末端,拍板呈展開狀,此為演奏動態的真實再現。拍板置于樂隊排頭最左側,突出了拍板指揮樂隊和打擊節奏的作用。出行圖繪制的時間約為晚唐,而且河西地區在當時尚屬邊陲,拍板已被運用在節度使出行儀仗之中,在當時的流行和樂隊中的地位可見其一斑,這也直接影響到之后拍板的盛行,到五代和宋,拍板在世俗音樂中的應用開始逐漸廣泛。趙為民先生在《宋代拍板》一文中根據《武林舊事》的記載曾提出:“宋代將拍板用于軍樂,在中國歷史上尚屬先例。”[15]然而出行圖中拍板的出現,可以將拍板用于軍樂的時代提前到晚唐甚至更早。
(2)橫笛,是我國古老的傳統橫吹形管樂器,與西周時出現的篪為同類樂器,只是篪為閉管,不同于橫笛的開管。敦煌壁畫中,繪有大量橫笛圖像,最早見于北涼時期,之后各個時期壁畫中均有橫笛,大多為1個吹孔和6個指孔,無膜孔。橫笛在樂隊中主要承擔旋律演奏。凡壁畫中有樂隊,“一般都有橫笛,有時一組樂隊連用數支橫笛,顯然是為了增加音量,突出高音聲部之音響效果”[7]。同時也證明橫笛在當時樂隊中的重要性。伎樂方隊中的橫笛,管身細長,長度約40厘米,材質為竹質。根據樂工的演奏姿態判斷,應由1個吹孔和6個指孔組成。吹孔位于笛頭頂端,距離右側指孔較遠。這種形制是敦煌壁畫中橫笛圖像所共有的特征。樂工以右手前置、左手后置的方式持笛,橫笛位于樂工身體左側。接近吹孔部分的壁畫剝落較為嚴重,故無法確定是否有膜孔或笛膜。橫笛置于整個方隊前排居中處,橫笛在伎樂方隊中應是主奏樂器無疑。
(3)前排左起第3件樂器,為豎吹形管樂器。在距今最早約8000年的上古時代,原始先民就已經開始制作和使用豎吹笛類樂器,如河南舞陽賈湖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就出土過大量的骨笛。根據學界關于《張議潮統軍出行圖》的研究成果來看,其中對該樂器的考證結果是不一致的。莊壯先生稱其為“尺八”[16],高德祥先生將此件樂器記錄為“豎笛”[17],而在湯君與陳明兩位學者的文章中,這件樂器又分別成了“簫”和“篳篥”[18,19]。可見,除壁畫圖像所呈現的演奏方式是豎吹可以確定之外,該樂器究竟屬何種吹管樂器,需進一步進行探究。為指稱方便,本文暫稱其為豎笛。
畫面上的樂工手持樂器作吹奏狀,右手位于管身中部,左手在接近管身末端的位置,證明樂器的指孔應開于管身中部與末端之間。根據樂工按孔的手指判斷,指孔應為6孔。整件樂器管身較為修長,長度、管徑與同方隊中的橫笛相仿,材質應為竹質。樂器所在壁畫的表面脫落情況嚴重,所以是否有膜孔、吹口形制如何以及是否有吹嘴,均無從得知。值得注意的是,鄭汝中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敦煌壁畫樂器分類的時候,不僅繪制出豎笛與篳篥的壁畫圖像,還詳細論述了豎笛與篳篥之間的區別:“豎笛,古代豎吹之竹管氣鳴樂器。古代豎吹之笛名稱甚多,有直笛、豎吹、單管、中管、幢簫、尺八等;”“篳篥,古代哨管樂器,文獻中亦稱觱篥、悲篥,或笳管;”“豎笛較長,有吹口,吹奏時兩手靠下;篳篥較短,稍細,在一端插有哨嘴,按指靠上。”“管體較笛粗壯。”[7]前文提到,壁畫中的樂器指孔開于管身中部靠下,這正好與豎笛的吹奏方式相合;再將該樂器圖像與鄭汝中文中所繪豎笛和篳篥的圖像進行比對,發現其更類似豎笛,所以首先可以確定此件樂器非篳篥。另外,鄭汝中先生認為豎笛即“豎吹之笛”,是豎吹竹管樂器的統稱,而非單類樂器的稱謂。陳旸在《樂書》中也說: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鐘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或謂之豎笛,或謂之中管。[14]685
楊蔭瀏先生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也指出:“從這時候有了豎吹的笛起,笛這一名稱,就成為豎吹和橫吹的兩種笛的概括名稱。……在此以后,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兩者在名稱上,就互相混淆了。”[20]綜合上述,歷史上豎吹的笛類,包括尺八、簫、中管等眾多樂器,所以在無法準確得知壁畫上樂器細部特征的前提下,也只能將其概稱豎笛,而不能確定其為尺八或是簫。
(4)位于前排最右側的樂器是琵琶,按其形制,應稱四弦直頸琵琶。漢代劉熙在其《釋名》中說:“批把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像其鼓時,因以為名也。”
可見漢代的琵琶應寫作“批把”,只是后來在字形上與琴瑟連類,才逐漸轉寫為“琵琶”,而“琵琶”二字本來的含義應是演奏琵琶的手法。琵琶一詞,我國古代與現今的內涵也是不同的。現在的琵琶單指一類彈弦樂器;“古代琵琶這一名稱,在從秦、漢直至隋、唐一段期間,曾適用于很多彈弦樂器——長柄的、短柄的,圓形的、梨形的,木面的、皮面的?譹?訛,弦數多一些的、弦數少一些的,都叫做琵琶。”[20]129
伎樂方隊中的琵琶為直頸,四弦,壁畫沒有繪制琴軸,但可以確定同為四根,無品、無相。音箱為梨形,面板自上而下為深褐色、石綠色和深褐色三色塊,材質應為木質。琴頸、背板、覆手和棙?譺?訛同為棕紅色。背板呈流線型外凸起。覆手外形與今日覆手的外形已相當接近。棙上寬下窄,形似傳統工藝品如意。琵琶由樂工手持橫臥于胸前,樂工左手于琴頸處按弦,右手持棙作彈撥狀。
敦煌壁畫樂隊所繪制的樂器中,琵琶數量居于首位,據統計約有700余件,凡壁畫中有樂隊,基本都能見琵琶。尤其到了唐代,琵琶的制作和演奏技藝達到一個高峰,它不僅在燕樂樂隊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還成為當時流行的獨奏樂器。從出行圖中的樂器排列來看,琵琶在伎樂樂隊中同樣是作為主奏樂器的,演奏方式是手持行進演奏,而不是傳統的坐臥式演奏,這也為琵琶在晚唐五代時期出行儀仗樂隊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例證。
(5)箜篌,位于后排最左側,具體而言,應稱豎箜篌。
《隋書》卷15云:
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華夏之舊器。[4]378
隋《九部樂》和唐《十部樂》中明確記載只有西涼樂、高麗樂、龜茲樂和疏勒樂使用豎箜篌,表明豎箜篌的確是西域傳入中原的外來樂器,隋唐時期以演奏西域諸樂為主。敦煌壁畫中的箜篌也以豎箜篌為主,大部分是樂工坐臥式演奏。樂隊中一般置于靠后的位置,豎箜篌在樂隊中多承擔旋律伴奏。
出行圖所繪箜篌正是上述的豎箜篌,只有深褐色的琴梁清晰可辨,其余如共鳴箱、橫肘以及琴弦均因繪制時畫工的省略或壁畫長時間漫漶而無法得知。依照樂器輪廓,其高度約在80厘米左右,豎箜篌由樂工手持演奏,故應屬豎箜篌中的小箜篌一類。豎箜篌在出行圖伎樂方隊中的出現,至少有三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至晚唐五代時期,豎箜篌使用范圍更加廣泛;第二,在樂隊中主要以旋律輔助和增加色彩性為主;第三,豎箜篌多用于西涼、龜茲等樂部中,加之歸義軍政權地處西陲,可以推測伎樂方隊所演奏的是具有西域風格的音樂。
(6)笙,在西周時期的“八音”分類中,歸入“匏之屬”?譻?訛。
春秋戰國時期,笙是一件重要的禮儀樂器。在宮廷舉行的大射儀、燕禮等儀節中,有聲樂,也有器樂。聲樂稱為“歌”;器樂稱為“奏”或“笙奏”;聲樂進行的時候,以瑟為唯一的伴奏樂器;器樂進行的時候,以笙為主要的樂器,鐘、磬以及另一些管樂器——合稱為“蕩”,都跟隨著笙進行演奏。用于器樂的鐘、磬稱為“笙鐘”、“笙磬”。在名稱上,以笙代表了器樂的全部[21]。
隋唐時期,笙被運用于《九部樂》和《十部樂》中,還出現大、小笙之分,但在樂隊中的地位已遠不如前。敦煌壁畫中繪有大量笙的圖像,時間跨度從北魏直至唐以后。笙本身結構復雜,發音主要依靠插于笙斗上的數根笙管。壁畫上的笙多為簡易繪畫,其形制細節不易分辨,只能通過外部輪廓和演奏姿勢進行考證。出行圖伎樂方隊中的笙同樣如此,加之壁畫顏料變色,只能依稀分辨笙的大致輪廓,至于笙斗、吹管的形制以及笙管的數量均無法判斷。畫面上的樂工雙手捧持樂器,作鼓腮吹奏狀。樂器通體似為原木色。出行圖中共有3件吹管樂器,只有笙屬于和聲樂器,其演奏時產生的“和音”效果對旋律產生輔助和烘托的作用,從而達到所謂“匏以宣之”的音響效果。
(7)后排左起第三為雞婁鼓與鼗鼓,由一名樂工同時演奏。鼗鼓在周代就被運用于典禮雅樂之中,《周禮·春官·小師》注云:
鼗,如鼔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22]
對雞婁鼓的記載,見于《通典·樂典》:
雞樓(婁)鼓,正圓,而首位可擊之處,平可數寸。[23]
直到宋代,《樂書》才明確指出二鼓并用、一人演奏的方式:
鞉(鼗)牢,龜茲部樂也,形如路鼗,而一柄疊三(二)枚焉。古人嘗謂左手播鞉牢,右手擊雞婁鼓是也……左手持鼗,右手擊之,以為節焉。[14]558,561
林謙三先生在考證二鼓時提出:“六朝后半期以至于唐,由中亞的龜茲、疏勒、高昌傳來的西域樂,全都用雞婁鼓,根據中亞、敦煌發現的許多唐以來的繪畫和中國、日本的古籍來考察,西域樂里雞婁鼓和鼗(鼓)常成一組,無可置疑地是由一個人來兼奏的。《隋書》、《新唐書》于上述的西域諸樂中樂器但舉雞婁鼓之名,而不及鼗,只是習慣于把鼗視為雞婁鼓的附屬品而不做特記。”[11]136雞婁鼓被運用于龜茲、疏勒和高昌樂應無疑,因為在隋《九部樂》和唐《十部樂》中,均可以找到以上三部樂使用雞婁鼓的記載,但隋、唐時期真正是如林謙三先生所言鼗鼓為雞婁鼓的附屬而不做記錄嗎?事實可能并非如此,因為《隋書》中就有“設簴設業,鼗鼓填填”的敘述[4]322,而且我們在唐《十部樂》中也找到“鞉鼓”?譹?訛被運用于“燕樂”?譺?訛的明確記載[20]256,所以隋唐時期的鼗鼓在演奏中是可以單獨出現的,鼗鼓也并非雞婁鼓的附屬。二者如不兼奏,則可能是運用于不同樂部的打擊樂器。另外,《樂書》在描述二鼓并用時的措辭為“古人”,可見二鼓并用的演奏實踐應早于《樂書》成書的北宋年間,出行圖繪制的時間上限應在咸通二年(861),所以鼗鼓、雞婁鼓二鼓并用的演奏方式在唐代就已出現。
出行圖中鼗鼓的形制是“一柄疊二鼓”,二鼓上小下大,均為深褐色,材質應為木質蒙皮;雞婁鼓位于鼗鼓正下方靠里位置,材質與鼗鼓同為木制蒙皮,鼓身呈深褐色且似有花紋裝飾于鼓面周圍,鼓面顏色為土黃色,二者在伎樂方隊中應是相互配合使用的節奏性打擊樂器。畫面中的樂工左臂內收,左手手指自然彎曲于雞婁鼓鼓面上作敲擊狀;右臂與右手所在位置的壁畫脫落較嚴重,但可以判斷樂工是以右手持鼗鼓且雞婁鼓夾于右臂腕上。而《樂書》中二鼓的演奏方式卻是“左手持鼗牢,腋夾雞婁鼓,右手擊之”,林謙三先生依據《樂書》的記載以及日本西本愿寺中亞探險隊在吐峪溝發現的絹本佛畫殘片圖像,指出:“這種鼓(鼗鼓與雞婁鼓)的兼奏古法是左手握鼗之柄,左脅夾雞婁鼓,系以綬帶,右手執桴?譻?訛打奏。”[11]139可見出行圖中二鼓的演奏方式與《樂書》、林謙三先生的觀點恰好相異,但值得注意的是《樂書》并未將“左手持鼗牢,右手擊之”的方式敘述成演奏定式。另外,我們在中、晚唐時期大量的敦煌壁畫中發現演奏鼗鼓與雞婁鼓的圖像,如盛唐第445窟南壁西側《阿彌陀經變》、盛唐172窟南壁下側《觀無量壽經變》、晚唐第12窟南壁中央《觀無量壽經變》等。這些經變畫中演奏鼗鼓與雞婁鼓的樂伎既有站姿又有臥姿;有的左手持鼗鼓、左臂腕上夾雞婁鼓,有的右手持鼗鼓、右臂腕上夾雞婁鼓;敲擊雞婁鼓也是持桴或空手形式各異?譼?訛,可見包括出行圖在內所有敦煌壁畫中雞婁鼓均被夾于臂腕之上,而非夾于腋下。看來林謙三先生在考證時并未注意到壁畫中的這些情況,所以其所謂“古法”之“左手握鼗之柄,左脅夾雞婁鼓,系以綬帶,右手執桴打奏”的推論有失妥當。
眾所周知,在鼓類樂器的演奏實際中,演奏效果其實與使用哪只手執鼓,哪只手敲擊以及如何持鼓并無必然關聯,而更可能與個人、群體或是某一時期的演奏習慣有直接關系,所以,對于演奏方式,我們只能認為是“一手持鼗鼓、另一手持桴或空手敲擊雞婁鼓”;而持鼓也有分別夾于腋下或臂腕上兩種方式,至于具體是在使用哪只手或如何持鼓均無法斷言。另外,出行圖壁畫漫漶,導致眾多學者在考證伎樂方隊時,認為此處的樂器只有鼗鼓,忽略了雞婁鼓的存在[2,17,18],在此一并指出。
(8)腰鼓,位于伎樂方隊后排最右側,是樂隊中典型的打擊樂器。腰鼓在敦煌壁畫中是應用比較廣泛的一件節奏性樂器,尤其在隋唐時期的壁畫樂隊中的出現極為頻繁,而且各種形制也開始出現,可以說隋唐時期的腰鼓不論使用程度、體型還是材質、精美程度均大大超越前代。
陳旸在《樂書》中提到:“腰鼓之制,非特用土也,亦有用木為之者矣。土鼓土音也,木鼓木音也,其制雖同,其音則異。”“皆廣首纖腹。”[14]561,592
根據敦煌壁畫中的腰鼓圖像以及《樂書》的記載來看,腰鼓分土制大腰鼓和木制小腰鼓兩類,但鼓面應該都是皮革所制,而且兩類腰鼓同為鼓面大、腰身小的形制。如再進行細化,兩類不同材質的腰鼓又有鼓面等大和鼓面不等大之分,鼓面等大,證明兩鼓面音高相當,其聲音變化主要依靠雙手打擊不同的節奏來實現;鼓面不等大,則意味著除可以表現不同節奏外,還可以產生不同音高的音響效果,所以鼓面不等大的腰鼓,其表現力要豐富于鼓面等大的腰鼓。敦煌壁畫中的大多數腰鼓為鼓面等大形制,而2012年考古發現的上海青龍鎮唐代長沙窯褐釉瓷腰鼓修復件(圖5)和出行圖伎樂方隊中的腰鼓均屬鼓面不等大的形制。
出行圖伎樂方隊中的腰鼓為小腰鼓,其腰身細長,右側鼓面較大,左側鼓面較小,兩側鼓面與鼓腔均構成镲狀外形,但鼓面材質難以分辨。鼓身通體深褐色,材質為木質,不同于圖5所示的瓷質。腰鼓固定在樂工的腰腹位置,樂工兩臂均上揚,做敲擊鼓面的動作。“由于腰鼓具有敲擊節奏、渲染氣氛、增強力度的功能,因而位置排列上也較為醒目。”[6]伎樂方隊中的腰鼓位于后排最外側,故在樂隊中以演奏低音節奏為主,而且由于鼓面不等大,它的加入使整個伎樂方隊的音色更加豐富,表現力更為突出。
三 ?余 ?論
如前所述,筆者將整個儀仗樂隊分為鼓吹前導和伎樂方隊兩部分,對伎樂方隊分別以低音聲部和旋律聲部進行分類考證,如表1所示。按照樂隊的編制來看,所用打擊樂器數量較多,吹管和彈撥樂器所用數量相當且比打擊樂器較少。出行圖所要表現的首先是儀仗行進主題,所以在樂隊中大量使用以節奏為首要功能的樂器是毋庸置疑的,只有這樣,才能將整個出行方陣的威儀和氣勢以音樂的方式渲染和烘托出來。其次,根據唐代《十部樂》和“坐、立部伎”所用樂器分析,打擊樂器種類的數量與吹管、彈撥樂器種類的總數相當,說明唐代音樂對打擊類樂器的重視,從而也使有唐一代的音樂風格以雄健恢宏為特點,而出行圖儀仗樂隊也正是延續了這種風格。另外,根據出行圖中的鼓吹前導、伎樂方隊以及舞伎方隊的編制分析,圖像所反映的歸義軍時期儀仗制度是符合史實的。同一窟內的《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繪制于公元938年左右的第100窟四壁下部《曹議金統軍出行圖》和《回鶻公主出行圖》中也有鼓吹前導、伎樂方隊以及舞伎方隊,而且編制、使用樂器與《張議潮統軍出行圖》所繪基本一致[24],證明歸義軍時期對樂隊和舞隊的配置是規范化、有組織的,當時應該有類似“鼓吹署”和“立部伎”的音樂機構來承擔儀仗出行中的樂舞表演任務,只有這樣,才符合出行圖所反映的歷史事實。
參考文獻:
[1]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M]//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09.
[2]暨遠志.張議潮出行圖研究——兼論唐代節度使旌節制度[J].敦煌研究,1991(3).
[3]李正宇.歸義軍樂營的結構與配置[J].敦煌研究,2000(3).
[4]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383.
[5]李林甫,等,著.陳仲夫,點校.唐六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2:463-464.
[6]莊壯.敦煌壁畫上的打擊樂器[J].交響,2002(4).
[7]鄭汝中.敦煌壁畫樂器分類考略[J].敦煌研究,1988(4).
[8]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94.
[9]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79.
[10]段成式.觱篥格[G]//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643.
[11]林謙三,著.東亞樂器考[M].錢稻孫,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383.
[12]郭茂倩.樂府詩集:卷21[M].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1995.
[13]劉懷榮.漢魏以來北方鼓吹樂橫吹樂及其南傳考論[J].黃鐘,2009(1).
[14]陳旸.樂書[M]//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91.
[15]趙為民.宋代拍板[J].中國音樂,1992(3).
[16]莊壯.敦煌壁畫樂器組合藝術[J].交響,2008(1).
[17]高德祥.西域音樂與古代軍樂的發展[C]//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藝術編.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第299.
[18]湯君.敦煌燕樂歌舞考略[J].文藝研究,2002(3).
[19]陳明.張議潮出行圖中的樂舞[J].敦煌研究,2003(5).
[20]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冊[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3:127.
[21]楊蔭瀏.《笙竽考》一文的補充[J].樂器科技簡訊,1975(1).
[22]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797.
[23]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3677.
[24]寧強.曹議金夫婦出行禮佛圖[C]//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藝術編.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304.牛龍菲.敦煌壁畫樂史資料總錄與研究[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