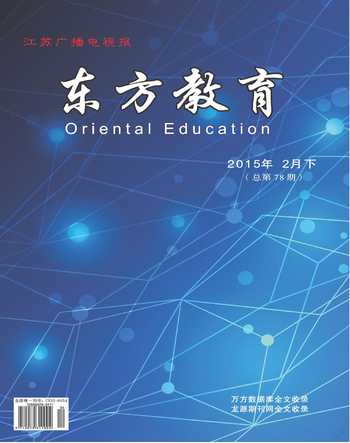精神分析批評視域中《蝴蝶君》中宋麗玲的性別身份之謎
張靜菲
【摘要】《蝴蝶君》是美籍華裔劇作家黃哲倫的代表作。劇中的“女”主人公、京劇旦角宋麗玲的性別問題一直是讀者爭議的熱點。從1960年伽里瑪對宋麗玲的一見傾心,到1986年巴黎審判時宋麗玲堅持褪去女裝以最直白、粗暴的方式呈現自己的男兒身,在兩人二十余年共同生活中伽里瑪究果真沒有識破宋麗玲的男性身份,還是他故意回避了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為解開這一謎底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一層層揭開了隱藏在伽利馬心中的宋麗玲真實性別身份的秘密。
【關鍵詞】《蝴蝶君》;人格理論;同性戀傾向;伽里瑪;宋麗玲
一、引言
《蝴蝶君》的創作最初來源于一個真實事件:法國外交官伯納德·布希科(Bernard Boursicot)和中國京劇男旦時佩璞墜入了愛河,這個持續了二十年的浪漫愛情故事最終卻是個間諜案件。布希科一直以為時佩璞是個女人,他們還有愛的結晶:一個男孩。①華裔劇作家黃哲倫讀到這個故事后,敏銳地覺察到這個真實故事中豐富的文化、政治和性別隱喻,“那個法國大使所愛上的不是某個人,而是一種東方女性的模式”[1]。他把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作為線索穿插其中,創作出了這部充滿性別神秘色彩和具有顛覆性的作品。
《蝴蝶君》中的主人公宋麗玲和伽里瑪的奇特愛情就是弗洛伊德人格結構說的痛苦演繹,他們的本我同性沖動與現實的規約構成了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不得不接受現實的規范過著不真實的生活,但最終他們的自我無法尋找到一個真正的平衡,不得不以一種決絕的方式結束了抉擇的痛苦,去直面殘酷的現實。在二十多年的相處中,他們都在本我與超我的沖突中,無意識地規避了自己的同性戀傾向。每當這個公開的秘密即將浮出水面的時候,超我意識的規約總能及時將它壓制下去,直到最后,當所有歷史的積累使主人公的心理不堪負重時,它被以一種最直白的方式宣告出來。
二、伽里瑪的同性戀傾向
作為伽里瑪最喜愛的一部歌劇,《蝴蝶夫人》展示了他心中最完美的男人形象——征服一個愿意為之付出一切的恭順、柔弱的東方女性。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本人卻最終取代了巧巧桑那個為情自殺的角色。這一舉動看似是殘酷事實打擊的結果,實則是他內心深處的秘密被揭露,慌亂中為維護自己尊嚴而做出的最后掙扎。
事實上,在第一幕第五場的時候,伽里瑪的性取向問題就暴露了出來。在獄中,他回憶起自己12 歲時第一次在叔叔的櫥柜里發現一疊艷女雜志。“我的身體哆嗦了起來。不是因為性欲——不,是因為權力。放在這里的這些女人,足有一架之多——我想讓她們干什么,她們就會干什么。”[2]。性幻想是大腦皮層活動的產物,是對現實生活中暫時不能實現的希望的精神滿足。每個心智健全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然而伽里瑪的幻想并非出于滿足自己的性欲望,而是權利欲望——那種被女性追捧從而在男權社會更好立足的虛榮心。他的心里早已貯藏了一個不能言說的秘密。或許,他從未質疑過自己的異性戀人身份,但他的身體卻給出了另一個答案。
在當時社會父權異性戀體制的威懾下,伽里瑪不得不將自己同性激情這種不能為主流意識所接納的沖動壓制到自己的潛意識中,將自己偽裝起來。這便注定他面臨著身份認同問題,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之間進行集體身份選擇”[3],并最終迫使自己以絕對的男性身份示人。選擇與海爾佳結婚,便由此向西方世界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成功男人邁進了一步。
海爾佳:我的爸爸是澳大利亞的大使。我在罪犯和袋鼠間長大。
伽里瑪:聽到這句話,我跟她走上了婚姻的祭壇。
(海爾佳退場)
伽里瑪:——在那里,我發誓要斷然拒絕愛……我將滿足于在事業的階梯上
快速躍升。我趕跑了激情,在它的所在之處——待著的是實用性。
他們的婚姻與愛情無關,只是一場權力的游戲。很顯然,伽里瑪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欲望之間并沒有父權異性戀所規定的二元對立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在伽里瑪身上,對權力的追求卻勝過了對男女性愛的原始沖動。他渴望獲得異性戀男子才能合法擁有的權力。弗洛伊德認為,制造壓抑和保持壓抑的力量在精神分析過程中表現為抗拒。[4]伽里瑪對任何有可能暴露他同性戀傾向的詞語都非常敏感。當宋麗玲在信中稱呼其為“friend(朋友)”時,他十分不悅,“當一個女人稱呼一個男人是她的‘朋友的時候,她是把他當成一個太監或者同性戀來呼喚的。”伽里瑪的這種閹割焦慮(castration anxiety)是有據可循的。“焦慮是沖突的結果:即來自潛意識本我的愿望與超我的懲罰威脅相沖突的結果”[5]。伽里瑪忌諱聽到閹割、同性戀之類的詞語,正是因為他本我的愿望——同性激情,與超我的懲罰——父權異性戀體制的唾棄之間出現嚴重的沖突,以致他在潛意識中與該類詞語之間劃清了界線。
即便與海爾佳的婚姻宣布了他的異性戀認同,并幫助其實現了權利的追尋,但沒有孩子的事實讓伽里瑪再次有了危機感,閹割焦慮也再次困擾著他。他曾對宋麗玲明確表示,“如果我不能有個孩子,我會覺得上帝自己也在嘲笑我。”因此當宋麗玲謊稱自己懷孕,并最終將一個混血男孩帶到他面前時,他的虛榮、驕傲及對權力的追求令他在無意識中忽略了真相。宋麗玲完美的“蝴蝶夫人”形象,只是伽里瑪躲避主流性別文化規約,實現自己內心隱蔽的同性戀欲望沖動的一種“合法”掩護手段。
三、伽里瑪眼中宋麗玲的男兒身
事實上,劇本中很多地方都或直白或含蓄地點明了伽里瑪早就發現宋麗玲的男性身份的事實。伽里瑪和瑞尼偷情后,曾強烈要求宋麗玲當面脫光衣服,但最終又放棄了。表面上看,他的放棄似乎是出于愛憐,實際上這卻是他的男性占有欲和內心深處隱秘的真相之間的斗爭。他很快意識到維護這個秘密是他在本我欲望與超我懲罰的沖突中所找到的唯一能夠接受的平衡點:
伽:我沒有脫掉她的衣服,難道是因為在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我知道我會發現什么嗎?也許。快樂是這么珍貴,以至于我們的頭腦會翻個筋斗保護它。
伽里瑪最終放棄那個要求并非出于愛憐,而是他內心深處的“某種意識”叫停了他的狂躁,以免親手毀掉自己編織的幻想。這種意識便是來自主流異性戀文化的超我規約。承認宋麗玲的男性身份就意味著兩個災難性的選擇:或者在異性戀主流意識的壓力下憤然自責為自己正名;或者接受現實,勇敢反抗,將自己至于批判和唾棄的洪水中。他斷然不會親手撕毀自己煞費心機樹立起來的成功西方男人的形象,也不會舍棄由對宋麗玲去勢而感受到的同性沖動的滿足的甜蜜,由此,他對宋麗玲的男性身份除了視而不見別無選擇。這便是為什么最后一幕中,當宋麗玲堅持褪去衣衫將“秘密”大白于天下時,他卻開始退縮,甚至不停地哀求。
伽:請別這樣。沒必要這樣。我知道你是什么。
宋:你知道?我是什么呢?
伽:一個——一個男人。
宋:你并不真的相信這個。
伽:不,我相信!我心里的某個地方始終知道,我的快樂是暫時的,我的愛情是一場欺騙。但是我的心牽制著這個認識。使等待變得可以忍受。
簡單的幾句話,揭穿了伽里瑪一直以來的偽裝。是對世俗中父權異性戀體制的威嚴的懼怕使伽里瑪啟用了自己的心理防御機制,在無意識中迫使自己去相信宋是他完美的蝴蝶夫人。如果說宋麗玲是一位技藝超群的演員,那么他勇敢地向伽里瑪表露自己同性戀傾向的行為,絕非演技所能解釋的,背后的原因更耐人尋味。縱然他在最初接近這位大使的時候懷有特殊的目的,但當最后他們苦心經營的愛情泡沫被刺破后,他沒有像對方一樣退縮,而是選擇更直接地表露自己入骨的愛意。相比之下,伽里瑪此刻的無措與無辜則對他曾經威風八面的大男子漢形象構成了莫大的諷刺。
四、宋麗玲的性別錯位
相對伽里瑪隱秘的同性激情而言,宋麗玲對自己同性戀傾向的表達則更為直白。然而,男兒身的宋麗玲為何能將一個東方女性的柔情演繹得如此逼真?要知道拙劣的“表演”是不可能騙過周圍人的眼睛,更不可能征服一位出入國際場合的大使。“東方男性易裝者并不是一味模仿女性,而是表達女性,易裝者不以女性為原型而受到局限,而是與所謂原型分離”[6]。因此,結論只能是這種“假裝的”柔情其實才是他真實的一面,性別在他身上發生了可怕的錯位。
劇本表明宋麗玲對女性從未有過好感。他的母親——他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女人,是一個妓女。他不知道自己父親是誰,從出世起就生活在自己的母親與嫖客之間,并從母親那里學會了取悅男人的技巧。由于見慣了風月場所的骯臟交易,他比女人更懂得如何吸引男人。同時,父愛的缺失及母親的疏于照顧使他從小就渴望得到呵護與寵愛。而伽里瑪正是那個能給他提供溫暖懷抱的人。
故事的開始,像伽里瑪一樣,宋麗玲也從未承認自己的同性沖動。當秦同志看到他的女性裝扮,并警告他“中國沒有同性戀”時,他也在為自己辯護。作為一名革命人士,他深知自己的同性戀傾向是不被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認可的。革命的熱情和當時的環境迫使他像伽里瑪一樣將自己的同性激情壓抑到了潛意識中。當發現自己真正愛上這位大使,卻又不得不為了革命一次又一次出賣自己的愛情時,他雖然痛苦,但仍然堅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他為革命傾盡所有,換來的卻是秦同志的羞辱:“你再也不能用你的性變態把中國熏臭了。你要去污染它產生的地方——西方。”這時,支撐他一直掩飾自己真實情感并出賣自己愛人的那個理由便瞬間瓦解了,宋麗玲再也沒有理由偽裝自己,而是開始渴望以真實的自我去直面他和伽里瑪之間的感情。
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單靠自己一味地拒絕裸露身體或避免能暴露性別的撫摸是絕不可能將這個秘密維系二十年之久的。自己的男性身份不過是彼此都不愿主動揭開的一個公開秘密罷了。在因為性取向問題被革命事業拋棄后,宋麗玲厭惡了這種虛偽的生活和躲藏的感情,決心將這個謊言親手拆穿。伽里瑪在看到宋麗玲的裸體后,羞憤地說:“我在只是一個男人的身上浪費了那么多的時間。”宋則悲情地告訴他自己不僅僅只是一個男人,并勇敢地向他表達了愛意:“我是你的蝴蝶。在這件長袍下面,在所有東西的下面,始終是我。”宋麗玲的舉動看似是在結束他與伽里瑪的關系,實則是期望他們的感情有一個嶄新的開始。剝去女性的偽裝后,他更愿意作為一個男人繼續他們之間的愛情。但這份坦誠卻沒有得到他所期望的結果。
五、結語
人不可能離開社會而生活在真空之中,個人本我沖動的滿足必須以遵守社會規約為前提,這就使這對戀人一度經歷了奇特的人生。對于伽里瑪來說,西方白人文化使他不得不以堅強的白人男性形象示人,他只能將自己同性戀的本我沖動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霸權意識又給他增加了更大的痛苦。這種復雜的心理使他不愿承認宋麗玲的真實性別身份。宋麗玲雖然有男性的身體,卻有著一顆熾熱的女兒心,他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的沖突給他帶來了更多的痛苦。兩人都希望沖破主流文化和性別規約的束縛,任憑內心的沖動得到盡情的滿足,可是社會現實的力量畢竟太強大了。因此,當宋麗玲將男性身份公布于眾時,主流社會性別文化變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沒有勇氣面對公眾的非議,他苦苦追求的“幸福愛情”的城堡便頃刻坍塌了。
參考文獻:
[1]Gainor,J.Ellen.The Norton Anthology of Drama[M].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9.
[2]黃哲倫.蝴蝶君[M].張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3]趙一凡.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4]Storr,Anthony.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M].尹莉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
[5]傅文青.臨床見證:埋藏在潛意識中的閹割焦慮[C].中國高等醫學教育學會醫學心理學教育分會第13屆學術會議論文集,2006.
[6]Barthes,Roland.Literature and Reality[M].Paris:Editions du Seuil,1982.
注釋:
①根據中西方媒體時隔多年的報道,布希科只是法國駐華使館的會計和打字員,并非外交官;他同時也是一名同性戀者,除了時佩璞外,另有其他男性情人。二十多年后,他向媒體坦言,時佩璞臨終之際仍深愛著他。也許正如他的辯護律師所言,這其實是個愛情故事,并非間諜案件。事件的真實性或許有待考證,但無關本文主題,故不作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