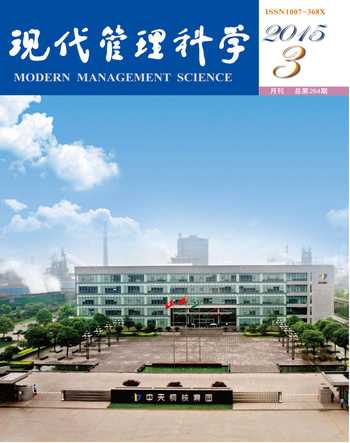母公司治理結構與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關系
宋涇溧 林潤輝 曹萌
摘要:在世界各國積極發展海外事業的國際背景下,文章通過收集中國上市企業集團的FDI相關數據,對母公司治理結構與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實證檢驗了所有權結構、董事會特征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影響,且證實了母公司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者和董事的政治關聯性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正向影響。
關鍵詞:公司治理結構;股權進入模式;所有權結構;政治關聯
一、 引言
為了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于1999年12月16日于在德國柏林成立了20國集團,又稱G20。中國作為20國集團的創始成員,對其跨國企業母公司治理結構與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這一戰略決策之間的關系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二、 母公司治理結構與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
1. 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對進入模式的定義不同,已有研究也早已證實不同的所有權結構(股權結構)會導致不同的控制能力;Killing認為母公司對子公司直接的所有權控制機制比非所有權控制機制效率要高。Anderson和Gatignon(1986)從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掌握的控制權的角度出發,將進入模式進行了定義和劃分。他們把海外進入模式看作是使企業能夠控制其境外業務的治理結構,將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各種形式安排從高到低進行控制的連續統一體。他們根據進入者控制水平對進入模式進行分類:(1)高控制模式——絕對控股、全資子公司;(2)中等控制模式——對等權益、較大權益、等權益(50/50股權)、契約式合資公司、管理合同、限制性排他合同、特許經營、非排他吐限制合同、排他性非限制合同;(3)低控制模式——分散權益、非排他性非限制合同(如集中分銷、某些許可經營)、小股東。而Pan和Tse提出的市場進入模式層次模型,首先將進入模式視為股權與非股權兩種,其次股權進入模式又分為全資經營和合資,而非股權進入模式則分為契約合同和出口。本研究將強調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所有權控制,因而研究海外子公司的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
2. 公司治理結構對股權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廣義上的公司治理結構包括股權結構、債權結構和董事會結構。根據以往對公司治理的研究(La Porta et al.,1999;Mallin,2004),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的公司治理特征在于公司所有權及其控制權,即公司治理結構中的股權結構和董事會結構。
Lien等(2005)的研究表明:在企業中,決策能力的基礎主要來源于高管和董事會成員所持有的股權。Claessens等(2000)則研究認為上市的企業股份廣泛持有,或者被金融機構持有。最近的一些學者研究認為不同類型的機構投資者會對企業戰略(包括國際化)產生不同的影響(Hoskisson et al.,2002;Tihanyi et al.,2003)。特別是Douma等(2006)的研究表明境內金融機構持股與境外金融機構持股相比,對企業績效具有負面影響,而且境內金融機構往往通過復雜的非正式關系網絡與家族企業產生聯系。此外,境外機構投資者則與企業投資組合公司沒有強業務聯系,因而企業更有可能鼓勵高風險、高承諾的FDI決策,即高股權進入模式;而境內金融機構則更可能與規避風險的家族企業、母公司股東和業內人士形成聯盟,進而支持低承諾進入模式,即低股權進入模式。
此外,企業FDI的戰略決策將由董事會成員共同作出,同時監事會負責監督。而且越來越多的戰略性研究已經意識到了公司治理因素在決策過程中的戰略作用,不僅僅包括董事會的規模,還包括在決策過程中對董事會進行監督的監事會規模,以及政治關聯等因素。因而,在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進行選擇的過程中,母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境內金融機構、境外金融機構)、董事會規模、監事會規模和政治關聯等因素對其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
三、 假設提出
1. 所有權結構對股權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從委托代理理論的觀點來看,機構投資者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股東。一些學者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的已經驗證了這一觀點,即機構投資者的出現對公司治理具有促進作用,并且深刻影響著公司的戰略選擇。(Filatotchev et al.,2001;Hoskisson et al.,2002;Lien et al.,2005)。
一些學者將投資者(如Brickley et al.,1988;Kochhar & David,1996;David et al.,1998)進行了區分,即將其分為“壓力反抗型”(Pressure-resistant)和“壓力敏感型”(Pressure-sensitive),并且通過實證,證明了不同的機構投資者類型對戰略決策的不同影響。其中,一種典型的“壓力反抗型”機構投資者就是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者,它們不太可能與其投資組合公司擁有較強的業務聯系,而對企業戰略決策可能擁有更大的影響力(Hoskisson et al.,2002).。另一方面,境內金融機構投資者則是一種典型的“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它們很可能與其所投資的公司擁有業務聯系,并且有責任或義務來支持管理者所提出的議程安排(Tihanyi et al.,2003)。
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1a:在母公司所有權結構中,境內金融機構的股權與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所持有的股權呈負向關系;
H1b:在母公司所有權結構中,境外金融機構的股權與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所持有的股權呈正向關系。
2. 董事會特征對股權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董事會和監事會對企業決策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母公司董事會的監事為內部戰略信息知識的交流提供了重要渠道,這些信息知識將被管理者在決策過程中使用(Hambrick,Geletkanycz & Fredrickson,1993);戰略研究特別強調企業面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市場經濟體的高不確定性環境時董事會的服務與支持功能(Peng,2004)。而董事會的服務與支持功能通常與董事會的規模和多樣性有關,主要集中在董事和監事的總人數。Yermack(1996)研究已表明董事會的總規模影響監督的質量。此外,中國企業中董事的多樣性特征主要體現在政治關聯性(政治關聯是指總經理、副總經理、董事長或副董事長是否曾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官員),即具有政治關聯性董事的企業比不具有政治關聯性董事的企業更傾向于選擇高股權進入模式。由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2a:母公司的董事會規模與海外子公司的股權進入模式選擇呈正向關系;
H2b:母公司的監事人數與海外子公司的股權進入模式選擇呈正向關系;
H2c:若母公司董事具有政治關聯性,則其海外子公司更傾向于選擇高股權進入模式;若母公司董事不具有政治關聯性,則其海外子公司可能更傾向于選擇低股權進入模式。
四、 數據收集與變量測量
1. 數據收集。為了確保數據搜集的可獲得性和準確性,本文選擇屬于G20創始成員中國的上市企業的海外子公司作為基礎研究對象,通過對Bvd數據庫中的《OSIRIS-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庫》2013年4月數據的收集,初步整理出186家在中國(包括港澳臺)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擁有子公司的非金融類集團企業。作為研究對象的母公司企業都是在滬深兩個證交易所上市并按要求定期編制合并報表的母公司,且母公司編制綜合反映企業集團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其變動情況的報表,主要數據來源包括:國泰安數據庫和上市公司年報。
在具體選取數據過程中,為了消除個別樣本的特殊性和信息缺失的樣本,本文選取樣本集合中至少擁有十個屬于中國企業海外子公司的東道國作為研究樣本,因此進一步選定了在17個東道國(US——美國、DE—德國、SG——新加坡、AU——澳大利亞、NL——荷蘭、CA——加拿大、JP——日本、GB——英國、ID——印度尼西亞、IN——印度、IT——意大利、VN——越南、RU——俄羅斯、TH——泰國、FR——法國、PH——菲律賓、MY——馬來西亞)的子公司。最終,除去不符合本研究主題以及數據不完整的海外子公司樣本,最終得到的樣本為在上述17個東道國分別屬于中國企業集團的186家海外子公司樣本,約占總樣本的18.3%。
2. 因變量。中國企業集團FDI背景下,跨國經營時的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測量,主要采用子公司所占股權比例來衡量。由于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所占的股權比例一般是比較穩定的,因此本文選取了最新獲得的2013年4月的海外子公司數據來測量其股權進入模式。本文將股權進入模式作為連續性變量(EM)回歸使用。
3. 自變量。對境內金融機構投資者的股權(DFIN)和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者的股權(FFIN)測量,本文通過母公司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來計算境內金融機構和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者的股權比例;對于董事會規模(DN),本文采用母公司年報中董事的總人數來進行測量;對于監事人數(SN)的測量同樣通過公司年報獲取;政治關聯性(PC)則作為虛擬變量,通過年報中公布的總經理或董事長是否曾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官員,是則為1,否則為0。
4. 控制變量。在母公司層面,本文選取了母國企業集團母公司規模(SIZE)、總資產(TA)作為控制變量。其中,母公司規模通過海外子公司成立前母公司年報中的員工總人數來測量;總資產則是海外子公司成立前的資產總額。
在母國(中國)和東道國層面,本文選取了東道國對外直接投資額(FDII)、東道國與中國的政治制度距離(ID)、經濟制度距離(ED)、文化距離(CD)、東道國GDP增速(GDPS)、腐敗控制(CC)、政治風險(PR)以及國家風險中的腐敗(CCR)作為主要控制變量。其中,東道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體現了東道國的經濟政策與市場開放程度;政治制度距離體現了東道國與母國(中國)在規制制度方面的差異性;經濟制度距離則體現東道國與母國(中國)之間在市場開放性等方面的差異;文化距離體現了東道國與中國的文化差異,在對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子公司時密切影響著企業的決策與經營;東道國GDP增速體現了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現狀,是成立子公司需要考慮的重要東道國環境因素;腐敗控制、政治風險以及國家風險中的腐敗,則共同體現東道國的腐敗程度和風險性。
五、 實證結果與分析
1. 回歸模型與結果。本文的數據分析方法采用多元回歸分析。首先,采用一般線性模型對控制變量進行了回歸,即模型1;然后,對所有權結構(境內金融機構與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者的股權)與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即模型2;最后,對董事會多項特征(董事會規模、監事總數和政治關聯性)與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得出模型3。
本研究中大多數變量的相關系數都遠遠低于標準0.8,所以模型中各主要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但為了更好的診斷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本文計算了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所有解釋變量的VIF值均遠遠小于10,除了個別控制變量以外,其他解釋變量的VIF值在1.221與1.763之間,可見不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于是,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得到的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2. 實證結果分析。表1中模型1對所有的控制變量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顯示東道國對外直接投資額、腐敗控制和經濟制度距離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的影響顯著,其中東道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和腐敗控制與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呈正相關關系,而經濟制度距離與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呈負相關關系。而本文著重研究模型2和模型3,模型2對母公司治理結構中的所有權結構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影響進行了驗證,如表1所示,境內金融機構投資者的股權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的相關關系不顯著,因而假設H1a沒有得到驗證;而在置信水平為95%時,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者的股權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影響顯著為正(Beta=2.435,P<0.05),支持了假設H1b,即母公司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者所持有的股權越高,則其對海外子公司更傾向于選擇高股權的進入模式,反之,選擇低股權進入模式。模型3則對董事會特征與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影響進行了驗證,如表1所示,在置信水平為95%時,母公司董事會的政治關聯性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影響顯著為正(Beta=7.924,P<0.05),支持了假設H2c。而董事會規模和監事總人數與股權進入模式選擇之間的相關關系不顯著,因而H2a和H2b沒有得到驗證。因此,董事會特征中,董事的政治關聯性對企業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具有重要的正向影響,即在成立海外子公司時,相對于不具有政治關聯性的母公司而言,具有政治關聯性董事的母公司更傾向于選擇高股權進入模式。
六、 結論
通過上述研究,本文的主要貢獻與結論在于:
首先,本文較早地將母公司治理結構與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且從所有權結構和董事會特征兩大方面進行了驗證。
其次,本文的控制變量結合了母公司、母國和東道國三大層面,尤其是考慮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政治制度距離、經濟制度距離和文化制度距離,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最后,通過收集G20創始成員中國的上市企業集團相關數據,實證檢驗了所有權結構、董事會特征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影響,且證實了母公司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者和董事的政治關聯性對海外子公司股權進入模式的正向影響,為中國企業集團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適合中國情境的管理決策依據。
參考文獻:
1. 吳中南.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走出去”戰略.管理世界,2004,(2):139-140.
2. 王鈺.從TCL跨國并購視角看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戰略.管理世界,2006,(3):150-151.
3. 周建,于偉,劉小元.跨國企業公司治理研究回顧與展望.外國經濟與管理,2008,30(4):1-8.
4. 蔣瑛,羅明志.戰略因素對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基于中國家電行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國際經濟合作,2011,(1):31-36.
5. 李維安,李寶權.跨國公司在華獨資傾向成因分析:基于股權結構戰略的視角.管理世界,2003,(1):57-62.
6. 王增濤.企業國際化:一個理論與概念框架的文獻綜述.經濟學家,2011,(4):96-104.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號:7113200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號:7097208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項目號:71302097)。
作者簡介:林潤輝(1972—),男,漢族,河北省邢臺市人,南開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網絡組織與治理、跨國治理;宋涇溧(1987—),女,漢族,山西省平遙縣人,南開大學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網絡組織與治理、跨國治理;曹萌(1983—),女,漢族,天津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人口城市化、社會保障。
收稿日期:2015-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