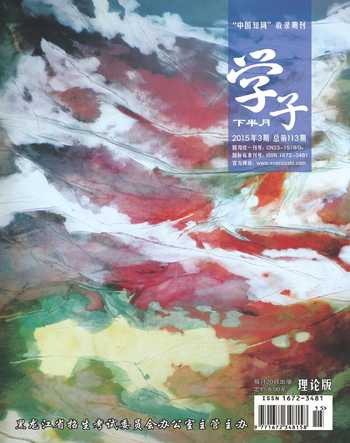閱讀教學存在的問題和策略試探
張於
閱讀教學是語文教學的重要內容,教師對其投入的時間和精力也相對較多,但現實情況往往事與愿違,教師的投入與產出并不成正比,在學生那兒收效甚微。上了不計其數的閱讀課,學生卻仍是一知半解,摸不著頭腦,更有甚者對閱讀課產生了恐懼和抵觸的心理。針對這樣的現狀,筆者試從教師和學生兩個方面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并尋找相應的策略和解決方法。
一、教師學生是源頭
首先,從教師的角度來分析。語文閱讀教學存在一個突出的問題: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閱讀教學呈現出程式化和技術化的傾向,教師過分注重和強化符號意識,重認識題型、解題思路和答題方法的指導,而沒有對文本本身進行深入的解讀分析,缺少了對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識的關照,使閱讀教學逐漸淪為教化和應試的媚寵。語文是語言的藝術,少用多媒體,多關注文本,緊緊抓住語言的韁繩(王尚文語)。正如課標所言:“閱讀教學是學生、教師、教材編者、文本之間的多重對話。”但事實上,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會在不經意間剝奪學生與教材編者和文本之間對話的權利,取而代之的是教師將自己與其他兩者的對話直接轉嫁給學生,從而使學生缺少自身生命的體悟。久而久之,學生思考和感悟的意識就會淡化。
其次,從學生的角度來分析。選入教材的許多文本創作的時間或地域等離學生的生活體驗都相去甚遠,學生很難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知識積累自發地融入閱讀的體驗中去,這種時空上的跨越就成了學生與文本進行交流的障礙,使學生無法獨立地去解讀文本。
那么,如何打破這兩種僵局?如何進行有品質的閱讀教學?筆者認為一切還要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的實際出發,來探究合適的教學策略。
二、以學定教是原則
閱讀教學是要著眼于學生的終身發展的,是關系到學生語文素養高低的重要教學內容,讓學生達到“學會”這一目標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讓學生“會學”,達到“為遷移而教”(奧蘇貝爾語)的目的。因此,教學目標的設置就要根據學生而來,秉承“以學定教”的原則。“以學定教”可以說是一種理念,也可以說是一種思想,“學”既指學習的主體學生,當然也包括語文這一學科特有的學習要求,筆者在這里談的主要是前者。
奧蘇貝爾說:“影響學習的唯一重要因素就是學習者已經知道了什么。要探明這一點,并據此進行教學。”而教師需要了解的就是這種“已有”和“將來”之間的差距,充分考慮學生已有的知識儲備和將來的需求,從而根據這些差距來設置教學目標。
其實,長期以來,就要求教師在備課時要做到“三備”,即“備教材,備教法,備學生”,其中的“備學生”就要求教師根據學生的學情來設置教學目標。雖然絕大多數語文教師都有“備學生”的意識,但事實上,很多教師都是憑借經驗或印象來做出主觀上的判斷,而很少做出實際的調查,多數情況也是將“備學生”這一工作看成是一項準備工作,僅僅停留在課前這一階段,缺少了課中和課后這兩個階段,沒有很好地把握預設和生成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由此可見,教師并沒有把“備學生”這一環節真正落實到位,或者說,行動并未與思想完全保持一致。教師只有真正了解了學生的情況,才會明了自己在教學過程和教學之后的得失狀況。因此,不能僅憑主觀不加調查的做出判斷,也不能停留在淺層,點到為止,一定要深入學生當中去研究,要有依據,用事實來說話,在研究分析的基礎上去尋找學情與文本之間的契合點,設置教學目標。
心理學家坦恩鮑姆曾檢討自己的教學:“我過去一向是歡迎最廣泛的討論的;但是,現在我才知道,我還是要求并期待我的學生了解制定給他的課文和講授材料。更糟的是,我雖然歡迎討論,但是在一切都說完做過之后,我首先還是要求班級得出與我的思路一致的結論。因此,從它們是否具有坦率、自由和居于探索精神性這幾個標準來看,這樣的討論都不能看作是真正的討論;從它是否啟迪思想來看,那些問題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問題。所有的問題都別有用意,因為我對于這些問題的滿意答案,有時甚至對其正確答案都有相當明確的見解。因此,我帶著材料來到班上,實際上把學生當作工具,我掌握情況,一步步引出我認為學生應當學習的材料的中心內容。”在坦恩鮑姆的檢討中,他所提到的自己的這種做法其實早已將問題解決的過程和結果都預設好了。而事實上,教學活動是一個師生雙邊互動的動態過程,閱讀教學是教師、學生、教材編者、文本之間的多重對話,教師應當保證學生的閱讀時間,加強對學生閱讀過程的管理和閱讀行為的觀察,讓學生借助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體悟文本,而不能讓課堂成為教師的“一言堂”,遮蔽學生的多元理解和感知,所以教師也要時刻關注教學過程中學生的活動,根據學生的情況對既定的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做適當的調整。
三、學會移植是關鍵
孫紹振先生曾經說過:“感覺到了的,不一定能夠理解,理解了的,才能更好地感覺。所以,不能單純依靠感受,在生活中也不能絕對地跟著感覺走。感受是需要深化、準確化的,不能不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理解要深化,只能通過分析。分析作為哲學方法,是普遍有效的。”同樣,閱讀教學也少不了分析的環節,只有通過分析,學生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文本。美國作家海明威曾以“冰山”來比喻文學作品,他認為作品的文字和形象只是具體可見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則是要讓讀者自己憑經驗去填充的“八分之七”。所以,對文本的理解,一定要有經驗的參與,才不會顯得單薄。
教材所選的都是一些經過歷史積淀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是屬于作者創作的那個時代,也應該屬于所有的時代,它總是與現在的生活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共通性。因而學生也完全能夠在教師的指導下,憑借自己的經驗和知識去感知理解這些作品。
在閱讀教學中,移植法是一種較為簡單實用的教學方法。移植法要求教師要指導學生暫時擱置作品的獨創性,抽取作品中的一些普遍性的要素,并以此為基礎,調動學生的生活經驗和知識積累,將其引入到文本的閱讀和理解中去,再根據生活的一般邏輯重新進行建構,最后回到作品中與文本進行比較,在比較的過程中加深對文本的理解。因而教師在閱讀教學的過程中要處理好作品的獨創性和普遍性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切實地從學生的實際情況來確定作品的獨創性,將作品的普遍性作為聯系文本和學生之間的橋梁。既要引導學生感悟、體驗“他人的世界”,也要“建構自己的世界”。比如,在分析環境時,可以暫時剝離情感的因素,抽取一些客觀性的描寫;在分析人物形象時,可以抽取人物的年齡、職業、身份等。
《祝福》反映的是封建禮教、封建宗法制度和迷信思想對婦女的殘害,在教學過程中如果我們僅僅是將教師歸納出來的主旨呈現給學生,學生一定很難理解。所以,在教學時我們不妨設計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主問題“是誰殺死了祥林嫂?”,讓學生變成法官,憑借自己的經驗做出判斷,將小說中的人物一一審問。在積極主動的參與過程中,走進文本,使自己和文本交融,從而揭示文本的本來面目和文中所蘊含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同化文本的意義。
閱讀教學應該是學生走近文本,親近作者,喚醒學生情感體驗的過程,所以一定要以學生為中心,切勿讓閱讀教學變成教師讀后感的“聽證會”。
(作者單位:江蘇省昆山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