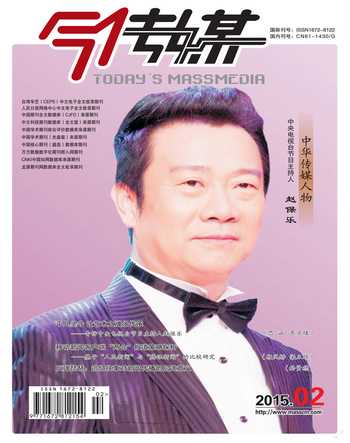國產電影沉思錄——繁榮下的危機
葛勝男 張如成
摘 要:中國電影自進入新千年以來就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電影格局:主旋律電影、商業電影、藝術電影突破了原有的界限,尤其是藝術電影和主旋律電影被商業元素所滲透,創作者期望在個性表達、市場利益、主流價值傳達與觀眾認可多方面達到平衡。本文通過梳理新世紀以后的褪舊變新的中國電影,分析其創作規律、摸索其經驗,暢想其未來,以期對中國電影發展有所裨益。
關鍵詞:電影發展;試聽奇觀;消解歷史;全民狂歡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2-0054-03
一、新世紀以來的電影發展
自從中國加入WTO之后,國產電影不管在票房還是數量上都超過了上個世紀,走進了它的“黃金時代”。面對國內國外帶來的挑戰和機遇,中國的主旋律電影、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步。
(一)主旋律電影的發展
主旋律電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特有的電影類型,它承擔著傳播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重任。自1987年,“主旋律”概念被提出以來,我們國家的電影工作者在這個領域可謂辛苦耕耘,創作了許多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如《開國大典》《孫中山》《馬背上的法庭》《張思德》《孔繁森》,它們涉及到了歷史重大事件、歷史偉人和生活中的平凡英雄。這類型電影往往會被貼上“呆板難看”的標簽,因為其普遍存在的弊病:視聽語言單調化、題材內容相似化、人物塑造平面化等等。觀眾看完總會覺得“創作不近情理、形象不近人理、表現不進心里[1]”很顯然,高高在上的政治說教式電影已經顯現出與時下流行的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格格不入。于是,主旋律電影也開始“改革”,嘗試開拓一條既迎合大眾文化又與市場規律接軌的創作之路。漸漸地,銀幕上出現的主旋律電影中“高大全”的倫理符號被偉人的平凡一面所取代;視覺奇觀支配了傳統敘事而占主體地位;大牌明星成為了主旋律電影一個重要的審美標識。以《辛亥革命》《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為代表的影片掀開了主旋律電影與商業化聯姻的序幕。影片《辛亥革命》對歷史中的偉人進行不一般的細節刻畫:毛澤東會在敵機轟炸下酣睡依舊、黃興和徐宗也有浪漫的戰地愛情、孫中山和唐曼柔之間的心有靈犀……影片除了讓觀眾深刻地了解那段歷史,也讓偉人走下了“神壇”,展現了普通的親民的人性面。《建國大業》有140多位明星加盟,《建黨偉業》更是星光璀璨,170位明星飾演不同角色,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數星星”數得不亦樂乎。上述幾部電影都在嘗試不同的方式突破市場,同時也顛覆了我們對主旋律電影的傳統認知。可以看出,在健康自由的經濟環境下主旋律電影走上商業化道路是必然, 我們如果把主旋律中的意識形態比作“毛”的話,電影票房就是“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二)商業電影的發展
2002年,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初試市場化運作和商業化規律,近兩億美元的全球票房讓這部電影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也拉開了中國“商業大片”的序幕。《英雄》讓國內導演們看到了大片的“甜頭”,馮小剛、何平、陳凱歌、紛至沓來,一系列的古裝大片《夜宴》《天地英雄》《無極》《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被相繼推出。導演們一時間把目光不約而同地集中到古裝、武俠、動作題材上,高度雷同的主題和故事讓中國大片陷入了簡單循環的模式。2007年的《集結號》和《投名狀》打破了大片陳規,將戰爭元素納入大片題材,隨后的《赤壁》《畫皮》《長江七號》《金陵十三釵》《唐山大地震》融入了更多的商業因素,如愛情、喜劇、科幻和災難。至2010年,國產大片的創作和發展呈現一片繁榮景象,檔期密度高、類型多元化、故事內涵也逐漸走向深度化。陣痛往往與新生并存,這類電影逐漸顯示出了共性問題:單薄的情節設計與奇觀的場面產生了相割裂,過度寫意的大場面不僅游離于敘事之外,還起到了阻隔、間離觀眾理解劇情的反效果。一直虎視眈眈的中小成本電影趁此期間迎頭趕上,彌補了觀眾對大片產生審美疲勞的“空窗期”。2011年影片《失戀33天》因其“接地氣”和“治愈系”品格深受年輕觀眾喜愛,開啟了中小成本電影“引領風騷”的新篇章。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中心主任陳旭光分析近年來中小成本戲劇片的成功經驗時說:“結構靈活多變、人物眾多故事相近、視聽語言活潑、敘事節奏快、明星客串多、多與大片唯美化拉開距離[2]”是中小成本電影的特點。2012年底,“草根性”十足的都市喜劇《泰囧》票房直飆11億元人民幣,2013年的趙薇導演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和陳可辛執導的《中國合伙人》以及今年的《分手大師》,都讓主創人員賺的盆滿缽滿。甚至連名導馮小剛和張藝謀都嗅到了這股商業氣息,轉而走平民化路線,投拍電影《私人定制》和《歸來》,影片雖然票房表現良好,但其藝術性眾說紛紜、褒貶不一。無論如何,中小成本電影以其特有的草根性、青年性、狂歡性和娛樂精神在市場激流中站穩了腳跟,這種“以小博大”的現象可以為中國電影的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新世紀以來,我們見證了國產影片從小成本商業片向商業大片發展轉而回歸到中小成本電影的成長軌跡,從追求藝術內涵到重視電影奇觀,從表現古裝俠義到講述草根故事,中國電影人一路演繹著對 “電影是什么”的不懈探索。
(三)藝術電影的發展
在中國電影業界學界,至今沒有哪位專家或學者給予藝術電影一個明確的定義。我們普遍地認為,它是一種區別于商業電影、以表達導演的獨特藝術風格和對世界的思考為目的、藝術風格明顯的電影形式。從意大利詩人喬托·卡努杜發表的“第七藝術宣言”來看,電影本身就是藝術。所以電影不光是一種商業活動,也是一種藝術活動。但是現在21世紀的中國彌漫著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氣息,藝術電影為了避免不被排擠到市場邊緣自娛自樂,強調藝術作為核心的同時適當引入商業元素已經成為當今藝術電影發展的標桿。第五代導演在90年代末20世紀初還因其拍攝的民俗文化電影而斬獲國內外各大電影節的各種獎項,進入新世紀以后也陸續為加入商業電影導演的隊伍。第六代導演因拍攝邊緣性、藝術性電影而著名,無奈的賈樟柯也發出這樣的感嘆:“在一個追求黃金的時代,誰來關心好人”所以我們看到賈樟柯、顧長衛這樣曾經只拍攝純藝術電影的導演們也逐漸在電影中加入商業元素,賈樟柯拍攝的《海上傳奇》中可以看出他對影片觀賞性的重視,顧長衛的《最愛》邀請當紅明星章子怡和郭富城擔當主角,都顯現出導演們為了更大范圍地得到觀眾和市場的認可。徐靜蕾拍攝過三部藝術片《我和爸爸》《夢想照進現實》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如今卻把鮮明的時尚和愛情元素引進電影《杜拉拉升職記》,讓電影變成了一道聲色誘人的“商業大餐”。姜文的《讓子彈飛》更是一部實現了藝術電影的基礎上大量融入商業元素的作品,結果給我們呈現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讓子彈飛》在電影創作的藝術性與商業性的結合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既在藝術上有所創新,又不會離普通觀眾的欣賞水平和觀影習慣太遠,確實為中國藝術電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典范 。“藝術電影不是電影的全部,但藝術電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電影藝術的整體發展水平,從不同側面反映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的社會文化形態。[3]”因此,我們希望中國藝術電影可以長久地存在,不因經濟利益追求而抹煞藝術的本性,讓藝術電影成為維持中國電影多樣性和民族性的一面旗幟,成為反映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面鏡子。
二、電影中顯現的問題
2002年,周星馳的《功夫》作為國產電影以2億元票房首次超過好萊塢大片,2010年,中國電影產量526部,國內票房總收入突破百億元大關,中國電影的發展呈井噴之勢。市場是只“無形的手”,它始終能夠操控著資本的走向,在巨大商業利益的驅動下,中國電影市場顯露出急功近利的創作態度。因此,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數量的井噴沒有帶來質量上的飛躍,數字上的繁榮掩飾不了中國電影背后的重重危機。
(一)試聽奇觀與傳統文化價值相背離
中國大片啟蒙于李安的《臥虎藏龍》,發端于張藝謀的《英雄》,經過《十面埋伏》《赤壁》《夜宴》《赤壁》《滿城盡帶黃金甲》《金陵十三釵》而發展成型。“奇觀景致、異戀故事、明星陣容、裸露鏡頭”成為中國式大片的美學特征。“巴里·迪勒作為公認的高概念電影的鼻祖,他寧愿藝考知名度高的電影明星、商品化的音樂配樂和高級的視覺效果,而很少依靠安排好的情節和人物的電影”[4]。大片的創作者似乎以迎合西方觀眾對古老神奇的東方世界的神秘想象為初衷,卻在國內引起了輿論的口誅筆伐。影片在文化價值觀上產生了偏差和混亂,影片的主題不是表現人性真善美,而是通過欲望和黑暗去講述故事、用暴露和亂倫來烘托藝術,這種極力放大欲望和張揚黑暗面的電影手法顛覆了我們的傳統倫理價值觀。我們不難看出《滿城盡帶黃金甲》來源于曹禺的劇本《雷雨》,卻很難看到導演像原創作者那樣對人性的熱愛和肯定,一場充滿震撼力的悲劇被演繹成了一場血肉橫飛、殺人如麻的慘劇。再看《夜宴》,其故事情節與經典文學巨著《哈姆雷特》的雷同我們姑且不論,但是莎士比亞在作品中的人文關懷在這部電影里卻消失得無影無蹤。暴力和悲劇不一樣,暴力是對人性的忽視對生命的否定,是對人間真善美的絕對背離。有網友評論中國大片的特點:“基本上都是古裝片;基本上都是宮廷戲;基本上場面都很大;基本上都有亂倫的內容;基本上女主角都有好幾個男朋友,而且基本上都喜歡;基本上都不是歷史;基本上都有少兒不宜的鏡頭;基本上演員都是大腕。[5]”好萊塢是商業大片的王國,他們通常用一部大片講述一個不完美的人經過對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最終成為英雄的故事,在這個反抗過程中幫助別人、救贖世界的英雄行為會成為整部電影的高潮和賣點,故事宣揚的依然是普通人在困境下戰勝自己救贖別人而成為英雄的精神。而中國大片卻反其道而行之,幾乎無一例外地對這種積極的精神進行了消解,殺戮、背叛、欲望取代正義、愛與偉大,正是這樣的“反英雄”的情節到成為了最受觀眾歡迎的大眾文藝趣味。
(二)商業元素消解歷史莊嚴感
細心的觀眾會發現主旋律電影在近兩年來也在有意識地進行“重組”,明星偶像、風花雪月、光影變幻這樣的詞匯和主旋律電影產生了聯系。2009年的《建國大業》和2011年的《建黨偉業》將主旋律敘事和浩浩蕩蕩的明星陣容、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相結合,顯示出創作隊伍熟練的市場化運作水平。網上有調查,大部分觀眾到電影院看《建國大業》的動機是去“看星臉”,而“數星星”也成了觀影過程中的一大樂趣。強大的明星陣容成就了影片的票房,但全新的敘事模式和明星的過度出現也消解了歷史事件的深度價值和電影文本的內涵意義。好萊塢的商業電影早已有所證明,《巴頓將軍》、《辛德勒的名單》、《阿甘正傳》沒有奇觀的場面、沒有燦若繁星的明星陣容、沒有不合時宜的風花雪月場面,照樣可以傳遞主流價值觀。其實,任何藝術形式都不是只有通過感官刺激才能達到“寓教于樂”的目的的,電影身負“文以載道”的文化重任,只有集“觀賞性、藝術性、思想性”于一身才是電影的最終歸宿。2011年,張藝謀導演的大片《金陵十三釵》,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教堂里,一群妓女用自己的生命換取女學生的生命的故事。這本該是一部嚴肅的戰爭片,但影片在宣傳的時候拿女主角玉墨的扮演者來大作文章,先是露了一個窈窕的背影,然后露出一個下巴,最后是半張側臉,勢要把觀眾的胃口吊得高高的。美國的《好萊塢報道》指出,“或許只有那些最愚蠢的好萊塢制片人才會想到在一部關于南京大屠殺這樣悲慘事件的電影中植入性感誘惑作為賣點”而這樣的性誘惑卻是《金陵十三衩》中的核心要素,以至于讓這樣一個經常被加以戲劇渲染的歷史時刻被女色所掩蓋,變得造作、沒有說服力。
(三)“娛樂至死”精神充斥電影創作
2006年寧浩的一部《瘋狂的石頭》以300萬的成本獲得了2000萬的票房,這種“以小博大”的勝利激勵了許多電影導演,不久之后,全國掀起了一股轟轟烈烈的喜劇電影熱潮,至今還有余熱。這類小成本電影的拍攝,技術含量低,拍攝周期短,經濟效益高,就連剛剛拍完大片的大導演張藝謀都要來湊湊熱鬧,邀請草根笑星趙本山和小沈陽,拍攝了《三槍拍案驚奇》。類似題材的電影還有《十全九美》《熊貓大俠》《非常完美》《人在囧途》,2012年的徐錚的《泰囧》更是把這股平民喜劇電影推向了票房巔峰。“這一類的喜劇電影以其鮮明的后現代特征,形成了一種以惡搞和顛覆為特色的話語狂歡和影像狂歡,迎合了以青少年為主的消費群體的娛樂需求。”與這種電影類型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一個名詞——“惡搞”。這個新名詞很好地詮釋了這類電影的喜劇策略:把各種網絡流行語、經典電影片段、熱門電視節目搬到劇情中來,通過夸張的表演手段,插科打諢的人物和現代網絡語言營造喜劇效果。這種“戲仿”消失了電影的原創力,也沒有黑色幽默電影對權威意識形態的解構和批判,淪落成為一種內容空洞、精神空虛的“假冒偽劣商品”。正如楊柳所說:“大部分的插科打諢大都只是指向日常生活情感的符號,它們似乎消解掉了自身的抵抗性原則,成為單純游戲性的虛無主義喜劇。[6]” “票房至上”和“娛樂至死”成為投機者創作的唯一標準,藝術追求和文化批評早已被消費主義和商業力量收編,我們呼吁國產電影市場能有真正的中小成本佳作出現。
三、結 語
中國電影至今已逾百年歷史,但發展到今天,我們的電影被那些俠客恩仇、紙醉金迷和虛無的狂歡所覆蓋。一種炫耀性消費已經在悄無聲息中逐漸形成,電影內容的蒼白與貧乏,無中生有的故事,極盡奢華的場面,明星扎堆的陣容,虛幻浮夸的情節,仍舊是今天國產電影的組成要素。近年來各方人士對于中國電影講故事能力的詬病,幾乎不絕于耳。我們曾經有過燦爛輝煌的電影歷史,新中國之前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小城之春》,改革開放以后的《城南舊事》《大紅燈籠高高掛》《霸王別姬》《活著》,新千年以來的《三峽好人》《瘋狂的石頭》《讓子彈飛》……這些誠懇、沉著、不浮躁的影片感動著我們也影響著世界。“什么是電影?”、“什么是中國電影?”這樣的問題逐漸被中國電影人所忽略,感官刺激正在逐漸取代心靈的感動,所有人似乎都滿足于窮奢極欲的感官享受。國產電影需要野心家,更需要以平和的心態投入創作的人。中國電影的未來還有太多的坎坷,太漫長的道路,現在自我鼓舞一番,明朝繼續上路。
參考文獻:
[1]李軍紅.關于主旋律電影冷遇原因及突圍策略的思考[J].山東藝術學院學報,2006(5).
[2]王霞.搭建中國電影的優質塔基——“中小成本電影:創作策略與市場推廣”研討會綜述[J].當代電影,2011(11).
[3]劉文欣.中國藝術電影的歷史與現狀[J].電影評介,2011(15).
[4](美)賈斯廷·懷亞特,RL拉特斯著.劉國選等譯.“高概念:使后現代抽象化”[J].當代電影,1990(6).
[5]饒曙光.中國類型電影:歷史、現狀與未來[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
[6]楊柳.消解與惡搞的狂歡——國產小成本喜劇電影與青年亞文化[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0(2).
[責任編輯: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