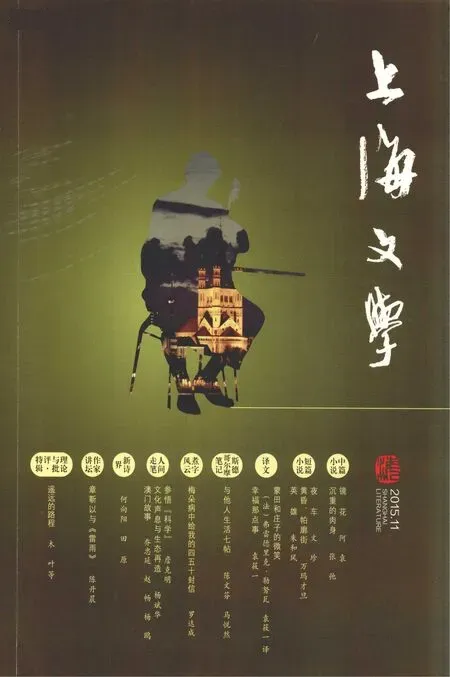幸福那點事
袁筱一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幸福成了不太能夠談論的事情。其實早在某電視臺滿大街地問“你幸福嗎”,從而收獲人們不少鄙夷的目光之前。這里面當然有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作祟:以哲學家為首的現代知識分子過于看重康德所謂的“驗前”知識,而將一切帶有煙火氣味的思考歸于塵土。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也不得不承認,崇尚快速閱讀的現代社會的確充斥著太多雞湯類的作品,讓我們無所適從。這或許是民眾對于知識精英的一種反諷吧。幸福雞湯通常通過“藥方”的形式來呈現,首先會告訴我們什么是幸福,為了幸福我們“應該”做到些什么,有時候,為了更為大家接受,還會穿插勵志的個人故事。多少年來,無論在什么問題上,我們似乎都順理成章地因循這樣一種教育和模仿的模式,我們似乎不會懷疑,就在我們將目光盯在別人的幸福上時,我們已經離幸福越來越遠。
因為這個原因,在拿起這本《一次幸福的哲學旅行》時,我是非常懷疑的。我有太多的理由對這樣一本闡述幸福的“哲學”敬而遠之:因為幸福是很個人的事情;因為幸福沒有客觀的標準;因為幸福甚至不是我們可以用來認識這個世界,認識自己的角度,自然也更無法成為我們建構認知體系的方法論;因為幸福無法預言,也無法衡量。因為幸福,只有在它失去的時候,才會前所未有地凸現它曾經的存在。真的,如果沒有不幸的參照,幸福是什么呢?連托爾斯泰也在《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處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見,對于小說家和詩人來說也是如此,只有不幸是可供講述的,仿佛只有不幸可以映照出死生契闊的動蕩與在死生契闊中,仍然能夠執子之手的人類的偉大。
不過,仔細想來,幸福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被描述的。在進入此次旅行之前,我以為描述幸福的方式無非兩種:一是將幸福縮減或偷換成另外的,更加明確的概念,例如快樂、成功、價值,甚至是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替換成健康、富裕、愛情等等;另一種也許我們更容易接受,那就是寓言——正因為幸福是不能夠準確定義的,所以,它可以通過隱喻構成的空間等待主體個人的“體悟”。
應該是很多人都聽說過青鳥的故事吧。在梅特林克夫妻的筆下,尋找青鳥的過程就像小王子尋找玫瑰的過程一樣漫長和茫然,因為幸福與愛情一樣無法定義,因而這個青鳥的故事也和小王子的故事一樣在四海傳播。寓言的好處在于有細節可以捉摸,同時也有定律可以總結。青鳥的故事能夠推理出的定律就是:需要走遍千山萬水,需要成熟的心智,需要對自己的交待與肯定,我們才能夠最終明白,幸福就在我們的手邊,如果你一生都無法成為它的主宰,就只是把它當成某個一成不變的目標來追尋,它或許始終都在距離你一步之遙的地方,逃離你的追求和索取——你急迫些,它跑得也快些;你懈怠些,它則也會放慢腳步。
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到,這兩種方式不能令所有人釋然。在我們替換了幸福的概念之后,總會有無數人跳出來對我們說,幸福不是成功,不是快樂,甚至不完全是價值——因為價值更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人;當然,幸福更不可能僅僅縮減為健康、金錢和愛情,雖然這一切都有可能給我們帶來幸福。至于寓言或者童話,它是屬于想像域的,在哲學與文學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即便是很重視藝術的康德,暗地里也總要懷疑文學的隨意性。
法國人的價值因而是在這里。自從蒙田發明了“隨筆”(essai,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詞,所以只能因襲原先的翻譯)這種樣式,似乎它就已然作為一種跨界的文字書寫存在。離笛卡爾奠定下來的西方理性基礎不遠,但同時離我們的生活經驗,離塵世的思考也不遠。似乎,用這樣的方式來描述幸福這回事也可以是另一種不壞的經驗和嘗試。
在沒有否定人們對于闡述幸福的種種懷疑的同時,這次關于幸福的哲學旅行用肯定的方式回答了我們心中的很多疑問,并非以心靈雞湯那種“實用手冊”的方式,但也不是一部有關幸福的哲學史。我們可以放下心來,幸福的確與快樂相關:塵世的快樂,無論是從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還是弗洛伊德的角度來看,都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同樣,在老子和莊子的筆下,盡力滿足向往快樂的本性也絲毫不構成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希冀著更加持續的幸福,我們就應該思考一下先哲們早就提出的關于節制的問題。人與動物的差別不就在這里嗎,因為懂得一味地遷就自己的欲望或許會帶來不幸,我們才會試圖建立更加健康的方式。
也是作者告訴我們,關于幸福的意識與幸福密不可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建立自己的幸福哲學,并且用明確的,人人都接受的語匯來定義幸福究竟是什么。幸福的意識意味的是目標、選擇以及為了目標而付出的努力。弄明白這一點,我們或許就不會因為“痛并快樂著”的處境倍感疑惑,也不會再一味地沉迷于他人的幸福模式中。因為這個世界遠遠不是非黑即白,他人選擇的合理性也從來不能夠證明放諸自身的實踐,也同樣合理。
我們懂得了信仰在幸福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信仰同樣是一種選擇,而不是我們人生既定的方向。我很喜歡作者將耶穌罹難的場景與蘇格拉底之死和康德的一生獨居相提并論。作者選擇這樣來解讀耶穌赴難的那一刻:
在他(耶穌)被逮捕的幾個小時前,“他帶上了皮埃爾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他已經開始感受到悲傷和惶恐,于是他對他們說:‘想到要死,我的心里充滿了悲傷,請留下來,和我在一起。走了一小段路后,他臉沖地,祈禱道:‘上帝我父,如果可能,請讓我遠離這份考驗。然而這份考驗并非出自我的意愿,而是你的。”
比較起對于崇高的無原則向往,我們更愿意相信,包括蘇格拉底、耶穌在內,他們也向往包括快感、舒適感在內的幸福,懼怕死亡,然而,信仰作為我們選擇相信的真理,它會令犧牲變為一種幸福。
值得我們思考的還有所謂“尊重自己”的提法:在一個過度宣揚價值感的社會,如何找回自我,“做回自我”,或許也是邁往幸福之路必經的階段。聽從內心的召喚是一件不容易達成的事情,內心的召喚與我們想像的可能相反,它也是理性的產物,是經過教育,獲取文化之后,榮格稱之為“個性化過程”的自我價值判斷。什么才是在有益于自我的同時也有益于社會的,并且在此基礎之上形成自我與社會之間的良性循環?并不是只有心靈雞湯才提供一勞永逸但卻令人難以信服的答案,哲學家、小說家、詩人、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都試圖從自己的角度貢獻于人類。
這次關于幸福的哲學旅行甚至沒有拋棄科學為我們揭示的種種奧秘。如果說,幸福的獲取絕不是可以依靠分子合成來完成的——但是相反,倘若我們感覺不幸,例如罹患了現代社會并不罕見的抑郁,我們卻不能無視現代科學的成果——我們卻有必要知道,幸福感與大腦的多巴胺、乙酰膽堿、伽馬氨丁酸和血清素分泌有很大關系。我們有必要知道,正如我們的生理構造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也可以作用于對于自身幸福感的構建。
《一次幸福的哲學旅行》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勒努瓦是一個哲學家,雖然他并不見得在當今的主流哲學占有什么重要位置。勒努瓦不是不了解法國,甚或是歐洲哲學界對于幸福問題的冷淡態度。就像阿多諾的反問“奧斯維辛之后,我們還能寫詩嗎”一般,在人類遭受了種種毀滅性的災難,似乎離幸福越來越遠的今天,我們還能談論幸福嗎?難道,所有這些毀滅性的災難——戰爭的殺傷力要遠遠高于霍亂、疾病,而科學的進步也并沒有能夠阻擋新的毀滅性病毒的來臨——不正是科學進步,和我們無度追求所謂的幸福造成的嗎?
是在這個意義上,從哲學的那一面來看,作者仿佛更崇尚先哲,東方,或者是西方的,因為我們的先哲還沒有被所謂的“邏各斯”束縛住手腳,他們更趨向于相信,如果哲學不能夠給人帶來美好的生活,它就什么也不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從幸福的角度而言,蒙田與莊子的距離不是那么遠;佛教與斯多葛派的主張也會不約而同;斯賓諾莎也與現代不二論吠檀多的智者安達瑪伊馬有相同的經驗講述。或許,在追求幸福和對幸福有所思考這件事上,東方和西方更多的是和而不同的彼此呼應吧。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在阿多諾之后,哲學的從零,從起點重新開始不見得是件壞事。
又或許,如果不能夠跨越時空的阻隔來欣賞人類共同的美好思考,又如何談論幸福呢?僅僅是這一點,這次幸福的哲學旅行似乎也不那么無聊,因為,就像作者再三強調的那樣,幸福的第一要素的確可以很簡單,那就是——“熱愛當下的生活”,改變自己對于幸福的感知能力。
也為了這個緣故,盡管我從來不相信思想可以救世,可以提供應對不幸的解決辦法,但是我愿意與大家分享作者,以及作者所提及的所有智者對于幸福的思考,并且隱約地相信,幸福是可以談論的,哪怕是像叔本華那樣,用不幸的方式來談論幸福。具有思考的能力,這本身難道不已經是人類無與倫比的幸福了么。我們暫且不急著要一個統一的答案,這就是法國人不受任何限制的essai能夠給我們帶來的好處。讀,或者寫,因而也成了一種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