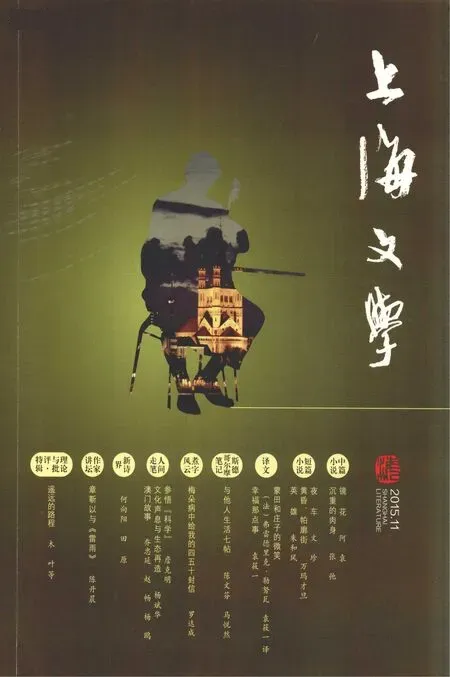參悟“科學”
詹克明
科學若參禪,虔誠悟自然。
——《科學雜詠》
有些事,你越是熟悉,越是難以準確說清;越是窮究,越是覺得它深不可測;越是努力靠近,越是覺得它無限遙遠。當你為此追求了一生,總算有了點實質性理解時,卻又發現,那竟然是個永遠也不可企及的彼岸。
科學本原所限,任憑其今后怎樣發達——科學永遠也不可能抵達絕對真實的彼岸!
在所有人類文明中,最不可思議的就是“科學”。
它渾然一體,和盤托出,你要么全盤接受,要么完全拒絕,不可以選擇性地承認一部分,而排斥另一部分,更不允許擅自增添或是刪減其中的任何微小部分。
它遵循自然,特立獨行,從不歸屬或依附于任何的文化類型,也毫不避諱任何有悖于當地文明的傳統禁忌。
它高屋建瓴,巍峨卓立,從根基上起就已孑然自立,任其自成一統,自我完善,自洽圓通,自行發展。因此它更像是一種單性繁殖的高級生命體。
它源凈流清,偽妄難藏,永遠保持極強的自潔能力,而且這種去偽存真的凈化過程只能依靠科學自身來完成,完全無需任何科學之外的力量非分評說,強行干預。
它大成若缺,深不可測,永遠沒有完成,永遠都有新的未知需要探究,使之不斷擴展壯大,分立出新的科學分支。
沒有現代科學就沒有現代人類!
作為現代文明的獨立支撐,科學又擁有諸多發自本原的內在稟性。
科學借助“粗略”尋求本真
嚴格說來,大自然只有“1”,沒有“2”(當然大自然也沒有“0”,“0”只存在于人的主觀世界之中)。
即使這個“1”,你也不能從它所在的環境中將其完整地剝離出來。
原則上你拿不到一個完全的電子,依據波函數平方計算,這個電子的幾率分布可以延伸到無限遠處。
你也從未看到過一棵完整的樹。須知,大樹的地下部分與地上部分同等壯觀。它的根系可以延伸至幾米、十幾米,而它最活躍的根毛尖端則是一個長八十至一千五百微米、直徑十微米的單個細胞。有誰能不失一個根毛細胞地挖出一棵完整的樹?同理,又有哪位植物學家敢說他見過一株如此絕對完整、不失纖毫的草?
你甚至看不到一顆完全的星。我們看到的星光或許只是它幾萬年前發出的極小一部分光(而且它現在已不在你所看到的位置上了),它的絕大多數星光都已輻射到太空中去了。
在這完全沒有全同的大自然中,要想得到可視為“相同”的一類事物必須具備適度“模糊”的粗略眼光。如同經過嚴格挑選的儀仗隊士兵,高矮、胖瘦、著裝都一樣,近瞧細看卻仍是眉眼有別。倘若是在大霧天氣,驀然一瞥就可視為全同。唯有模糊了非主要因素,掩蔽其次要差異,才可能無需分辨地將本質相同的一些事物視為同一,并將它們歸為一類。有了類別才可以產生名詞、動詞、數詞,才可以有語言,有邏輯思維,有科學,有數學。
由是觀之,構成語言之詞必須帶有某種得以概括全員的“粗粒化”特征。正是借助這些抽象“顆粒”之間多種多樣的組合,才會在我們頭腦中整合成無比精彩的大千世界。其融合過程很像法國印象派畫家修拉所創立的“點彩派”技法。他的一幅名畫《大碗島上的星期日下午》描繪了巴黎奧尼埃大碗島上人們假日休閑的情景。與傳統畫法截然不同的是,畫家不施油彩,全部使用直徑一毫米左右的紅黃綠三原色小圓片,按照畫面配色所需,精心選擇恰當比例的小原色片貼附在畫布上。畫家巧妙地借用了人眼分辨率的有限,當你退到三米開外,各種不同配比的三原色彩點在你分辨略顯模糊的眼中自行“調色”,其整體效果與畫家手持調色板的傳統設色技法毫無二致。僅僅借助了視覺“模糊”即可讓有限品種的“粗粒”幻化出無限色階的細膩色彩。
堪稱“粗粒化”極致的要數達利那幅油畫《眺望大海的裸體加拉》。畫面僅僅由不足兩百個方塊組成,近看是裸女背影,退至二十米之外觀賞,一幀美國總統林肯的頭像就會浮現出來。
從科學視角來看,沒有重復就沒有規律可循,當然也就不會產生科學。既然“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故嚴格說來世上本無真正意義上的完全重復。唯有保持適度模糊,忽略次要因素,人們才有可能觀察到一系列所謂的“可重復事件”,并從這種穩定重復中把握事物運動的共同特征,發現其內在規律。
“粗粒化”還表現在對自然的雕鑿上。大自然渾然一體,原本無“數”、無“量”、無“階”。由于人們創立了使之得以分割的升斗、尺寸、斤兩、分秒等“單位”,又創制了相應的各類量具才有了“量度”,也才有了“數”。有此量化之后才會有科學測量,才可得出定量的科學公式(當然也就同時有了“精度”與“誤差”)。如同一處坡度連續的山丘,人們唯有把它鑿成步步臺階才有了拾級而上。藝術也同樣如此,本是連貫的鶯聲婉轉,非得把地籟天聲的連續音域“鑿成”音階才可譜寫音樂歌曲。
沒有“鑿階”,沒有量化就沒有人類現代文明,當然也就不可能有科學。《莊子·應帝王》中說:“南海之帝倏,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人類對自然也是如此,諸多自然之物本來無階,人類擅自將其鑿階,所得之物已非原本之自然,當屬人工之物。亡自然而起人工,自會與自然疏離。然而,不施鑿階又哪來的科學?
科學借虛問實
通常的抽象都是對具體實物的直接抽象,唯有“科學”抽象卻是疊床架屋的游離實體,對一些實際上并不存在的虛擬體系完成抽象。
它首先通過抽象思維設定一組虛擬元素,然后用它們架構起完整的理想體系,通過對這個體系進行邏輯推演來創立一整套簡潔、嚴格、嚴密的科學理論。例如物理學、數學,通過科學抽象引入一些現實并不存在的極端形態——有質量而沒有大小形狀的“質點”、電量集中于一點而不必考慮形狀分布的“點電荷”、沒有任何分子間作用力的“理想氣體”,以及幾何學中沒有面積的“點”、沒有寬度的“線”、沒有厚度的“面”——然后再借助這些元素構建出相應的物理學、數學體系。所有科學理論都是對這些體系進行演繹推導而得出的。這種以虛求實的科學抽象確是不同凡響,就其所涉體系而言,導出的科學規律足以闡明一切,指導一切,預示一切。
科學抽象是對現實世界的超越。這種抽象雖屬于主觀精神范疇,卻是對客觀規律最本質、最深刻的反映,也因此而帶有普遍性與穩定性。在抽象過程中它最大限度地摒棄了所有的個體差異,從而讓其共性得以凸顯出來。故此假想的極限狀態也完全擺脫了現實的干擾,使所得科學規律最具顛撲不破的堅實性。你可以顛覆“具象”,卻無法顛覆“抽象”。
科學抽象由于進行了最為徹底的簡化,也就必然會與客觀真實存在差距。這使得任何科學理論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來自本源的近似性。雖說現實世界中沒有哪一樣事物會嚴格按照理想化的科學規律演進,但任何事物的運動又都確鑿無疑地必定以它作為依據。
抽象是事物的“靈魂”,它支配著一切事物的運動,一切本質上的真實俱在抽象之中。
抽象通“神”,它使人們得以深切探知造物主的本來意志。
沒有抽象,便沒有科學。
在科學研究中確立理想狀態固然必要,而在發現與驗證這些規律過程中,為了消減變數,簡化影響因子,有時還需要專門設定一些現實中罕有存在的實驗條件。如研究氣體的體積、溫度與壓力三者關系的“氣體狀態方程”,不僅要采用極稀薄狀態的理想氣體,還會要求三個變量之中,每次體系變化必須要讓其中一個保持恒定,只觀察另外兩個變量之間的變化依賴關系。這樣更有利于發現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的定量關系。
科學是件“百衲衣”
大自然是個無窮嵌套的統一體,從微觀、宏觀,到宇觀,依據不同的尺度劃分為各種不同的層次。各層次之間互相聯系,渾然一體,成為一個協同運動的整體。
科學由于其自身視野的局限,不可能同時聚焦于所有的物質層次,使其得以全然一體地審視這些同時發生卻又層次迥異的運動狀態。
科學只能割裂自然!要么見樹木不見森林,要么見森林不見樹木,要么見得樹葉微觀脈絡,森林與樹木兩者皆不見。就像一位專業攝影師針對不同拍攝對象的體量大小、距離遠近,必須為同一母機配置一系列不同焦距的鏡頭:廣角鏡頭、長焦距鏡頭、常距鏡頭、微距鏡頭……
曾經見到過一張像素極高的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的數碼照片,幾百萬人聚集在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上,展示在計算機屏幕上可謂人頭如蟻。但你只要隨意點到某個角落的某一小點,將圖像一次一次地連續放大,最后你都可以清楚地辨別出這一微小區域里的每一張臉。然而,科學對這個業已膨脹了一百三十七億年的整個宇宙卻不可能給出這樣一張無限像素的全景“照片”,使其也像就職慶典照片那樣讓你點到銀河星系,一次次放大后再點到太陽系,反復放大后點到地球,再依次放大,點到北京,點到西城區,點到一座四合院,點到院子里坐著的一個人,點到他的臉,他的鼻尖,點到他鼻尖上的一個汗毛孔,孔中的一個細胞,點到細胞核,DNA雙螺旋大分子,點到其中一個碳原子,碳原子核,點到核中的基本粒子,夸克……當然,你還可以點開太陽系的木星看大紅斑,或看前幾年小行星撞擊出的一連串隕坑,可以點開一顆白矮星看它的元素組成,看這種超高密度下物質的微觀結構……宇宙的一切俱在科學渾然一體的通覽之中。可惜“科學”完全不具備這種全景式的視野!
各行各業的科學家就像一群高度近視的人并排圍觀宋代張擇端繪制的那幅五點二五米的《清明上河圖》:在擁擠的人頭攢聚中,有的湊近汴河拱橋,仔細研究它的木架結構,成了橋梁專家;有的研究巨舸風帆、槳舵,以及遇橋放倒桅桿的折疊裝置,成了船舶專家;有的從刀剪鋪產品考察北宋的冶鐵工業;有的從高懸酒幡上的“新酒”二字推斷出北宋多為低度“米酒”,尚未普及高度蒸餾酒;有從“神課”招牌研究測字問卦的;有從“看病”字牌研究醫生坐堂問診的;有專門研究城樓建筑結構的;有研究酒肆飯館上下兩層布局的;有研究宋代民間服飾的;有研究集市貿易的,等等。所有科目中就數研究運輸的專家最多,而且還分成幾個學科分支,有的趴在那里研究牛車運貨,有的專攻駝隊運輸,有的關注小奚奴的趕驢馱運,有的論證拱形橋梁要求貨車須加強配置雙驢、雙牛,或四馬畜力……遺憾的是,諸多高度近視觀畫者中竟無一人能擺脫目光局限,足以高瞻遠矚,統攬畫卷全幅!
其實,對觀看“自然長卷”的科學探究人而言,他們不僅比這些分段研讀《清明上河圖》的人還要近視,更為至關重要的是——不同學科的科學家簡直就像原始山林中彼此隔絕,語言不通的“科學部落”,由于缺乏專業共同“語言”,也使得各學科之間絕少溝通。眾多科學家確是“隔行如隔山”!不信你去對地質學家談“頂夸克”和“粲夸克”,對天文學家談“酶”的蛋白質結構,對數學家談馬門溪龍,對生物學家談脈沖星……絕對的一臉茫然!
然而大自然的運動又是全然一體化的。一個碳-14原子,當它原子核發生β-衰變的同時,它的原子又參與組成了金剛石立方面心晶胞,此晶胞又嵌在巖石晶體里,長在某一礦脈之中,這礦脈又埋藏在大山深處隨地球繞著太陽旋轉與自轉,這太陽系又在銀盤平面上以每秒二百二十五公里的速度,歷時二點二五億年繞銀心公轉一周,同時它又寓于銀河系某一根旋臂中,隨從整個漩渦星系在宇宙中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是同時進行的,僅僅是由于科學各學科的視野局域才使我們不得不將這些運動形式割裂開來,分門別類予以研究。為此,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研究成果”也只能是一些離散的互相分割的知識,這些分門別類的專業成果需要在我們的大腦中通過思維將其整合,成為較為整體性的科學識見。
大自然原本“天衣無縫”,我們卻承載不起,只能人為剪下霓裳一片,供一群志同道合的專家們共同問究鉆研。各科學分支所織績的“布片”相對完整,自成體系,但片與片之間并非緊密系縛,只是粗針大線地彼此勾連在一起。神圣的科學就是這樣一件草草縫合的“百衲衣”,虔誠的科學圣徒們正是披著這件由眾多科學“碎片”連綴而成的“百納袈裟”,法度莊嚴,踽踽獨行于崎嶇的未知探索的征途上。
不要小看這件百衲衣,它上面每一片布的存在都必須嚴格遵從造物主的意志。再強勢的人也休想憑借科學以外的力量,狗尾續貂地補綴上一小片專署自己名字的破布片,哪怕是一絲一縷也難以得逞。誰若心胸狹隘地想從上面扯下一片與自己理念抵牾的衲衣布片也是癡心妄想。科學百衲衣看似粗率,卻是件“圣物”!
科學是座“懸空寺”
莊嚴的科學殿堂其實是一座僅靠著幾根“虛空支柱”撐持起來的“空中樓閣”。它很像北岳恒山的那座懸空寺——離地五十余米,唯見十幾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撐,“上延霄客,下絕囂浮”,嵌于萬仞峭壁之中。
全部科學體系僅僅依靠幾條基本假設撐起。這些人為的假設定律你只能接受,必須承認,別問為什么,也完全無須和你講明道理——“能量守恒原理”、“物質不生不滅”、“絕對零度不可達”、“三角形三內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動者恒動,靜者恒靜”、“力等于質量與加速度的乘積”,相對論假設“光速不變”,量子論假設“能量不連續”……雖說科學的所有理論都經歷過嚴格的驗證,但唯獨支撐全部科學的這些看似武斷的基本假設與定律卻全都沒有經過任何論證。沒有誰知道它們為什么會是這樣,也沒有哪一位權威向你解釋過其中的道理。在這些足可視為“天條”的基本假設面前,再桀驁不馴的科學家也得俯首聽命,再慣于懷疑一切的科學家也會堅信不疑。都說“人生識字糊涂始”,其實科學理論才是真正的“糊涂始”,打從根上就沒想讓你知曉這些基本律則之所以然。然而令人折服的是,這些根本性假設卻是那么的傲睨自若,安如磐石,經得起任何詰問——縱然無須證實我對,但任何人休想將我“證偽”!
全部需要嚴格證實的科學體系卻是靠著幾條完全未經證明的假設來支撐——真乃普天之下最大的“悖論”!
然而令人擊節嘆賞的是,依靠“假設”支撐起來的這座神圣莊嚴、堅實無比的科學“懸空寺”竟是何等的宏偉壯觀,前來朝拜的科學信徒又是多么的敬畏虔誠!
假說自有假說的威力!其中最具魅力的莫過于化學關于“原子”的假說。自古希臘留基波和德謨克利特創立《原子論》假說以來,19世紀初英國化學家道爾頓結合“定比定律”、“倍比定律”把“原子說”變成為一個科學概念。此后通過一系列化學實驗,人們精確地測出了每個元素的原子量,定出了每種原子的化合價,給出了每一元素的“原子序”,寫出了由各種原子組成的分子式,搭出了立體的分子結構模型,排出了“化學元素周期表”,甚至建立了龐大的化學工業,按照化學反應方程式定量生產出了數不勝數的化學制品,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但是又有誰見過原子,證實過原子存在呢?完全沒有!無怪乎日本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湯川秀樹在其《基本粒子》一書中承認:關于原子的概念仍舊只是一種“假說”!當我們習以為常地享受各種琳瑯滿目的化學制品的時候,又有誰會去想,獨自支撐整座化學殿堂的最主要的支柱,長達兩千多年來竟然只是一種虛之又虛,未經證實的“原子假說”!值得慶幸的是,只是在近幾十年人們通過掃描隧道電子顯微鏡(STM)總算看到了原子的直觀圖像。
科學從源頭上就已成功地駕馭了“真”“假”相反相成的依存關系,不僅刪繁就簡地設立一些假想的、現實并不存在的理想狀態(質點、點電荷、點、線、面),還通過精深的悟性確立一些假設定律來作為整個科學殿堂的支撐。
真理之“真”建立在假想、假說之“假”的基礎上,雖稱不上“假作真來真亦假”,也可算是“假”撐“真”來真愈真。
科學永遠也不可能抵達絕對真實的彼岸
無限復雜的“絕對真實”是科學永遠無法達到的彼岸。
宇宙中任何事物都處在普遍的聯系之中。任何現象的發生都會伴有一系列數不勝數的“現象群”與之同時共生。科學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將他所研究的體系盡可能從這個相互纏結的現象群中剝離出來,剝離得越干凈、越徹底,體系就越簡單,對發現科學規律也就越有利。我在《敬畏自然》中曾經描述過從樹葉上滴下一滴雨水的過程,它看似簡單,任何一個中學生都可以用自由落體公式計算其下落全程,但若考慮到與之相關的所有影響因素:潮汐、海拔、緯度、傾角、溫度、濕度、風速、蒸發、氣泡、液滴震蕩、磁場作用、沖擊增壓、尾流減壓、灰塵與溶解的分泌物……這個滴落過程實際上是無限復雜的。
“理想氣體狀態方程”也是這樣,它只有在極其稀薄的惰性氣體中才能較好符合,并保持了公式的簡潔形式。但若想包容各種影響因素,力求使公式計算結果符合實際,就必須給這件完美精當的華服補綴上一塊又一塊的“補丁”:用于實際氣體需加上一個修正項“補丁”,并非稀薄氣體又得加上一項修正“補丁”,考慮氣體分子的極性作用再加個修正項“補丁”……這樣的修正項可以是無窮多的。雖說每加一個修正項,它的計算結果就會與實際測量更接近一步,然而,修正項太多,公式長長一串,這個氣體狀態方程也就不成其為科學公式了。更何況你不可能窮盡所有影響因素,公式再長也不可能使你的計算百分之百符合絕對真實。
面對無限艱深的大自然人類智能終歸是有限的。
在古代科學尚未發軔時期,人們對一切自然現象茫然無知,先民們在威力無比的大自然面前是那么的無助:洪水、海嘯、地震、火山、雷電、林火、暴雨、狂風……各種災難讓他們深切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嚴、深奧與不可抗拒。先民內心中把這些難以抵御的自然現象全都當作各種主宰之神來頂禮膜拜。
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在宏觀物質層次建立了堪稱完美的經典科學體系,包括歐幾里得幾何學、牛頓力學、經典熱力學與統計力學、光學、電磁學、化學元素周期律、達爾文進化論……使得人類文明在科學領域達到無以倫比的巔峰。
經典科學之所以如此全面地達到了頂峰,這首先在于這些科學研究使用了簡單直觀的科學手段:法拉第使用過鐵桶和驗電器,牧師孟德爾利用業余時間自種豌豆研究遺傳基因,伽利略親手磨制鏡片組成天文望遠鏡,門捷列夫用類似紙牌的卡片來排列元素周期表。其次,這些研究成果讓公眾憑著直覺經驗就可充分理解,科學直通民眾使全人類都受到空前鼓舞。再次,經典科學帶動了技術的突飛猛進,產生了許多提高生產效率的機器產品,并讓人們充分享受到了美好的科技成果,如蒸汽機、電動機、內燃機、火車、汽車、輪船、電燈、電話、電影、電訊……
經典科學使人類智能達到了空前絕后的偉大輝煌,那時科學家牛頓、愛迪生所享譽的偉大盛名絕不遜于古代西方蓋世英雄愷撒大帝、亞歷山大大帝。此后的科學再也沒有如此燦然炫目過。
當經典科學天空一派晴朗之時,驀然飄來兩片烏云晦暗了整座科學殿堂,這也意味著經典科學的終結。以相對論、量子論為代表的現代科學雖然也曾產生過激動人心的偉大時刻,創造出核動力、計算機、互聯網、激光技術、宇宙航行、家用電器、智能手機……讓人們的生活再次為之改觀。但毋庸諱言,莫測高深的科學理論也日漸疏離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理念與直觀體驗。它再也不會像經典科學那樣易于理解,便于接受了。
如果說當年愛因斯坦四維時空、海森堡測不準關系、波函數、矩陣力學還能讓公眾勉強接受的話,現在霍金的十一維空間以及借助艱深數學與諸多玄奧概念(宇宙波函數、時空奇點……)的科學理論讓一些訓練有素的理論界權威都已然陷入困頓之中。原本為人釋疑解惑的科學,如今業已變得日益艱澀難懂,反倒讓人平添了諸多困惑。而且,愈是執迷科學愈深,久為此科學所化之人,其所感受困惑之量程亦愈甚。
在經典科學時代,有時科學家在隨常生活之中即可發現新的科學規律。伽利略坐在教堂里看到屋頂吊燈的晃動,以自己的脈搏作為計時發現了“單擺運動”規律。阿基米德洗澡時身體泡入澡盆的一剎那受到啟發,從而發現了“液體浮力”規律。如今科學發現已日漸艱難,科學難題也日益玄深,落入荒谷的科學早已遠離公眾視野,變成純屬少數科學家的事業了。各路科學人馬面對層層科學難題更是顯得力不從心。人們逐漸清醒:作為科學家有待攻克的“對手”,我們所面對的大自然已然是在居高臨下地以逸待勞。而且“對手”這種縱橫交錯的統一布陣,似乎還帶點誘敵深入的謀略——讓經典科學大軍順利得手大獲全勝之后,成為一支脫離公眾視野的科學孤軍,驀然被引入到一片十面埋伏、殊難攻陷的堡壘群陣之中。可以說,在這些遠離宏觀層面的科學領域里,留下來的個個都是啃咬不動的科學難題。面對攻堅難度逐級增強的重重壁壘,科學家早已消解了經典科學時期那種意得志滿的底氣十足。
這支科學孤軍的后勤補給業已日益困難,主要是開銷實在太大。現代科學超級靡費的投入竟然如此高昂,像哈勃望遠鏡、火星探測器這些還只不過是在太陽系小圈子里轉悠的探測裝置,其花費就已經沒有幾個國家承受得起了。幾十年前歐洲(CERN)造個大加速器還要籌集西歐幾國財力共同建造維持。我們的地球畢竟資源有限、能源有限,若想窮極宇宙諸多大問,小小地球將何以堪?
更何況當前人類還面臨著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它們早就在長年累月地困擾著我們,現在更加頻亮紅燈,時時緊逼,處處危機:環境污染、水源短缺、糧食匱乏、能源危機、氣候異常、土壤沙化、人口膨脹,煤炭和石油只夠用幾百年,還有幾億人吃不飽,更有雪上加霜的連年戰爭與巨額軍費開支,我們又能有多少余力去填補這個耗費龐大無比的“純科學”無底洞呢?
為著人類的長遠生存,我們應該更為得當地支配這點有限的智能、資源與時間——避免用于耗資巨大的毀滅性戰爭,審慎投入那些用錢無度又永無盡頭的科學探究,杜絕窮奢極欲的掠奪與惡化生存環境。身居有限,心存無限,遙望彼岸,珍攝家園。
大自然是不可窮盡的,它宏觀無限,微觀無限,艱深無限,復雜無限,而人類的探究能力畢竟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科學面對無限的大自然,這本身就是個永遠不可企及的彼岸!
彼岸玄深,奧秘不可窮盡,得以領略,便是夙緣。“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