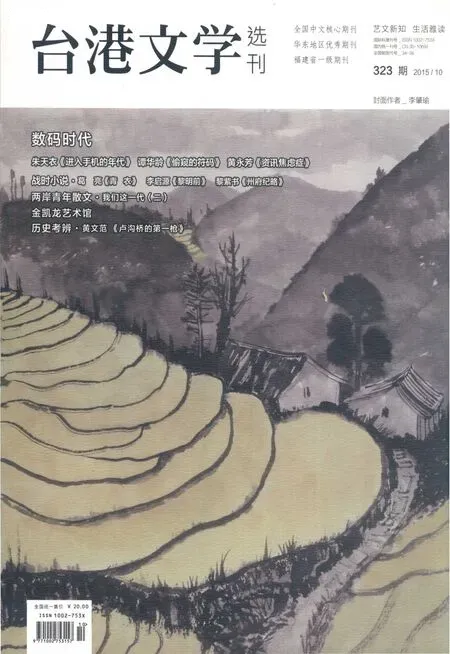進(jìn)入手機(jī)的年代

我是一直堅(jiān)持到七年前才擁有第一支手機(jī),而且一直使用到今天從未換過,即便在這期間,它曾被我摔在地上四分五裂過,但經(jīng)過重新組合,功能卻一點(diǎn)也沒受影響。為此,我覺得這家瑞典手機(jī)廠商真該找我去當(dāng)他們的活廣告。
手機(jī)之于我,只要能收話、撥號(hào)就可以了,我是連簡訊都不傳、也不會(huì)傳,其他功能就更不必談了,但即使我是以最原始的方式在使用手機(jī),甚至潛意識(shí)里抗拒著它所帶來的干擾,但用慣了它,若忘了帶它出門,那便會(huì)惶惶然的少了分安全感,幾乎要忘了當(dāng)初沒有手機(jī)的年代都是怎么過活的了,不過話又說回來,當(dāng)時(shí)似乎也沒錯(cuò)過什么。
在還沒有手機(jī)時(shí),曾流行過好幾年的“B·B·Call”它一開始應(yīng)該是針對某些需要隨傳隨到的特定人士設(shè)計(jì)的,比如說醫(yī)生,急診、接生都需要靠它傳呼,我年輕時(shí)曾主持過一次外科醫(yī)學(xué)年會(huì),席問“B·B·Call”便此起彼落叫個(gè)不停,我和學(xué)生談起這物件的功用時(shí),看他們的表情,我好像是在描述一件古化石,至于那傳送訊息的阿拉伯?dāng)?shù)字各有其意義,更讓他們匪夷所思,比如“520”代表“我愛你”,“5757”是那個(gè)常在中午約會(huì)的“小三”來電,在他們眼中,這簡直像原始人的壁畫般令人費(fèi)解,而這一切不過是二十年前發(fā)生的事,所以目前我所使用的手機(jī)會(huì)被當(dāng)作古董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說到古董手機(jī),我每次拿著自己碩大的鉛筆盒,比擬第一代手機(jī)的模樣,都可看到學(xué)生嘴巴張成O字形,難怪當(dāng)時(shí)它有另一個(gè)稱號(hào)“大哥大”,果真是好大一個(gè)呀!初始時(shí),手機(jī)號(hào)碼受到控管,不是有錢就能擁有的。我在一九九五年參選“立委”時(shí),便曾獲準(zhǔn)可申請二十個(gè)號(hào)碼,我自己沒這需求,一方面那時(shí)話費(fèi)特高,再者,為什么要隨時(shí)待命等著接電話?這不是自找苦吃?所以這特權(quán)于我是無意義的。
后來真的擁有手機(jī),我最常使用的是在擁擠的公共場合,被人潮沖散時(shí)可借著它找到對方;另外我們家院子大且崎嶇,有時(shí)也得靠它尋找那躲在角落的人。至于行車間看到任何危急或不公不義的事,便靠它通知警方,這對老愛管閑事的我,手機(jī)便成了路見不平那把可用的刀了。
不過,我一直很欣羨有些人打電話總是輕聲細(xì)氣的,和我一樣習(xí)慣提高音量打電話的大姐,常被二姐笑作是“鄉(xiāng)下人打電話”。我們的大嗓門,應(yīng)該源自對機(jī)器的不信任吧。要靠那小小的東西遠(yuǎn)距離傳遞訊息,對我這類原始人的思維,還真需要點(diǎn)想象力呀!
(選自臺(tái)灣城邦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麥田出版《記憶如此奇妙:朱天衣散文集》)
- 臺(tái)港文學(xué)選刊的其它文章
- 餓與福州干拌面
- 人文薈萃的福州三坊七巷
- 日本:e病纏身的年輕社會(huì)
- 福州印象
- 州府紀(jì)略
- 黎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