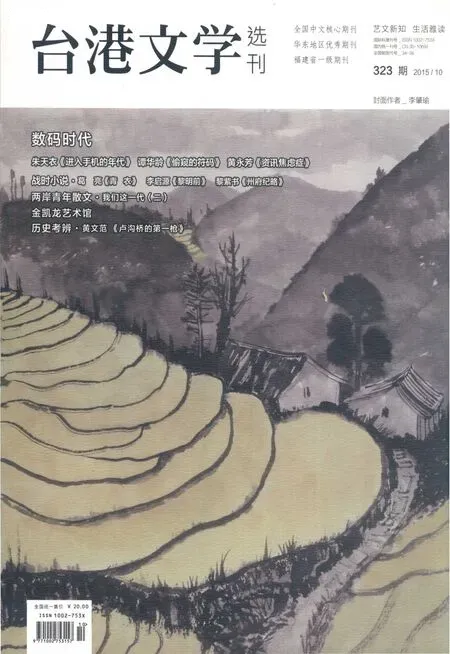餓與福州干拌面

逯耀東,江蘇豐縣人,193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學位。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散文集《那年初一》、《異鄉人手記》、《過客》、《窗外有棵相思》等,另有史論專著多部。曾獲臺灣散文金筆獎、文藝獎等。
那一年,該是1956年,我大三的那個暑假。不知誰說的,大學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但到了大三,已是夕陽無限好了。因為過了這個暑假,到了明年驪歌唱罷,出得校門,就前途未卜。
所以,那個暑假留在學校沒有歸家,只是為了享受一枕蟬詠,半窗斜陽,但卻挨了餓。暑假宿舍人口流動頻繁,伙食費五天一繳,雖然為數不多,但錢已被我用罄,而且庭訓有示,出門在外,最忌向人借貸,于是,我就挨餓了。
餓是啥滋味,我過去曾在課堂上問過學生,他們瞠目以對,然后我說我們那年月都挨過餓。他們竟說我運乖,沒有遇到個好爸爸。的確,挨餓的經驗我是有過的,少年時隨家人在敵人的炮火下,倉皇逃難,拉起來一兩天沒飯吃是常事,喝一口山澗水,就一口蒜瓣就頂過去了。人說生蒜瓣可以解毒。
后來因事被捕入獄,其實我被捕也不是犯了什么大案,只是在課堂上寫“致前方將士書”,出了岔子。小小十六歲的年紀就唱了“男起解”,從嘉義遞解臺北,在里面蹲了三個多月,尤在臺北號子里的那段日子,真正嘗到餓的滋味。
在那里蹲了兩個多月,出來后,我發誓不再吃黃蘿卜那種東西,不過,卻練得無菜干吞白飯的功夫。
現在我真的挨餓了,而且沒有任何逼迫,自由自在挨餓,真是一錢逼死英雄漢。想到孔子當年在陳絕糧,竟弦歌不輟,老夫子真有一套挨餓的功夫。于是整衣端坐,掀書而讀,但讀了不到兩頁,但覺字行搖晃。前胸貼后心,腹內油煎火燎,一個字也讀不下去。心想肚子
是盤磨,睡倒不喝也不餓。不過,睡前還得填填胃,于是拿了漱口杯,到隔壁洗澡房,對著水龍頭,灌了幾杯自來水,回到寢室,立即上床睡覺。雖說水可壓餓,但喝多了也不好受,水在肚子里晃蕩,平躺也不是,側臥也不行。室外蟬鳴聲噪,反復難眠。突然想起今天是我
自己的生日,于是一躍而起,想到早晨買新樂園,還剩下五毛錢,出得校門,買了張公車票,到小南門。我女朋友在小南門醫院實習。見了她就說:“今天是我生日,你得請我吃碗面。”她一聽笑了說:“怎么,又花冒頭了。”于是,她換了工作服,陪我到醫院門口的面攤吃面。
那個小面攤開在小南門旁的榕樹下,依偎著榕樹搭建的違章建筑,是對福州夫婦開的,賣的是干拌面和福州魚丸湯。雖然這小面攤不起眼,日后流行的福州傻瓜干拌面便源于此。但福州傻瓜面和這小攤子的干拌面相較,是不可以道里計的。福州干拌面的好與否,就在面出鍋時的一甩,將面湯甩盡,然后以豬油蔥花蝦油拌之,臨上桌時滴烏醋數滴,然后和拌之,面條互不黏連,條條入味,軟硬恰到好處,入口爽滑香膩,且有蝦油鮮味,烏醋更能提味。現在的傻瓜面采現代化經營,雖然面也是臨吃下鍋,鍋內的湯渾濁如漿,鍋旁的面碗堆得像金字塔,面出鍋哪里還有工夫一甩,我在灶上看過,也在堂里吃過,真的是恨不見替人了。
我連扒了兩碗到第三碗時,才喝了口魚丸湯。抬起頭來看見坐在對面微笑的她,說了句:“大概可以了。”后來她成了我太太,四十多年來相持相伴,生活雖然清平,卻沒有再餓著。太太是湖南人,在西安長大,習慣各種面食,但卻不喜吃面條。我豐沛子弟,自幼飄泊四方,對于飲食不忌不挑,不過自此后,就歡喜這種福州干拌面了。
1949年逃難到福州,在那里住了快半年,而且還混了個初中畢業文憑。當時兵荒馬亂,幣值一日數貶,后來不用紙幣改用袁大頭,或以物易物,拉黃包車的早晨出門帶把秤,車價以米計,拉了天黑就回家,車上堆了大包小包的米。我當時住校,每周回家,返校時母親就給我一枚金戒指,作為一周的食用。我記得當時一斤肉七厘金,一碗面是三厘,有各種不同澆頭的福州面,有鴨、蚵仔(蚵仔是現剝的)、黃(瓜)魚、螃蟹等等,面用意面,下蝦油與面湯共煮,味極鮮美。不過,我更佩服老板剪金子的工夫,一剪刀下去恰恰三厘,不多不少。后來來臺灣一直懷念福州面的味道,早年勝利的海鮮米粉尚有幾分余韻,現在已經沒有了。不僅臺北,我曾兩下福州,也沒有吃到那種風味的福州面。不過,在福州卻沒有吃過福州的干拌面。不知臺灣的福州干拌面,是否像川味牛肉面一樣,是在地經過融合以后,出現的一種福州味的干拌面。
臺灣是個移民社會,當年從唐山過臺灣的福州移民并不多,但福州的三把刀:裁縫的剪刀、理發的剃刀、廚師的菜刀對當年臺灣社會生活影響很大。現在三把刀已失去其原有的社會功能,只剩下干拌面和魚丸湯,融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臺灣流行的干面,除福州干拌
面外,還有鹽水的干拌意面、切仔干拌面及炸醬面。這三種拌面用的面料各有不同,意面來自福州,切仔面的油面,傳自泉漳與廈門的閩南地區,炸醬面用的是機制的山東拉面,很少用手搟的切面。我曾在廈門一個市場,吃過下水切仔拌面,用的就是油面,味極佳,面中也
以韭菜、綠豆芽相伴。福州干拌面用的是細面,現在稱陽春面,陽春面名傳自江南,取陽春白雪之意,即所謂的光面。
福州干拌面雖平常之物,但真正可口的卻難覓。后來在寧波西街南昌路橫巷中尋得一檔,是對中年福州夫婦經營的面攤,由婦人當爐,別看她是個婦道人家,臂力甚強,面出鍋一甩,面湯盡消,清爽,十分可口。男的蹲在地上攪拌魚丸漿,是新鮮海鰻身上刮下來的,然后填餡浮于水中,他家的魚丸完全手工打成,爽嫩,餡鮮而有汁,吃福州干拌面應配福州魚丸湯,但好的福州魚丸也難尋。我在這家面攤吃了多年,從老板的孩子圍著攤子轉跑,到孩子長大娶妻生子,后來老板得病,攤子也收了。
日前,太太去法國旅行,夜里打電話回來報平安,并問我早上吃什么。我說去市場吃碗干拌面。我家附近的小菜市場有家賣干拌面的店,老板矮矮胖胖的,五十來歲的福州伯,后來得急病死了,面店由兒子接手,經過五六年才練得他父親下面的功夫。每次我去,他都說
聲照舊。所謂照舊,是一碗干拌面,配一碗餛飩湯另加一個嫩荷包蛋,面來,與荷包蛋移至面碗中。與面同拌,蛋黃滲于面內,又是另一種味道。
(節選自臺灣九歌出版社“2003年散文選”)
本輯責編__馬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