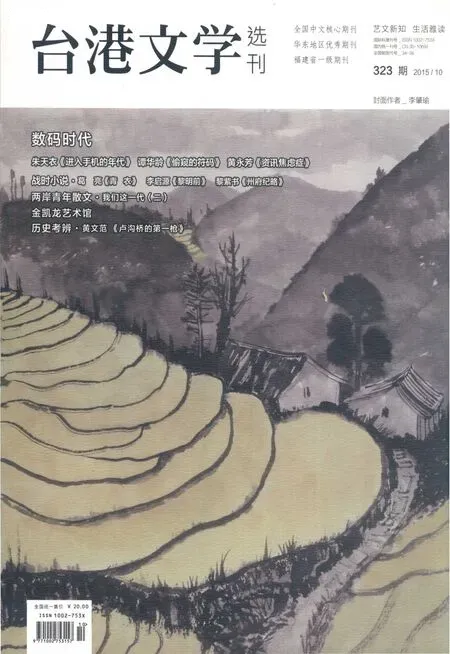青衣



葛亮,1978年生。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執教于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著有中短篇小說集《謎鴉》、《七聲》、《相忘江湖的魚》等,曾獲第一屆香港書獎、第十九屆臺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作品曾入選《二十一世紀中國新文學大系》、臺灣2006年“誠品選書”等。
仁楨第一次見到言秋凰,是一九三七年。她記得清楚。
她是在十條巷的巷口看到言秋凰的。她先看到的是父親馮明煥。父親清癯瘦高的背影,還有顏色有些發舊的墨藍綢長衫,都很易辨認。
按理,她放學很少走過這條巷子。這一天,是因為突然很想吃“永祿記”的糖耳糕,便纏著二姐拐到了這里。這時候,她覺出仁玨的手心里,滲出了細密的汗。幾步之遙,她本能一樣,喚了一聲,“爹”。
仁玨原本僵在原地,聽到這聲卻手里一緊,牽著她就要轉身。但一切已經來不及。也是本能一樣,明煥聽到熟悉的聲音,回過頭。
仁楨看到父親面無表情,眼神空洞無內容。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竟然挪動不開。卻見對面的陌生女人,遲疑了一下,臉上泛起柔和的笑。女人款款地走過來,躬下了身子,對她說,我沒猜錯,這就是楨兒。老聽你爸說起你。
仁楨聞到一陣不知名的香氣,從這女人身上彌漫過來。這香味十分豐熟溫暖,竟讓她不覺間嗅了一下鼻子。
沒有等她回答,女人站起身,輕輕說,這位是二小姐吧。仁楨看見姐姐卻昂一下頭,將眼光偏到一邊去。
仁楨覺得二姐的神情,未免有些不太禮貌。她便和事佬一般地開了口說,請問,你是誰?
女人笑了,露出整齊的牙齒。牙很美,細密如同白色的貝殼。她執過仁楨的手,打開,在她掌心一筆一畫地寫下一個字。仁楨也笑了,因為手心很癢。
她說,這是我的姓。
你姓“言”啊。仁楨辨認出了這個字,很興奮,原來這還是個姓。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們都叫我言小姐。
言小姐。仁楨重復了一遍,覺得這聲音的綿糯,是很符合她對“小姐”這個詞的想象的。這稱呼應該是有些柔和嬌,帶有著被呵護的成份。她覺得自己和一眾姐妹,性格里都有些鏗鏘,便似乎當不起。這女人,其實穿戴是很樸素的,甚至臉上并沒有妝。但看著你的時候,眼睛里卻有跌宕。一層層的,最里面一層,是種懶懶的困意,卻有要討好的意思。當仁楨看出了這層意思,就突然在心底生出好感來。
她就從身邊的袋里,取出一塊糖耳糕,放在言小姐還攤開著的手心里,說:請你吃。
女人說,是“永祿記”的吧,我最愛吃,就不客氣了。說完又笑了。這一回,仁楨因看得仔細,發現這自稱小姐的人,眼角已有了淺淺的紋路。
女人回過身,仁楨看見她松綠色的旗袍,簌簌響了一下,隨著身體的扭動泛起波瀾。女人說,馮先生好福氣。令嬡年幼,已是知書達理。
又說,不知道我后天的大戲,楨小姐賞不賞面來呢?
這時候,仁楨突然驚覺,這女人便是活在家人口中的“戲子”言秋凰。這實在是有些意外。跟著父親,看過她演的一出《鎖麟囊》。臺上那個人的光彩,與唱腔,美得不可方物。雖則長輩們提起這個名字,口吻都十分微妙。但在她心里,卻好像是仙界下來的一個人。然而此時,立在眼前,卻讓她意外了。這意外是因為,這女人的家常與普通。仁楨甚至注意到,她手袋上的一粒水鉆,已經剝落,拖拉下一個很長的線頭。于是整個人,似乎也有些黯淡了。
也在這一剎那,她發現,在她與言秋凰對話的過程中,父親與姐姐,保持了始終的沉默。
多年以后,仁楨想起她與這女人的初遇,仍然覺得是美好的。哪怕此后,她的記憶受到歷史與他人的改寫。但對這個場景的重現,她會在心底蕩漾起一點暖。女人的面目日漸模糊,令她對曾發生的事情,有些不自信。她會尋找一些只字片語,讓那個下午重又清晰與豐滿起來。
她在一張發黃的報紙上,看到了女人的照片。報紙有些發脆,她將它小心地鋪展開,因為老花,她不得不彎下腰,讓自己與報紙保持了適當的距離。在那個時代,這張照片算是拍得十分好。言秋凰燙著波浪的鬈發,顧盼生姿。雖然是一貫的明星的樣態,幾乎有些刻板。但并不見一絲造作。笑得也好,并且在這含笑的眼睛里,她又看見了當年的那一點“討好”。這讓她心里動了一下。
報紙說的是言秋凰來到襄城前的一樁往事。大約在當時甚囂塵上。仁楨也曾聽家里的大人提及,可是總有些不自覺的夸張與游離。比如,說起言由北京一番輾轉,至此地,總是用“流落”一詞。這報上的文字,雖多少也有些小報口吻,但事情的脈絡,總歸還算是清楚
的。
說起來,作為梨園中人,言秋凰早年算是頗為順遂的。雖則當時女旦并不被看好。但言秋凰入行,卻是個機遇。原是有些家世的孩子,祖上是鑲藍旗的漢籍旗人,聽說和鄂爾泰一支還有過姻親。早年失怙,但有一個叔父,官至三等輕車部尉,駐在御河西岸的淳親王府。家境原是頗不錯的。可洋人打了來,一場“義和拳”,家業毀了一個干凈。叔父先是無罪失官,兩年后郁郁而終,生活便難以支撐。她嬸子就打通關節,將她送進親王府做了女侍。
淳親王府上的老福晉,原是個難伺候的人。但這孩子做事十分伶俐,因為家中變故,形于神色,眉目間又惹人哀憐,竟很得上下人的歡心。老福晉好戲,家中大小堂會,便是不斷。這小女孩子也頗學會了幾出。一次親王在園中,見這丫頭躲在僻靜處,口中咿呀,聽了
竟是一折《坐宮》。正唱到:“我這里走向前再把禮見,尊一聲駙馬爺細聽咱言。”這一段西皮流水,唱得雍容自如。再聽下去,念科都有式有樣。親王便很感慨,這孩子平時安靜訥言,此時卻煥發出了十二萬分的神采,或者真是祖師爺要賞飯吃。如此,便將她的嬸嬸找來,說是免了典價,送到戲班去好好栽培。
這戲班,便是當年京城稱首的“和云社”。拜了師傅,是大名鼎鼎的劉老板劉榮德。劉老板本是抱定不收女徒弟的,因為淳王爺所薦,就見了一見。這丫頭謙恭有禮,帶些男兒氣度。穩健中卻有些哀艾,再一聽聲音,竟真是唱青衣的好材料。也是爽快人,當時就拍板收
下了。原本那日桌上擺著本《苕溪漁隱叢話》。要聽這孩子音色,便讓她隨意念了一段。書上錄了蘇軾的句“秋風摵摵鳴枯蓼”。大約也是緊張,這孩子竟將“風”念作“凰”。做師傅的心里一動,倒覺得這錯是個吉兆,就干脆賜了個藝名“秋凰”。
做嬸嬸的,是個知恩承情的人。以后言秋凰紅了,念著老太太的話,從未忘本,將淳王爺與老福晉的壽誕銘記心中。到了時候,就去王府里唱一個晚上的堂會。三不五時有新排未公演的戲,又在王府先演上一場。老福晉八十壽辰,壓軸就是言秋凰新排的《謝瑤環》。如
此,言秋凰是分文不收,說是孝敬。這樣,王府上下,對她便愈發愛了。周邊的人,也都力捧。到了二十歲上,已經是京城數一數二的青衣。風頭甚至蓋過了師傅。
按說劉老板也是個很有心胸的人。愛才也惜才,對這個女徒弟的培養不遺余力。言秋凰紅了,他最初也是喜在心里。旁人多少有些閑話過耳,他也不當回事。
直至言秋凰有了自己的戲班“雨前社”。首演《碧玉簪》,那真個叫盛況空前。每晚的花籃幾十個堆疊得擁擁簇簇。場場爆滿,戲院門口,汽車一字排開二百多輛。茶會,堂會,言秋凰更無一絲之暇。相比之下,當師傅的這邊,倒顯出了寂寥來。
報紙上說的,是這年秋天的事情。也是梨園界著名的“劉言之爭”。后來好事的人,說這“流言”不祥,注定是一語成讖。《鐘業晚報》投票評選八大名伶。言秋凰與師傅排在了首十六位。說起來入圍的都卯足了勁頭。而唱青衣的,偏就是這師徒旗鼓相當,針尖麥芒。這年年底的游堂會,兩大劇院,一個在“銀興”,一個在“玉蟾”,真格地擺起了擂臺。捧劉與捧言的兩派唇槍舌戰,在各大報章上對上了火。一是久積薄發,一是銳氣當前。勢均力敵,難分伯仲。劇場夜夜高滿,觀眾是聽得如癡如醉。兩人是越唱越勇。這夜里散了場,劇場的經理帶了張字條來,說是劉老板托人捎來。言秋凰展開看了:“凰兒吾徒,明暫休一夜。念念。”恰這一夜是言秋凰在“銀興”連唱六場新編的《鎖麟囊》,廣告都貼了出去。想不能對觀眾食言,便又上了臺。到下傍晚,“玉蟾”也上了廣告,是劉老板的箱底劇目《玉堂春》。坊間便說,這一夜是有決戰的意味了。六場唱下來,叫好不絕。然而下了臺,言秋凰便看出眾人神色不對。追問之下,是師父在第二場倒在了臺上,咳出了一口血。
這張舊報紙的標題:“望鵑啼血花落去,新凰清音換新天”。這大約是言秋凰最后一次出現在新聞的頭版。后來,據說是她自愿退出了“八大名伶”的選舉。在眾人的不解與期待中,半年未再登臺。這年的年底,積郁成疾的師父歿了。她一身素裹,守了一個月的喪。臨
了給師父的遺像磕了一個頭,立下誓言,從此離開京津伶界。
后來,又有人說她在滬上停留。無奈一個女人,又少人扶持,竟分外艱難。洋場上的規矩,又正邪難循。一來二去,得罪了黑道上的人。好不容易脫了身,輾轉一番,才來到了襄城。
襄城這地方,比起京津,民風大約又淳樸容納些,言秋凰便安置下來,棲身在一個叫“榮和祥”的戲班。這里的票友知道來了個女伶,叫“賽慧貞”,也覺得稀罕,口耳相傳。開始的幾場,挨在幾個角兒當中唱上一段,便不覺得惹眼。后來一出《鴛鴦冢》,中有段西皮慢板,是極難把握的,卻被新來的女旦唱得行云流水。聽者驟然發現了這青衣的不同凡響。沒過多久,便有見過世面的票友辨認出,原來就是名震一時的名伶言秋凰。
襄城原本不大。這事便很快在票友間傳開了。關于這一層,對于言秋凰與父親的相識,仁楨有許多的想象。直至長大以后,她仍然覺得,這想象的諸多版本,并未有一個是真正可說服自己的。
她每每想起十歲的自己,當初與父親踐約去聽言秋凰的大戲,實際便是這想象的開始。
那是她第一次踏進重新整修后的“容聲”大舞臺。在襄城的地界上,出現這么一處地方,多少堂皇得有些不真實。門里懸著半人高的燈籠,一字排下來,上書“玉樓天半笙歌起,蓬島閑班笑語和”。迎臉兒的花崗巖影壁,鑲滿了各色臉譜,生旦凈末丑,一應俱全。并不撩亂,仿若色系。因間中自有秩序,便頓然氣勢非凡起來。進了去,才是別有洞天。橢圓形的舞臺已擴建到了數十尺。臺前蒙了重重的疊帳,紫天鵝絨制,光影在燈底下熠熠地波動。座位排了二百來個。前排照老例兒自然是花梨酸枝的太師椅、八仙桌。卻依墻又擺了幾只鑲了軟墊的貴妃短榻,布局一時之間中西合璧起來。仁楨看著新鮮,并不知道,這是為城中幾位軍界要人的姨太太特設的,只嚷著要去坐。父親明煥沒理會她,嘴里輕聲說,這角兒還沒幾個,倒先把京城里的派頭學來了。
說著便牽了她的手,上樓去。巴羅克式的轉角樓梯,通往樓上的包廂。這包廂是幾個有名姓的大戶留下的。多是為攜了家眷,免得拋頭露面,圖個清凈。馮家是長期包了一個。可是這一日,偌大的地方,卻只有他們父女倆。仁楨便站到了椅子上,手扶著欄桿往下面張望。看著底下人頭攢動。見過的沒見過的人,來來往往,作揖打招呼,寒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倒也十分熱鬧。她正看得真切,明煥卻將她抱下來,說,小心栽了跟頭下去。你不是孫猴兒,到時爹可沒有筋斗云來救你。
說著鼓點便響起來。開場的是一出武戲《挑滑車》。角兒剛上來,亮了一個相,便跟著有喝彩的聲音。這折戲用來熱場,是極好的。說的雖是個魯莽的英雄,倒也十分的有作為,觀眾便會投入。扮高寵的葉惠荃,據說是“金陵大武生”趙世鱗的弟子。趙雖是長靠優于短打,行家云其拙于翻撲。但仍有許多看家功夫,像是大靠夾鞭,飛腳三越,都是旁人不會的。一一傳給了這弟子,便十分的有看頭。而這葉惠荃因為后生,英武逼人,眉宇間又有些富貴氣。肩上四支藍色令旗,上下翻飛。倒真將個少年氣盛的王爺將軍演得很像一回事。仁楨對這一折戲并不陌生。小時候聽父親講《說岳全傳》,內容是熟透了的。說起來,她總是對這高寵有些同情,怪岳武穆不近人情。將個少年人逼急了,終于有些頭腦發熱。可又真是有本事的,替岳飛解了圍,卻不得善終。為了打外面的人,死自己人是可以。可這樣死,終究是有些無謂。所以,仁楨看這出就十分入戲,每次高寵一得意,仰天而大笑,她便心里捏一把汗。想著他離死期不遠了。當挑了第十二輛滑車,見他直挺挺地倒下。仁楨就如釋重負,然后又惆悵得很。她再惆悵,底下叫好的聲音不絕于耳。那角兒經不住央求,又活生生地出來謝了一個幕。這下倒真顯出了她自己的傻來。
可終究是分了神,為了這個死而復生的英雄,下面就有些看不下去。不知為什么,演到中央,插了一折崑曲《風箏誤》。明煥嘆了口氣,說,“花”“雅”合流,也真是沒有規矩。崑曲的唱腔持重靡綺,對一個小孩子來說,便是有些悶。所以,當一個面相很老的小生在臺上咿咿呀呀,仁楨險些坐在椅子上瞌睡起來。但好在他身邊還有個書僮,倒是很活潑可喜。只看著他手執著一只風箏,在那里長篇累牘地對書生講著大道理。可是仁楨聽不懂他在說什么,精神終于渙散了下去。
就在這時,她看見對面的包廂里,坐著幾個人。因為光線昏暗,衣著形容,并看不清晰。大約是很有些排場,只見得一團錦簇。錦簇中卻坐了一個少年。這少年筆直地坐著,凝神屏氣,是個端穆的表情。他身旁的女眷,交頭接耳。他卻似乎不為所動。只是遠遠地望著舞臺。眼神也是靜止的,雖然和泰,卻看不出喜樂。倏然間,他轉動了一下頸子,解開了藍綢夾襖上的一粒扣子。旁邊便有個仆從躬下身,和他說了一句話。他便抬起手,只輕輕擺了一擺。再靜下來,仍然是個端坐的姿態。仁楨便有了一些興趣,覺得這人的做派,像是這戲外的另一出戲。雖然眉宇已很見了成人的輪廓,可以俊朗來形容。那微微垂掛的嘴角,分明還是稚嫩的。這分老成與克制,便有一些可笑。
接下來的一折《三岔口》,本是仁楨十分愛的。加之扮了任堂惠的小云昌,在當地也算是一個角兒,臺下便很起了一些反應。明明是大亮的一片,戲中的兩個人卻要裝著在烏漆抹黑間,不明就里,摸摸索索地打斗。卻是摸也摸不到,碰也碰不得。每看這一出,仁楨就在
心里惡作劇,盼著兩個人,不由己地撞到一處去。只是今天有些分心。打到最緊張的時候,劉利華一個鷂子翻身,穩穩落在地上。她便又向對面望過去。少年人神情凝滯,眼里依然沒什么內容。仁楨便想,真是一個木頭人。這樣想著,就打了一個很大的呵欠。
任堂惠與劉利華還未和解,仁楨卻聽到些騷動的聲音。忽然卻又靜下來。她引了引脖子,朝底下看過去。什么也沒瞧見。人們卻一水兒地往后場望。再接著,望的人都陸續低了頭。她就看見,是一隊荷槍實彈的兵士走了進來。打頭的是個日本軍官,個頭兒不高,只看得見清瘦的背影。走路垮著一邊的肩膀,也并不挺拔。他信步走到臺前,臺上臺下,一時之間,都停止了動作,鴉雀無聲。舞臺的馬老板趕了來,給這軍官鞠了一躬,表情很是惶恐,只連連說:少佐駕臨,有失遠迎。
軍官站定,行了一個軍禮,仁楨卻并未聽到皮靴上馬刺撞擊的聲音。只見他將手慢慢放下來,說道,客氣話就不用說了。上次在天津,未聽上梅博士,深以為憾。今天言小姐的演出,是不得不來捧場了。
他的中國話十分地道,北方腔兒,帶著些喉音。雖然字間仍有生硬,暴露出了他是個異族人。仁楨只覺得這聲音耳熟。正恍惚,待他側過臉,便立時間認出來,是幾次三番到家里來的和田少佐。甚至有次她放學回來,竟和他打上了一個照面。這少佐的臉相,和她想象中
的日本軍人,并不十分相符。青白臉色,眉目疏淡,卻長了茂盛的鬈發。那回他看見她,從口袋里掏出幾塊糖,放在手心里,沖她笑一笑。這些花花綠綠的東洋糖塊,讓仁楨遲疑了一下。但是,慧容走過來,牽著她的手,把她帶進房間去了。
這時候,和田少佐將身上的斗篷緩緩解下來。里面并不是軍裝,卻是一襲青布的長衫。在他摘掉了軍帽的一剎那,簡直像變戲法一般,迅速蛻變成了一個普通的中國男人。
他沖馬老板一拱手,馬老板立即會意。并不等有什么交代。坐在前排的幾位當地的所謂貴人紛紛站起身來,虛弱地笑一笑。被伙計引到后面一排坐去了。和田與他的部下,便要落座。貴妃榻自然也空了出來。女眷們看著男人們站起來,都有些緊張,亦步亦趨。然而有一
個很年輕的,是聯合準備銀行秦行長新娶的續弦。大約是平日里給寵慣了,有些不知厲害。別扭著,就是不愿意走。男人作勢不管她。眼見一個日本人走過來,她才慌亂著站起來。旗袍竟掛到了扶手,拉扯不開。那士兵嬉笑著,將手按在女人不慎露出的大腿上。女人驚叫了一下,躲開去。士兵正嘟嚕了一句什么。和田走過來,看了士兵一眼,一個耳光打在他臉上,十分響亮。士兵被打懵了,捂著臉。這一巴掌太突然,倒好像打了在場所有人的臉,熱辣辣的。
仁楨被這巴掌打得有些驚怕。他回頭看一眼自己的父親。明煥袖著手,低下頭也正看著她。她再抬起頭,卻看見對面的包廂里,那少年的臉色。他仍是端坐著,眉頭卻微微地蹙著,眼睛里有波動。
場上寂靜得怕人。和田卻走到馬老板跟前,短促有力地鞠了一躬,說,叨擾了。
他整了整長衫,慢慢坐下來。目光移向臺上。臺上的兩個演員,正不知所措。手與腳,都擺得很不是地方。
和田重又站起身,將戴好的手套又摘下。他沖著演員的方向,緩緩地拍起了巴掌。這掌聲,并沒有人應和,在空曠的大廳里,顯得格外的寂寥。
馬老板頭上滲出了一層密密的虛汗。他對著幕后的鑼鼓班子揚了揚手。半晌,先是稀稀落落的幾個鼓點,試探似的。然后,頻密起來。演員愣一愣神,跟著鼓點亮了一個相,接續上了情緒。臺上臺下,終于又熱鬧起來了。
和田滿意地坐下來。
仁楨一抬頭,看見對面的包廂,已空無一人。
一折《坐宮》。兩個演員做念是中規中矩。全然無精彩之處。到了鐵鏡公主的一段西皮流水,快得好像是要趕場子。不是楊延輝急著要出關去,倒像是公主要逐他走。楊四郎在快板又唱錯了詞,竟也沒有人計較喝倒彩。都知道,壓軸的言秋凰,就要出場了。
戲單上寫的是《宇宙鋒》,恰是“修本裝瘋”一折。仁楨暗地里歡喜。因為這一折戲,是她最愛的。正旦行里頭,她愛的并不多,卻獨喜歡這個趙艷容。依她一個小孩子的眼光。也看得出這青衣其實是美在了一個“苦”字。《五家坡》里王寶釧十八年的寒窯,苦得癡心。《望江亭》里的譚記兒先是孤寡,后情事輾轉,又苦得無謂。前前后后,竟沒一個人可自主命運的。獨這個趙艷容,攤上一個機關算盡的奸相做爹,已然不幸。后夫家又幾近滅門。她本也是悲戚的,但終究是給逼急了,到最后竟也破釜沉舟,裝瘋賣傻起來。要上天,要入地,哪里有一個女人可有此等氣魄,將一群男人,上到皇帝老倌,下至滿朝的文武,給耍得團團轉。然而仁楨終究是有些心疼她。她本也并沒什么主意,先是說什么“先嫁由父母,再嫁自己身”,這樣討價還價,到底是有些蒼白的。不知怎么的,仁楨就想起了二姐仁玨。二姐乳名“蠻蠻”,是個自由慣了的人。一嫁卻沒有嫁好。父母與她相互都有些無奈何,以后的事,就不知要到什么時候了。
開場鑼鼓響起,趙高踱著方步走出來。形態沉郁,倒是頗有氣勢。家丁念白:“二堂傳話,有請小姐出堂。”眾人屏息,望向臺側。啞奴速行立于臺中。只見言秋凰一身黑帔,蓮步輕移,慢慢進入視線。站定,垂首。待她抬起頭來,幽幽念道:杜鵑枝頭泣,血淚暗背啼。同時向臺下張了一眼,仁楨心下遽然一驚。她并未意識到,瞬間,這一眼會影響了她之后數十年的審美。她只是驚奇,一個女人的哀戚,竟可以在眼神流轉間,被表達得如此美麗,如此內容豐富。是哀而不傷,卻也是穆然成習。
大約這個亮相,也擊打了眾人。先是頓然沒有了聲音,突然有人回過神來,禁不住叫上一聲“好”。臺下便紛紛鼓起掌來。突然間,前排有人用日本話嚷了一句什么,然后也噼里啪啦地鼓起了掌。其他人聽了,倒噤住了聲,沒言語了。
接著的情節,是趙艷容哀求父親修書奏免匡家之罪。一段西皮原板。京胡繞梁,言秋凰便開了嗓,“老爹爹發恩德,將本修上……”聲音凝膩和婉。然而唱到了“上”字的尾音聲音卻突然間斷裂,劈了開來。幾近刺耳,令人猝不及防。這時候,仁楨看見言秋凰捂住了自己的喉頭,急促喘息,開始劇烈地咳。咳得掏心掏肺,身體都禁不住抖動起來。待她終于鎮定,便向臺下屈身行禮。向后臺匆匆走去了。
這一幕實在是出人意表。
半晌,馬老板才走上來,臉色緊張,一面賠不是,一面解釋說,言小姐積勞成弊,今日的得罪,馬某甘愿承擔。演出票款,全數退還。人們啞然,繼而竊竊私語。就有人冷笑,揭這馬老板的老底,說原是山東青州的一個戲霸。這次跑到襄城來混,到底水土不服,是敗走
麥城了。然后就有人開始起哄,亂嚷嚷,說要砸場子。
在這聲浪中,和田少佐緩緩地站起來,從部下腰間,抽出一把軍刀。并未多作猶豫,便走到臺上,眼睛也沒在馬老板的身上停留。他環視眾人,臉頰似乎抽動了一下,然后將軍刀高舉,狠狠地插在了舞臺中央。
在眾人瞠目中,軍刀還在孤獨地晃動。和田披上斗篷,施施然離開。馬老板要跟上去,卻被隨行的士兵狠狠擋在了胸口上,險些就是一個趔趄。
仁楨張著口。當她確信眼前的事情,已經停止。才回頭看了一眼自己的父親。她看到明煥,在昏暗中,點起了一支巴西雪茄。同時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笑意。臺下響起了更劇烈的聲音,令仁楨來不及消化父親的笑。甚至,來不及作任何驚異的反應。她只記得那雪茄的味
道,濃烈而辛辣,揮之不去。
然而,半個世紀后,她再想起這不合時宜的笑容。總覺得其中有些安慰的成份。這或許是一種本能。仁楨并不知曉,因為前一天風聞日本人的到場,言秋凰曾經計劃連夜離開襄城。父親阻止了她。同時將隨身的雪茄剝開,把粉末泡在一杯茶水里,讓她喝下去。
你會暫時變成一個啞巴,即使你自己想唱,也唱不出來。父親說。
也因為這笑容,仁楨打消了當夜去探訪言秋凰的念頭。是的,她寧可這么想,父親與這個女人之間,存在著某種盟約。這盟約中有一些不足外人道的內容。非關男女。甚至也包括她。
這樣想著,她心平氣和起來。將老花鏡取下來,折好。然后小心地將那張報紙輕輕地放進抽屜中。在這剎那,她看見報紙上的女人,微微揚起了嘴角,表情依然,是對她的一點討好。
(選自臺灣《短篇小說》總第6期,2013年4月1日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