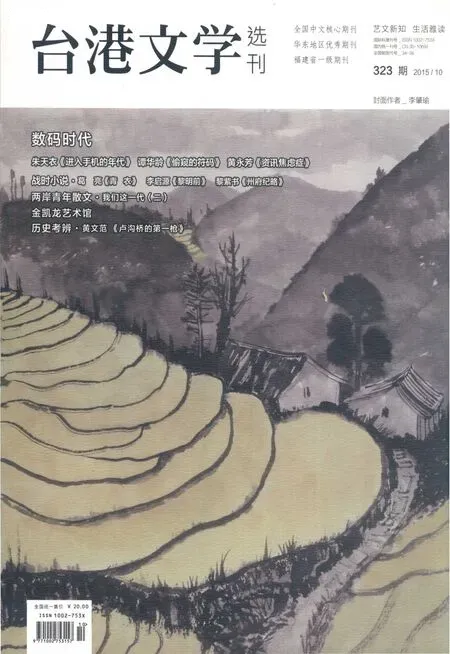黎明前



李啟源,筆名李渡予,1960年生于臺北。美國加州大學心理學博士。1996年初開始涉足導演,作品有《臺北異想》、《巧克力重擊》、《河豚》等。
他絕望地看著那位軍帽后面綴著幾塊土黃布的鬼子兵老練地解開小鐵門上的鎖,用靴子跩掉攔在入口處的東西,轉過一張獰笑的臉,示意要他跟進來。身后兩個衛兵推了推他。他們對待他沒有像先前審訊時那般粗暴,只是對他那張因驚嚇過度而扭擰的面孔有所嘲弄。
開鎖的士兵,手里頭鞭子呼呼飛舞著,一路踢進去。他聽見黑暗中有人痛苦地呻吟,空氣里的味道令人欲嘔。
他站在鐵欄外踟躕半晌,拼命想看個清楚,仿佛這樣會減少他的恐懼。里頭烏烏毿毿,不知有多少人擠在那里。“口好渴,賞點水喝成不成?”黑暗中有人近乎哀號地說。他聽見皮鞭的回答聲。一股惡臭沖鼻,他禁不住干嘔起來。
背后冷不防地被用力推一把,他踉蹌地摔了跟頭,肘根剛好壓在一副軟軟的肉軀上。“想死啊,找死啊,他奶奶的!”他不理會咒罵聲,徑把臉貼在鐵柵上,驚恐中軟弱無力地抗議道:“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讓他在牛柵睡了一宿……那時他渾身是傷,你根本不可能趕他走……”沒有用的,那些日本兵根本不管他在說什么,他眼睜睜看著他們把鐵門閂上。“我什么也不知道啊!”砰一聲巨響,門關了。手電筒的亮光隨皮靴聲愈來愈微弱。終于,他完全陷入一片絕望的黑暗之中。
不多時,在他的腳邊突然有個聲音說:“有煙嗎?”他本能地將腳縮回來,卻撞到另個人。“水、水、水,快!”隔壁凌人地敦促著他。
“沒有。”他頹喪地回答:“什么都沒有。”他仿佛看到四周含敵意的眼光正注視著他。“我是無辜的。”
“呸!誰不是?”有個聲音不屑地說。
他黯然垂下頭,渾身上下痛得要命。回想方才的審訊,仍心有余悸:皮鞭如驟雨般地掄打下來,皮破肉綻處,他猶可感覺到濕濕滑滑的液體,不消說那是他的血,嘴里盡是腥膻的味道。
一切都完了——再也沒任何希望,他想:遲早那些日本鬼子會發現他在扯謊。到了那時,他們更不會饒過他。也許他早該聽他婆子的話,不讓那個陌生人靠近他家門……他甚至可以用耙子驅走他。隔鄰雙喜家一定這么干,否則那年輕人不會多添腳程,將這趟麻煩往他家送。不過是個老實的莊稼漢哪,他懊喪極了,身上的傷痕,隱隱作痛。這下自己的模樣倒像了昨晚那個癩狗般的陌生人。
“先生,好痛啊,好痛啊……”房間不遠處傳來微弱的哀求聲。
“誰衣服干凈些?撕點兒過來。”同個方向有個低沉的聲音說。
沒有人搭理那個說話的人。“唉!就快不行了……”語氣沉著得近乎漠然。
他再次伸出腳,兩手撐著身子,小心翼翼地一吋一吋擠出點空隙,爬往聲音的來源。耳邊響起惡毒的詈罵聲,他裝作沒聽見。
“是你要布條嗎?”
“你有?”那人口氣有些驚訝。
“臟,但有。”
“可以啦。”說著,他即伸手幫他解衣服。
“……喂,輕點……”他痛苦地說。覺得那人手勁兒重得出奇,尤其接觸到他傷口的時候。
“那些個禽獸不如的東西!”那人一面動作一面哼了哼,好似這樣出氣,會使他好過些。
其實也無所謂解不解衣服,他身上披著的橫豎是早被鞭子抽爛了的破布條兒。舊痕新疤緊緊黏在上頭,那人每扯一下,就像撕掉他一塊皮。他開始有點后悔,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已經是泥菩薩過江之身,何苦再討這種罪受。他婆子平日罵他的一點沒錯,他實在
是個濫好人。
“忍著點,都是自己同胞。我看他撐不過今晚啦!替他換條繃帶,能夠讓他舒服些,就讓他舒服些吧!”
那人用著半勸半哄的口吻,好像當他是個任性的小孩似的。奇怪的是,那人聲音里頭有一種他所無法理解的,融合著撫慰與善解人意的力量。雖然他渾身痛楚,但在心底深處卻仿佛攫獲了那股力量,登時踏實了不少。
“這位兄弟大名是……?”那人問。
“叫我大柱子就成了。”
“大柱子。”那人喃喃復誦了一遍。
“你呢?”
“夏漢民。我是位傳教士。”
“傳教士?”
那人嚴肅地點點頭,多么遙遠而模糊的名詞。激不起他絲毫有意義的聯想。印象中依稀聽他婆子提過:長生鎮上來了個穿袍子的,常教人在那間黍楷和干打壘搭建的窩棚子里頭,愣坐著聽他講話,不時會在散場兒后發些面粉、大米什么的。婆子常慫恿他去瞧瞧究竟。可
是他硬不相信天底下會有這種事,什么活兒不干,凈坐著聽人講話就有東西可白領;他柱子窮歸窮,可沒淪落到要人可憐施舍的地步,所以他始終抗拒到那兒去。莫非眼前這個人就是那個穿什么袍子——“在長生鎮上周濟人家面粉的?”他怯生生地問。
“哈。”教士尷尬地苦笑一聲,沒有說什么。
大柱子聽見自己衣服被撕裂的聲音,在黑暗中出奇地刺耳。他一動不動地挨著墻坐著,視力已慢慢恢復過來。牢墻頂端剝落處,正有一線微弱的月光進來。不超過十呎見方的牢獄,擠滿了鬼影一般的人頭——軟癱的、焦愁的、失魂落魄的——一個個骨瘦如柴、赤身露背,
從他們身上散發出汗和糞尿混雜的味道。整個囚室看來就像一潭發臭的死水。
墻壁濕膩膩的,貼著他赤裸的背脊。大柱子僅容屈曲著腿坐著,他望著隔壁的傳教士正熟練地為枕在他膝蓋上那個血流不止的人包扎。這個發面粉的人實際年紀也許并不很大,但看起來卻十分蒼老:瘦骨嶙峋的身材,灰短的發,削細的頷顎,使兩丸眼睛突顯得分外炯炯晶亮。而靠著他腿的那個人卻是奄奄一息,剩下兩片嘴唇一張一翕,好像一尾垂死的魚。
有個靠近他們的人發出沙啞的嗓音說:“沒有用的,他拖不過明天。唉,我不知……”
“畢竟他還沒有死。”教士頭也不抬地說。
黑暗中傳來鼾聲,大柱子羨慕極了,即使在這樣臭氣薰天、蚊聲鼎沸的黑牢內,照樣有人好夢不驚:他會夢見他的妻兒嗎——在明亮干凈的青空下向他招手,汗流浹背的他接過他們遞上的茶水,喉嚨喀咯一陣后吐出來,唇齒間遂浮上一層暢意的茶香……
“喂,怎么個進來?”那個聲音沙啞的人再度開口。
大柱子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同時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好似這口氣他已忍了許久,再也忍不住了。
“去問老天爺吧!”他忿忿不平地說。
那位傳教士也抬起頭來,有人愿意聆聽他的苦難,他感激地看著他們兩個說道:“昨兒個村子里狗吠聲一夜不歇,約莫二更天,聽見外頭砰砰砰的急促敲門聲,開了門,發現像僵尸一樣挺一個掛了彩的小伙子站那兒,臉色泛鐵青,一副搖搖欲墜。恰時我家婆娘跟出來,一見這光景,又哭又嚷,硬是不讓他進門。老天,當初要是聽她的,也不會落到現在這個下場。”說著他有些頹喪,又像自嘲般,“好說歹說,拿兩張餅給他充饑總可以吧。”
“你會充英雄好漢!你不怕死!老娘這就帶幾個小渣巴出去,你愛讓他睡哪就睡哪,愛給他什么給什么……”
“住嘴!想把日本鬼子喚來了不成?到灶間拿兩張餅來,我打發他上路。”
餅拿來了:只有一張。陌生人仍感激地收過。他掉頭便走,他忙跟上去。
“你跟出去干啥?”他婆子狐疑地問。
“萬一人沒走,賴在前場的黍楷堆上睡覺怎辦?盯著他走遠哇!你門閂上,屋里待著,等我叫了門再應。”
待門一關上,他馬上拉住小伙子的胳膊,往牛棚方向走。穿過曬谷場,順手就在衣竿上撂一件單衣下來。
“地方不好,勉強湊合一夜,餅吃了會好過些。”他盡量壓低聲音說。
“謝謝大叔,我……”
“好啦,刀兵兇年的,我也甭問你是誰,打哪兒來的。我家那口子怕你惹麻煩,莫要怪她,換了別人也一樣。日本鬼子的狠勁兒,你我心里頭都有數,否則今天你也不會落到這田地。我要是聰明人,應該把你攆走。把衣服換了吧。”
他把陌生人血漬斑斑的衣衫,塞進那堆黍楷兒中,并用雙手撥撥弄弄,直到它看不出一絲痕跡。“你休息,我得走了,免得我家婆娘起疑。”
“我一夜睡不安穩,天剛蒙蒙亮,看著他離開才下田做活兒。”
人門的傾聽,使他心寬不少。
“沒想到——沒多久,日本鬼子突然包圍村子大搜索,從清晨到傍晚,每一吋地方都翻遍了。到了日落時分,那件烏不溜嘰的衣服終于被他們搜出來了……”
“挨鞭子啰?”一個聲音岔進來。
“更糟!逼供時我謊稱那人往玄明山方向逃。到時他們找不到人,更以為我大柱子存心掩護要犯。天曉得,我連他姓啥叫啥都不知道哩!”
“萬一他要真往玄明山逃呢?”
“不可能的。”大柱子斬釘截鐵地說:“他渡河往永寧堡去了——是我用舢舨渡他過去的。”
忽然周圍都安靜下來,一片死寂,宛如他說了什么可怕的事。他只能清楚聽見自個兒咽口水的聲音。莫非又干了什么傻事不成。好不容易與其他人聯系起來的線,啪,又斷了。他覺得自己像給孤伶伶地遺棄在一個荒涼的世界上。
“我敢賭咒我壓根兒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日本鬼子為什么要捉他?”
“牧師,他們會槍斃他嗎?”角落一個滿臉胡碴的人問。
牧師?他們管那給人面粉的人叫牧師?又是一個他從沒聽過的字眼兒。他能夠預卜他的命運嗎?最重要的,他能告訴他自己究竟造了什么孽?善有善報,為什么他得到的卻是這種下場?
“牧、師——”他舌頭有些別扭,“鬼子會槍斃我嗎?”
傳教士緩緩轉過頭來,滿臉的憂戚,卻仍力圖鎮定,他遲疑了一會兒說:“凡人到頭來終歸難免一死。”
是的,每個人最后都難逃一死!這話是對的——不是老死,就是病死。但為什么在這時刻選擇他?大柱子腦中閃過一連串的念頭:貧窮、瘟疫,數不清的屈辱,都沒使他倒下過,現在,只有一粒冰冷的槍子兒,什么都完了——他的一生。人的命運到底是怎么回事?時空
遞嬗過程中某個偶合的交點,他伸手援救一個素昧平生、無助無告的人。其至連援救都談不上,他只是給那陌生人一張餅、一件衣服,末了渡他過河那段,與其說存心想搭救他,倒不如說是緣于自己的恐懼:他不想讓婆子知道他留下這個危險人物在牛棚中過一夜。這點陌生
人也是明白的,河床上他說得清清楚楚:“別用那種感激的眼光看我,怪不自在的。不是特別厚待你,今兒個要不是你,換上別人,我也會這么做。懂吧?小伙子!渡你這一趟,是怕你留下被鬼子發現,咱們一塊兒遭殃,明白吧?我害怕,從小我就不是一個勇敢的人,如今更怕連累到我的家人。所以到了對岸,我不認識你,你也不欠我人情。”
沒有話說,黑夜像堵墻一樣圍著他們,密不透風。“我只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漢啊……”剩下他一個人在墻內喁喁抗辯著。
如果在日本人查獲那件血衫時,坦白向他們吐露陌生人的行蹤,或甚至在當晚就驅走他,現在又會是一番什么樣的景象?他正在家里做什么?大柱子胡亂地想著。但也許鬼子們會捉到那個人——他們不會笨到輕信一個莊稼漢的話——可能現在就在永寧堡逮住他了。他突然涌起強烈的渴望,好像已經親眼看見一般;但這念頭同時也給他帶來不安和譴責,但愿能擺脫這種齷齪的想法,但是它猶如沸騰起來的鍋水,再無法抑遏了:齷齪也是一種希望。他還有一線生機,他不是陌生人的黨羽,那個人可以證實他的清白,如果他們現在已經捉住他的話。
“這位老哥,”他滿懷希望對著那位喉嚨沙啞的人說:“你是怎么關進來的?”
那人像進來有些時日了,他似乎對這里的惡臭、擁擠和痛苦適應得很好。大柱子由衷期待他的情況和他一樣,這一來,他只是罪犯中的一個罪犯,不至于特別突出;至少,他不會完全的孤單。
只是那人只瞪了他一眼,卻緘默著。
“他不像你那么勇敢!”滿臉胡碴的人搶口道,帶著鄙夷:“他只是個投降的孬種,這里面有三個人因為他而被關進這鬼地方來,包括牧師腿上那位快死的春生。他奶奶的!敗得窩囊!老子寧愿戰死在外頭。”
大柱子闔上眼睛,內心有種奇異的感覺:介于哭與笑之間的矛盾感覺,超過他所能夠處理的限度。他覺得渾身乏力,精疲力竭。耳邊剩下蚊子嗡嗡作響,單調的聲音,似近而遠。黑暗的時間無止盡向前延伸,不久他便進入夢鄉。
他夢見那位陌生人就躺在他身邊,混在一堆囚犯之中。“他們逮捕你了嗎?”他有一種解脫的快感。“我已經盡力了,只能怪你自己運氣不好。”說著,他站了起來,看見柵欄外的老婆和幾個小孩期待的眼神,他興奮地張開臂膀想擁抱他們,卻被門口的兩位士兵攔住。“人在哪里?”他們兇狠地問。“指出來!”他環顧牢內:傳教士、教士懷中瀕死的人、降敵者、戰士……許多張慘黃枯槁的臉孔。他哭泣了。“為什么要叫我做這種不義的事……”“指出來!指出來!”他們更大聲地吼叫。他醒了過來,一身的冷汗。
傳教士腿上那個傷兵,依然在呼痛,只是聲音更微弱了。
他不再閉目睡覺:他在盤算和上天進行一場交易,就像拿大麥、高粱換騾。這一次,倘若真能脫離這個地方——不管日本鬼子以什么方式捕到他們所要的人——他都決心將所有的謙卑、虔誠、信仰,包括個人的激情,完全奉獻給他記憶中的每一位“神祇”:玉皇大帝、
觀音菩薩、城隍爺……他會盡力去學習做個熱愛這充斥暴力與殺戮世界的“圣人”。只要他能離開這湫窄可憎的環境……
喀、喀、喀……皮靴聲愈來愈清晰,光芒也愈來愈刺眼,他心頭跟著一亮。抬頭看見士兵正在解開牢房的大鎖。大柱子一顆心幾乎鼓出來,胃里頭翻攪著不安和忻悅的空氣。“喂!你!”強烈的白光使他雙眼感到一陣暈眩。
“還有你!”他們指著傳教士。
士兵們粗魯地拿著槍將他們兩個押到一間小室中。
“報告!人犯帶到了!”士兵們持槍敬禮后,退到角落去。
小室當中站著一位英挺的軍官,皮鞭在他手掌心中輕拍著,他不懷好意地往眼前這個驚惶失措的小人物身上打量:他沒有一點“英雄”的氣質,甚至連站在那兒腿都會顫抖。扁平干黃的臉,眼屎尚無恥地搭黏在那對細小如耗子的眼眶上——與他心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完全
不符。這樣的一個人,一個低劣的賤民,竟會有英勇的行為么?他感到疑惑,這些中國人,他永遠難以理解,既頑強又可恨……
兜臉就是一拳,大柱子搖搖晃晃地朝后仰倒,鼻孔一濕,一片血腥。這一拳不僅打得他眼冒金星,也把他所有的希望擊個粉碎。
咆哮,嘶叫,各種怪聲,從那位剃光了頭的軍官,嘴里煙黃的獠牙間迸出。大柱子被踩在皮靴底下,痛苦地搖頭,他一句也聽不懂軍官在說些什么。
“告訴他!告訴他!”軍官漲紅了臉對教士說,“他竟敢欺騙日本皇軍!”
“他不會明白你所說的欺騙是什么意思。”教士說:“他根本不認識你們要抓的那個人。”
“今天早上我們在他家搜到血衣。也有人證實昨晚聽到他們家不尋常的交談聲。”軍官冷冷地說,一只靴子仍踩在柱子的胸口上。
“陌生人半夜敲門求助,他讓他住了一晚,不就是這么回事么?換上你,你也會這么做吧?人都有惻隱之心……”
“混賬!我不是請你來講道的。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立場。我要你——翻譯,懂嗎?”軍官尖刻地說:“就像你每個安息日所做的,把上帝的話,翻譯給那些村夫愚婦聽一樣,我要你把我每句話、每個字都清清楚楚讓他明白,”他指著泥地上那張蠟黃、荒蕪的臉:“那是你的錯。”
“為什么找我?你們多的是懂翻譯的人。”
“不錯。但我們缺少一個能教人遠離死亡的人。看我腳底下這個人——”軍官皮靴更使勁地在不幸的軀體上磨蹭著,無情地瞧著他掙扎和哀號。“瞧,他的求生欲還是十分熾烈的。如果你不能拯救他的肉體,他的靈魂永遠不會托付給你的上帝。”
“夠了,夠了。”教士別過頭不愿再目睹慘劇。“你這個虛妄的人。”
“哈、哈、哈……”日本軍官洋洋得意地笑。
他把皮靴放下,示意他的部下把地上的人拎起來。“現在,可以正式開始啦。”他驕矜地宣布道。
“他和那個特務到底是什么關系?”
教士把他的話翻譯給大柱子聽。
“什么關系?——天啊!會有什么關系呢?我和他非親非故的,會有什么關系呢?”他惶惑地說,“牧師啊,他們該不會以為我是他同道的吧?我哪曉得他是什么特務不特務的,與我這個不識半個斗大字的莊稼漢有什么關系呢?他餓,他累,我給他吃,叫他休息,我只當他是個普通的人,就是這樣。牧師,求求你告訴他們吧。”眼睛偷偷地瞟了一下,他已經預感了某種不幸,心不由得在胸口突突撞擊著。這么一件單純不過的小事——人與人之間純粹的濟溺行為,為什么他們會不明白?
“你把他形容成情操高尚的人。”軍官輕蔑地說。
“不。”牧師搖搖頭:“是你們殘酷的迫害和壓榨教育了他。”
“問他人到底往哪個方向逃逸。”軍官厲聲命令道。
“大柱子,他問你人逃到哪個地方?不要管我事先知不知道這回事。”牧師急切地說,“你怎么說,我怎么告訴他,你自己決定……”他突然張口結舌,想說句適切的話,卻想不起來。他應該鼓勵他繼續隱瞞實情嗎?——即使因而丟掉性命?為什么這個無辜的人“應該”這么做:為了良心,道德?……還是僅僅為了滿足他個人宗教上的虛榮心?在從前的日子,他一定毫不遲疑勉人走向正義,但在這時刻,真正生死攸關的節骨眼兒,他卻力不從心,想到的字眼不是陳腔便是濫調——他對“人”從未有過如此的陌生。
“玄明山!”他可沒有聽錯,從這個受盡壓迫和屈辱的人的軀體,真誠發出來的聲音。他首次為一具粗糙但堅貞的靈魂,深深感動著。
“玄明山。他說玄明山。”
“哼,我早就知道。”仿佛證實了原先的揣測,軍士像只獵犬一樣瞪視著眼前這只不幸的獵物。“他如果不是支那政府的地下工作人員,絕不可能為一個不相干的人賣命。沒有人會這樣做的。別以為我們是好耍的,我已經得到那特務逃亡永寧堡的情報,等著瞧,我終會
抓到他的,至于他……”
“你明知道他只是個無辜的農民。”
“別指望我會相信你的鬼話。你這個窩藏扒手、強盜,聲名狼藉的神棍,你不配替他求情。”軍官蠻橫地說。
“你們打算怎么對付他?”
“槍決!”
“罪名,罪名是什么?”教士激動地喊著。
“牧師啊,他們會殺我嗎?”那是大柱子陰沉的哀聲。
軍官一鞭子揮到他身上去。
“嗯,這倒是個有趣的問題,牧師。”東洋軍官懷著惡意的戲謔看著教士:“什么罪名,能使這賤人變成英勇的烈士——私通重慶的抗日分子?哈哈,黎明時分我會派人沿街敲鑼,叫村人們來刑場‘觀禮,看他們的烈士在面對著子彈時,會擺出怎樣怪異的姿態。”
“黎明時槍決的人為什么不是我?我在你心目中前科累累,窩藏過流氓、扒手、強盜,更嚴重的,我相信你不會不曉得,在你們抓那諜報員最緊要的時候,我曾讓他在我那兒藏匿了三天。”
“你想怎樣?”軍官聲音里帶著憤怒。
“我只要求正義。”
他那剃得青亮的頭顱閃著汗珠,嘴巴張開半晌,露出兩顆黃色的獠牙:“不要太有自信。我不怕多槍斃一個人。”
“這是一場不仁的戰爭,你一樣會有恐懼,”教士毫不留情地說:“你不敢殺我,你還是害怕遭——天譴!”
“把他們統統帶走!”軍官氣急敗壞地咆哮著。
“嗨!”他的部下馬上一擁而上,架著兩個人離開。
傳教士在士兵的簇擁下仍掙扎地回頭大聲說:“你還未在人性中成熟……”一把槍托迅速擊在他的小腹上。
空蕩蕩的小室中只留下軍官一個人。他驀然轉首,眼光恰好停在墻壁懸掛的一幅中國版圖上,地圖上標示的河流、城市、山脈、鐵道,似乎隨處都隱藏著他的野心、欲望、權力、殺機……不知經過多久,也許若干年過去了,每當他回顧那段毀滅的日子(他毫不懷疑人具
有那種可怖的力量),他想起了那些背墻而立,在他一聲號令下,飲彈而亡的中國人,不禁有著羨慕:他們瞬間坦然的地走了,而他卻得背負著空虛的生命繼續下去。在他世界中,創造的只是冷酷、瀕死的經驗。最難堪的,他耳邊總是無休無止地響起那位灰發教士的話語:“你還未在人性中成熟。”
黑夜重又籠罩在他們四周,這個逼逼發臭的環境,猶如外邊的世界,充斥著過量的憂傷與苦悶。而他不再夢想逃脫,生活的煎熬,使他不輕易信賴奇跡。
“牧師,什么時候……?”再沒有比無精打采的聲音更令人覺得悲哀了。
“天亮后。”牧師覺得自己回答得像位劊子手。“也許不會那么快……”
倚在身上那位瀕死的人,這時忽然發出囈語:“是你嗎,娘?”
“他娘來接他回極樂世界啰。”那副沙啞的嗓音說。“他就要得到真正的解脫了。這些個日子來,我一直在想怎樣才得有真正的寧靜與平安,那也是當初引誘我投降鬼子的渴望……”
“呸!不要臉的東西!”一個粗糙而倔強的聲音說。
“我敢指天發誓,我并不全為自個兒打算。當時春生傷成那副德性能再打嗎?”
“別為自己開罪啦,沒有人會原諒你!你的大罪就是——怕死!怕死!怕死!”滿腮胡碴的人吼道。
那人微紅的眼睛初露慍意,但不久又消失了,取代的是一個殘破迷茫哂笑——他沒有權利生氣。
“啊……我也駭怕……”大柱子的頭垂落兩膝之間,充滿絕望的聲音。
“每個人都害怕死亡,我也不例外。”教上肅穆地說,“但茍活著未必比死更來得容易和愉快。我們最大的難題是死得既能榮耀自己,又能榮耀他人。”
“你是個有學問的人,告訴我究竟是犯了什么冤孽,得到這種報應?”
“不,大柱子,這不是報應,你的磨難來自于慈悲。我深信你選擇的是一種榮耀的死。我知道這些話不能改變什么,但我還是想告訴你我衷心信仰的一句話,記住它你會好過些——‘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我的老婆和孩子?”
教士堅定地說:“出去后,我會盡力照顧他們。”
“這位兄弟,只要我活著一口氣在,沒有人敢欺負他們的!”大胡子說。
“一切拜托了。”
他是在交代遺言么?他想起小時候阿爺臨終前的情景:高高的床榻像一座困頓的神龕,家人們的臉都朝向躺在上頭的人,忍受著從被褥間擴散出來的發爛的內臟氣味。那夜大廳的燈燭點得特別亮,好像那一張他們從沒在意過的臉,今夜要獲得補償似的。阿爺忽然露出了
平日難得見的笑容,娘見了馬上捂著臉哭泣,接著每個人都學她的樣將臉捂住,不知是因為傷心,還是忍受不了那種腐敗的味道。世間上沒有像死亡這般丑惡的東西。而現在就要輪到他了。
“我……快撐不住了……”那位垂死的人呼吸沉重,發抖呻吟著,把牧師的祈禱打斷了。“你可以撐下去的。”“為什么……”低悶的聲音使人聽不清楚他的話語。
“他就快死了嗎?”大柱子語氣中帶著一股淡淡的平靜。
“嗯,上帝自有他的打算。”
“我也沒有多少時間了……啊,很奇怪,我怎會突然想起家鄉的一首小調,我已經好幾年不曾開口唱過歌了。”接著他輕輕地哼了起來;歌搖像只手,把箱子合上,一切不愉快的記憶鎖在里頭:
郎邪個撐船波水喲
千里迢迢嚒望鄉間
想起妹來個淚汪汪
桃李花開喲我還鄉
桃李花開喲我還鄉
……
……
黑暗永遠是一樣的,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而現在又是那么地不可靠。有時他幻想黎明永遠不會到來,夜將恒常地持續下去;有時卻又想象著一秒鐘曙色就會偷偷溜進來而心悸不已。
周圍的人,靜寂無聲,在一片愁云慘霧中,逐漸地睡去了。
“你困了嗎,牧師?害你跟著我受累一番。”
“哦,不。”教士說,“像這樣的一夜,孤單一人不好……”
但他終究還是禁不住打起盹來。大柱子輕輕把那傷患從教士身上移到自己肩頭來。“呵——”教士無意識地伸了伸腿,仿佛卸下一副重擔,輕松許多。他轉了一個身又沉沉地睡去。
現在整個世界都遺棄了他,伴著他的只剩下自己的呼吸聲,但連這點可憐的生命也不停地離開。頹然倚在他肩頭的那位垂死的人,已幾乎感覺不出喘息聲了。也許死亡就像這么回事吧:你放棄了一切,也被一切所放棄。大柱子沒有注意到,暗夜中尚有一對不眠的眼睛,
正渴慕地注視著他。
傷患喃喃動著嘴唇,大柱子試圖和他講話,因為他再也忍受不了陰森的沉默。“你看過人被槍斃的樣子?”“……好亮的光……”“會痛苦很久?”“一下……舒服了……”他直覺伸手摸摸那人的鼻息:沒錯,他斷氣了。
死亡原是這么件輕而易舉的事。大柱子把死者輕若羽毛的頭輕輕枕回土地上去。
“過去了?”那張背負著罪疚的符咒和疲累的臉,張開嘴巴說:“他運氣,撒手便一了百了,而我呢?不論到哪里,不論做什么,再沒有人會當我正經地看。打從被鬼子俘虜……不,用不著再撒謊兒了,我廖圣怕死向鬼子討饒的。這些天來看到春生呻吟、痛苦的模樣,就恨不得自己死去。我真是個無可救藥的人,沒有用的窩囊廢。瞧他們看我那種眼光……我簡直就不像個人。“說著,淚水淌滿他的臉龐。”大柱子,不要轉頭過去,聽我說……“那人緊張地握住他的手。”你就要成為——英雄了,我羨慕你!“
他清楚見到眼前這顆脆弱的心,受苦的臉。驀地,他發現不只可以看見這一張臉,另外一張臉孔,一張,又一張:黎明終于來臨了。他是唯一清楚的人。本想搖醒牧師,但又何必呢?他開始正式向這世界告別,獨自迎向那條漫漫的,無人可取代的,光榮之路。
(選自臺灣希代書版有限公司《新世代小說大系·歷史/戰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