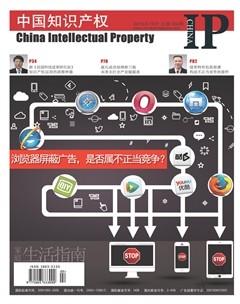客觀技術問題與發明人聲稱技術效果的關系
石必勝

在專利創造性判斷的司法實踐中,對于客觀技術問題的認定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客觀技術問題與發明人聲稱的技術效果的關系是什么?這里面又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客觀技術問題是否必須依據發明人聲稱的技術效果進行認定;第二,客觀技術問題是否可以依據說明書沒有記載的技術效果進行認定;第三,客觀技術問題是否可以依據本領域技術人員顯而易見的技術效果進行認定。本文擬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以期能夠為統一認識打下基礎。
一、客觀技術問題是否必須依據發明人聲稱的技術效果進行認定
在確定客觀技術問題時,技術效果具有重要影響。《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1.1節規定,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是指為獲得更好的技術效果而需對最接近的現有技術進行改進的技術任務。雖然技術問題不完全等于技術效果,但是,技術效果是引導發明人確定技術任務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專利創造性判斷過程中,技術效果對確定客觀技術問題有重要影響,技術效果可以作為確定客觀技術問題的基礎。關于技術問題與技術效果的關系,我國《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1.1節規定,發明的任何技術效果都可以作為重新確定技術問題的基礎,只要本領域的技術人員從該申請說明書中所記載的內容能夠得知該技術效果即可。
既然技術效果是確定客觀技術問題的基礎,那么在確定客觀技術問題時只能依據發明人主觀認為的技術效果來進行認定,還是應當依照一個更加客觀的標準來確定呢。我國《專利審查指南》規定客觀技術問題應當客觀地認定,并不能完全受到發明人聲稱技術效果的限制。《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1.1節規定,基于最接近的現有技術重新確定的該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可能不同于說明書中所描述的技術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根據審查員所認定的最接近的現有技術重新確定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
為什么客觀技術問題的認定不受到發明人聲稱技術效果的限制呢,這是因為,專利審查員所認定的最接近的現有技術可能不同于發明人在說明書中所描述的現有技術,現有技術不同,發明的起點就不相同,發明相對于最接近現有技術需要進行改進的技術任務也可能發生變化。正如歐洲專利局所述,確定客觀技術問題的目的是為了客觀地判斷創造性。在T0641/00COMVIK案中,歐洲專利局對“問題—解答”方法進行了以下說明:“為了客觀地判斷創造性,問題—解答方法中的問題應當是一個技術問題,它應當實際被權利要求中的解答所解決,權利要求中的所有技術特征都應當用于解答。問題應當是在優先權日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提出來要求解決的……如果在專利申請中不能提取出技術問題來,則歐洲專利條約第52條中規定的具有專利性的發明就不存在。”我國現有判例也強調,由于專利權人在說明書中描述的現有技術可能并非專利復審委員會認定的最接近現有技術,因此,基于專利復審委員會認定的最接近現有技術重新確定的該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可能不同于專利權人認為的技術問題。
我國《專利審查指南》關于客觀技術問題的規定,實際上參照了歐洲專利局的相關規定。歐洲專利局在T0024/81案中認為,如果新發現的現有技術比發明申請中原始記載的最接近現有技術更接近發明申請,則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可能需要重新陳述說明書中表述的技術問題。最后,發明申請相對于新發現的最接近現有技術所具有的技術效果應當被用以確定新的客觀技術問題。
我國《專利審查指南》的上述規定得到了人民法院的確認。例如,在(2010)高行終字第311號“電動自行車輪轂”的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專利權人上訴主張,“行星軸固定在離合器上、離合器固定在主軸上,省略了行星架,解決了簡化離合器結構、減輕構件重量的技術問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則認為:“由于專利權人在說明書中描述的現有技術可能并非專利復審委員會認定的最接近現有技術,因此,基于專利復審委員會認定的最接近現有技術重新確定的該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可能不同于專利權人認為的技術問題。本專利權利要求1相對于附件2的技術方案多了離合器這個部件,而增加離合器能夠解決現有技術中輪轂外殼的轉動通過行星齒輪機構傳遞給電機轉子,引起電機不必要的轉動的技術問題,因此該技術問題是本專利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
客觀地認定技術問題是各國專利審查和審判實踐中的普遍做法。美國在司法實踐中也提出在確定技術問題時注意客觀性,有的情況下不一定要與發明申請人或專利權人聲稱的技術問題相同。在KSR案(KSR. 82 USPQ2d at 1397.)中,最高法院特別地指出了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在四個方面存在錯誤,其中第一項就是認為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和專利審查員只是局限于考慮專利權人意圖解決的技術問題。美國《審查指南》(MPEP § 2144.)規定,對比文件中記載的改進現有技術的動機往往就是發明人進行改進的原因,但有時發明人卻是為了不同于創造性判斷者的目的或解決不同的技術問題而進行相同的改進。只要取得相同技術進步或者效果,發明人改進的原因與創造性判斷者認為的原因不相同并不影響顯而易見的判斷。是否有技術啟示,應當根據發明人面臨的普遍問題來確定,而不是由發明具體解決的問題決定(In re Kahn, 441 F.3d 977, 987, 78 USPQ2d 1329, 1336 (Fed. Cir. 2006))。本領域技術人員并不需要認識到記載在現有技術中的相同技術問題以進行改進(In re Linter, 458 F.2d 1013, 173 USPQ 560 (CCPA 1972); In re Dillon, 919 F.2d 688, 16 USPQ2d 1897 (Fed. Cir. 1990), cert. denied, 500 U.S. 904 (1991).)。
二、客觀技術問題是否可以依據說明書沒有記載的技術效果進行認定
按照專利法的一般原理,如果不是本領域技術人員在本專利說明書和現有技術基礎上能夠知曉的技術內容,發明人應當在說明書中充分公開,否則,這樣的技術內容就不能作為認定專利有效的依據。從公開技術貢獻從而換取保護的角度來說,發明人在申請日之前沒有發現并記載在專利申請文件中的技術效果,不能視為發明人的技術貢獻,因此不能作為確定客觀技術問題的依據。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行提字第8號“抗β-內酰胺酶抗菌素復合物”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所強調的那樣,專利申請人在其申請專利時提交的專利說明書中公開的技術內容,是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審理專利的基礎,亦是社會公眾了解、傳播和利用專利技術的基礎。因此,專利申請人未能在專利說明書中公開的技術方案、技術效果等,一般不得作為評價專利權是否符合法定授權確權標準的依據,否則會與專利法規定的先申請原則相抵觸,背離專利權以公開換保護的本質屬性。
司法實踐中的很多案例都在有關客觀技術問題的爭議中強調了上述原則。在筆者審理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高行終字第285號“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鈉氯化鎂凍干粉針劑及其生產方法”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專利權人認為本專利要解決的客觀技術問題是:“現有技術采用活性分裝,使用時現場配比,而本專利采用單一制劑,其活性組分在工廠生產中完成嚴格配比,有效克服了現場配比所帶來的配比波動性。”本專利說明書記載有將三磷酸腺苷二鈉和氯化鎂制成凍干粉針劑,提高了藥品的穩定性,據此專利復審委員會認定權利要求1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在于以冷凍干燥的方法提高藥品的穩定性。二審法院認為:“本專利說明書所描述的背景技術內容與證據1的技術內容是相同的,因此本專利要解決的技術問題不包括避免配比波動性,且本專利說明書也未記載其他可以使本領域技術人員從中能夠得知本專利具有避免配比波動性的技術效果的內容,因此原審判決認定權利要求1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不包括避免配比波動性亦無不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行提字第8號“抗β-內酰胺酶抗菌素復合物”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表示,本案中專利權人主張其為了解決本案專利的安全性、有效性、穩定性,還進行了長期毒性試驗、急性毒性試驗、一般藥理研究試驗等一系列試驗和研究,但由于相關技術內容并未記載于本案專利說明書中,不能體現出本案專利在安全性、有效性、穩定性等方面對現有技術作出了創新性的改進與貢獻。因此,這些試驗和研究不能作為認定本專利權利要求1的創造性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論述表明,說明書中沒有記載的技術效果,不是發明人實際作出技術貢獻的依據,因此不能作為確定客觀技術問題的基礎。
三、客觀技術問題是否可以依據本領域技術人員顯而易見的技術效果進行認定
前面的分析表明,由于不是發明人的技術貢獻,因此不能依據說明書沒有記載的技術效果認定客觀技術問題。但是,在最接近現有技術不同導致發明人聲稱的技術效果不能作為認定客觀技術問題的依據時,是否絕對不能依據說明書沒有記載的技術效果認定客觀技術問題呢?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非常有必要強調,專利創造性判斷的主體應當是申請日的本領域技術人員,應當從專利創造性判斷主體的角度來分析這種情形下如何確定客觀技術問題。首先,發明是否具備創造性,應當基于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的知識和能力進行評價。其次,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也可稱為本領域的技術人員,是指一種假設的“人”,假定他知曉申請日或者優先權日之前發明所屬技術領域所有的普通技術知識,能夠獲知該領域中所有的現有技術,并且具有應用該日期之前常規實驗手段的能力,但他不具有創造能力。再者,既然本領域技術人員并不具有創造能力,把對本領域技術人員顯而易見但說明書沒有記載的技術效果作為認定客觀技術問題的依據,就不會違反前面所述的技術貢獻原則。
前面的分析表明,即使說明書沒有記載,但只要技術效果對本領域的科技人員是顯而易見的,也可以作為認定客觀技術問題的依據。這樣既符合專利創造性判斷的主體標準,又不會違反說明書應當公開請求保護的技術貢獻的原則。我國《專利審查指南》的相關規定體現了上述思想。《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1.1節規定:“重新確定的技術問題可能要依據每項發明的具體情況而定。作為一個原則,發明的任何技術效果都可以作為重新確定技術問題的基礎,只要本領域的技術人員從該申請說明書中所記載的內容能夠得知該技術效果即可。”其中的重點在于“本領域的技術人員從該申請說明書中所記載的內容能夠得知該技術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行提字第13號“乳腺疾病藥物組合物及制備方法”發明專利無效案中認為:“專利權人主張本專利實際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是提高丹酚酸B的含量,并非改變劑型。然而,本專利權利要求書中并沒有記載藥物組合物中丹酚酸B的含量,也沒有記載用于提高丹酚酸B的具體技術手段,更沒有記載丹酚酸B的含量與療效之間的因果關系。本領域技術人員在閱讀說明書后,無法得知本發明要解決的技術問題與提高丹酚酸B的含量有何關聯,更無法得出本案專利實際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是改變藥物特定活性成分比例的結論。”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論述可以解讀為,如果本領域技術人員在閱讀說明書之后不需要付出創造性勞動即可以得知本發明要解決的技術問題與提高丹酚酸B的含量有關聯,則可以將本專利實際要解決的客觀技術問題確定為提高丹酚酸B的含量;如果本領域技術人員在閱讀說明書之后需要付出創造性勞動才可以得知本發明要解決的技術問題與提高丹酚酸B的含量有關聯,則因為說明書沒有公開上述技術內容,因此上述技術內容對應的技術貢獻沒有公開,也不能作為認定本專利客觀技術問題的依據。
四、小結
本文的分析表明,說明書沒有記載的技術效果,一般不得作為確定客觀技術問題的依據,因為發明人沒有發現并公開的技術效果,不是發明人的技術貢獻的內容,也不得作為創造性判斷的依據。但是,雖然說明書沒有記載,但本領域技術人員可以顯而易見地確定的技術效果,可以作為確定客觀技術問題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