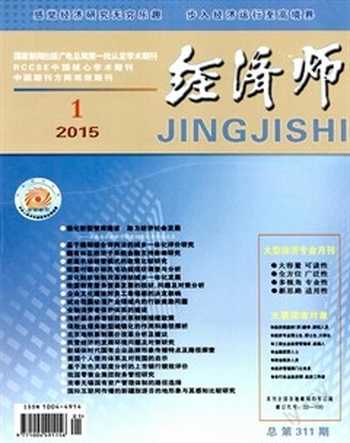縣鄉關系的理論解讀
吳艷 謝曉如
摘 要:鄉鎮本應是一級政權組織,但在實踐中已經成為縣的派出機構,出現了法律權力缺失的情況,比較突出的是鄉鎮人大缺位,人事權上移和鄉鎮財權喪失。盡管縣與鄉(鎮)之間有諸多矛盾,但縣與鄉(鎮)之間在工作上仍然能夠形成默契,這種默契可以通過“共謀”理論、“規則的內在方面”理論和“半自治社會領域”理論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論解釋。
關鍵詞:縣鄉關系 共謀 規則的內在方面 半自治社會領域
中圖分類號:F2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1-046-03
鄉鎮本應是一級政權組織,但在實踐中已經成為縣的派出機構,鄉鎮機構權力在實踐中有缺失的趨勢。雖然我國《憲法》《地方組織法》《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等制度性規范對縣鄉的關系、縣級政權組織職權和鄉鎮機構職權都作了相應規定,然而,實踐中鄉鎮機構的職權運行卻違背了制度設計的初衷,主要體現在:其一,鄉鎮人大權力在法律實踐上的缺失。我國《憲法》和《地方組織法》明確規定鄉鎮人大享有重大事項決定權、審查權、選舉權、罷免權、保障權等權力,然而,這些權力在實踐上還有待完善。其二,鄉鎮政府權力在法律實踐上的缺失。我國《憲法》和《地方組織法》明確規定鄉鎮政府有執行權、管理權、財權、保護權和保障權等權力,然而,鄉鎮政府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執行“上面”的責任狀和交辦的事項。同時,本該有的財權也完全交給縣里,每年縣里下撥的經費只能維持鄉鎮機構正常運轉。其三,鄉鎮黨委權力在制度實踐上的缺失。《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明確規定鄉鎮黨委有執行權、決定權、領導權、人事權等權力,然而,鄉鎮黨委直接受縣委領導,在執行權、決定權、人事權等方面只能根據縣委的指示而為之,并沒有真正的決定權。M鎮的縣鄉(鎮)關系雖然并不是單純的制度范疇中的關系,但是卻運轉正常,并表現出默契、高效的特點,這種縣鄉(鎮)關系的復雜性,可以通過“共謀”理論、“規則的內在方面”理論和“半自治社會領域”理論得到解釋。
一、“共謀”視角下的縣鄉關系
在經濟學研究中,“共謀”是指在非充分競爭的寡頭市場(oligopoly)條件下,幾家大公司秘密協商定價、瓜分市場等違反反壟斷法的經濟行為。經濟學研究認為,共謀行為的激勵在于這些私下協議有利于參與者之間通過非競爭手段獲取超過競爭價格的利潤。近年來的經濟學研究注意到了共謀行為與科層制組織之間的關系。例如,導致共謀行為的一個原因是組織內部各方的信息分布。不對稱信息使得公司所有者(委托方)無法有效控制經理(監督方)和員工(代理方)之間的共謀現象。梯若提出了新的博弈模型來描述分析在委托——監督——代理三方之間的組織結構中,監督方與代理方“共謀”應對委托方的博弈過程。周雪光借用梯若提出的概念將“共謀”界定為基層政府與其直接上級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種策略應對來自更上級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檢查監督。他認為,在現有體制下,基層政府的共謀行為已經成為一種制度化的非正式行為,這種共謀行為是其所處制度環境的產物,有著廣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礎。這些行為并不是個別官員或個別部門的私人活動,在許多情形下,在正式組織權力結構下公開運作,以政府部門的組織權威輔以實施,甚至是大張旗鼓地加以部署安排。學者們已發現基層政府間普遍流行共謀現象,就是在執行來自上級部門的各種指令政策時,基層政府常常共謀對策,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各種手段,來應付這些政策要求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檢查,導致了實際執行過程偏離政策初衷的結果。更多的情形下,這類行為體現在上下級基層政府持續雙向的互動過程中。因為這些應對策略和行為常常與上級政策指令不符甚至相悖,所以大多是通過非正式方式加以實施。對于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趙樹凱對其也進行了描述:“在應對自上而下的檢查中,地方上存在一種規律性現象:如果是省里來檢查,市、縣、鄉、村都緊急動員起來,共同應付;如果是市里檢查,縣、鄉、村則都緊急動員起來,共同應付。比如省里檢查時,市里有關部門就會提前探情況,向下邊的縣提供某些檢查信息、應付方法的“公共服務”,當市里來檢查時,縣里有關部門就為鄉鎮提供這樣的服務。”
在M鎮也存在基層政府的共謀現象,例如:2011年8月省里來人要到縣里檢查烤煙收購情況,路途中要經過M鎮的烤煙地,因鎮里烤煙烤房沒有建好,導致好多煙葉不能烤而爛在地里,縣里擔心省里發現,就事先通知M鎮領導叫人將路邊烤煙地的成熟煙葉摘了并把煙葉弄走,縣和鎮怕省里發現這一問題影響政績,不得不“共謀”通過摘、撿煙葉方式遮掩此事。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政府內部的考核機制設計在很大程度上促就了基層政府間形成利益共同體,為各方維護共同利益而參與共謀行為提供了另外一個制度化基礎,導致了目標替代;二是在目前中國政府組織環境條件下,制度正式化給基層官員的職業生涯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而行政關系人緣化是政府官員針對這些風險的應對策略;三是在制度正式化的過程中,制度環境壓力越大,政策執行的不確定性越高,行政關系人緣化趨勢越強,政府間共謀行為的程度便越高。
二、“規則的內在方面”或“內在觀點”視角下的縣鄉關系
“規則的內在方面”或“內在觀點”是由英國法學家哈特提出的,他在《法的概念》一書中首先提出了內在觀點(the internal point of view)和外在觀點(the external point of view),又稱內在視角(the internal perspective)和外在視角(the external perspective),哈特是這樣描述內在觀點和外在觀點的區分的:
當一個社會群體有某種行為規則時,這一事實就為許多密切相關但卻不同類型的主張提供了機會。因為就規則來說,有關的可能是:或者僅僅作為一個本人并不接受這些規則的觀察者,或者作為接受這些規則并以此作為指導的一個群體成員。我們可將這些主張分別稱為“外在觀點”和“內在觀點”。
在這里,哈特區分了兩種社會成員。第一種社會成員,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法律實踐的參與者,他所說的實踐規則是參與者在實踐當中所理解的那些規則,這些參與者將實踐規則視作行動的理由,贊揚和譴責的基礎等。這種社會成員,換句話來說,即使他們不參與實踐,也認真對待那些參與者的觀點。第二種社會成員,僅僅是一種觀察者,滿足于僅僅記錄與規則一致的可觀察行為的規律性和與背離規則相聯系的不良反應、譴責或懲罰中的進一步規律性。這種社會成員,與其說是將實踐規則描述為行動的根據,毋寧說是對實踐作一個因果關系的描述,指出某種行為(比如,將垃圾丟在街上)會規則地導致另一種行為(丟垃圾者也許會被警告,或者開出罰單并被罰款)。由此可見,內在觀點是一種將規則作為規則來看待的觀點,是一個誠信參與者的觀點,認可規則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內在觀點是一種對規則的認同、接受、信賴的態度。
哈特認為:“‘規則的內在方面意指規則行為模式中出現的行為者將行為模式視為自己行為及批評他人的理由和確證的主觀方面。在規則行為模式中,正面心態行為者‘反省主觀意念是‘規則的內在方面,行為的規律性是‘規則的外在方面。沒有‘反省性質的內在方面,行為模式便會成為諸如習慣等類的行為模式,或者成為僅有強暴要求逼迫的被迫行為模式。‘內在方面而非外在他人的‘要求,是規則存在的至關重要的本質特征。在任何規則存在的行為模式中,都可以發現這種‘內在方面”。
事實上,根據哈特“規則的內在方面”的理論來看,在M鎮政府里也可以發現一些鄉鎮領導和干部對待縣里下放的各種事權“規則”的積極態度,將這種規則作為規則來看待,認可、接受、信賴這種規則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并且是一個誠信參與者。例如:M鎮政府鎮長就是以積極心態對待縣里下發的各種責任狀、文件和安排的各種工作任務,想方設法把各種工作做好。根據M鎮政府工作規則的規定鎮長職責主要有:其一,鎮長領導和主持鎮人民政府的全面工作;其二,鎮長召集和主持鎮人民政府全體會議、鎮長辦公會議和鎮人民政府現場辦公會議。鎮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須經鎮長辦公會討論決定,日常工作要按分工負責處理。其三,鎮長在工作中,要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充分發揮各職能部門的作用,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密切聯系群眾,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發揚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樹立“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形象,努力學習,勤奮工作。根據這些職責看出,烤煙生產收購任務屬于鎮長的職責范疇,每年縣里都要與M鎮政府簽訂烤煙生產收購責任狀,并且每年下達的烤煙生產收購任務都呈增長趨勢。然而,農村的大部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人小孩,在這種情形下,烤煙任務的完成就是一大挑戰,鎮長為了完成縣里下達的烤煙任務,親自到各村各戶落實烤煙種植事宜,由于烤煙種植面積不夠,他自己租地種了120畝烤煙,最終M鎮政府光榮地完成了烤煙任務。由于鎮長工作的出色表現,他被調到了比較好的鎮擔任鎮長,鎮長的這種敬業精神正好有力地詮釋了哈特“規則的內在方面”的內涵。
三、“半自治社會領域”視角下的縣鄉關系
一些學者在研究鄉鎮權力時,發現鄉鎮權力運作過程的一種獨特方式,即“正式行政權力的非正式運作”。如孫立平、郭于華在對華北B鎮收糧過程的研究,發現“軟硬兼施”的現象,他們認為這是行政權力的一種“非正式行使”,也就是說,“在正式行政權力的行使過程中,基層政府官員對正式權力之外的本土性資源巧妙地利用,即將社會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地運用于正式權力的行使過程之中。”吳毅在《小鎮喧囂》中對鄉鎮權力運作技巧的展示也基本沿襲了孫立平的分析策略,再次鮮活地顯示了基層干部與農民互動時的“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那么,鄉鎮權力的非正式行使為何會得到上級的默認、鼓勵甚至“共謀”?并使鄉鎮政權非正式運作成為“共識”?這是由于制度總是在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得以貫徹實施,在這個社會關系網絡中,正如美國著名法人類學者穆爾(S.F. Moore)所言,存在無數半自治社會領域,這些半自治社會領域“能夠在內部生成規則、習俗與符號,但又易受源自其周圍的較大型社會(世界)的規則、決策和其他強制力的影響。半自治社會領域自身具有‘創制規則(Rule-Making)的能力,有誘導或強迫(人們)服從的手段;但它同時又置身于大型社會的母體之中,這個社會母體,時而根據半自治社會內部成員的請求,時而根據它本身的情況而能夠且實際地影響和侵入半自治社會內部。”半自治領域及其邊界是通過其活動的特征來加以限定和識別的,即它能夠生成規則并且強迫或勸導(人們)對這些規則的服從。因此,在社會領域中,人們相互交往形成的復雜社會關系的地方,都可能存在半自治社會領域,并生成其內部規則。國家政策在M鎮實施中也存在同樣的情形。國家政策要進入各村委會和各村民,基層政府、組織及其成員、村民間,都可能在相互關系中“創制規則”,半自治社會領域內部具有誘導、強迫其成員服從的手段。例如村委會成員有配合M政府開展種植烤煙工作的職責,但半自治社會領域卻還讓他們帶頭種植烤煙的“潛規則”;又如縣里2011年給M鎮每個村下達兩個特色農業項目,M鎮政府再安排給各村,由村民們自己出錢搞項目,如果項目不成功的話則由村民自己承擔損失,村民權衡利弊之后都不愿意搞項目,但半自治社會領域卻還讓村委會成員自己貸款搞項目的“強制性能力”;還有M鎮政府為了完成上級安排的各種工作任務,實行的“包村干部”制度,這些包村干部多半都是來自本鄉本土的熟人社會,他們與村民多是親戚、鄰居、朋友、同學,他們在村里開展工作會得到村民們的支持。
穆爾認為:“對半自治社會領域的詳察有力地表明:那些使內部生成的規則有效的不同過程,也往往是決定國家創制的法律規則之服從或不服從模式的直接力量。”正是因為半自治社會領域內部創制規則的存在,出現鄉鎮行政權力非正式行使的普遍現象,致使鄉鎮政府職能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阻礙鄉鎮職能的實施,以便保護地區、團體、群體等的利益。
近幾年M鎮各村的許多年輕人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兒童,無力再去種田種地,然而,上面仍然下達糧食生產任務,在這種情形之下,M鎮很難完成目標任務,只得玩起“數字游戲”。例如為了M鎮政府和相關人員的利益,村民、村委會、M鎮政府“共謀”虛報了糧食種植面積,還有對各村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也進行了虛報,半自治社會領域創制的規則使得縣級的下達目標任務最終沒有完成。
出現以上的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壓力型體制下的“高指標”、“多任務”與虛弱的鄉鎮權力不相匹配。在鄉鎮財政資源匱乏和權力弱小的現實下,很難完成上面下達的“高指標”、“多任務”。二是目標任務設置不切實際。上級在制定各鄉鎮目標任務時,只考慮自己認為重要的目標,而忽略各鄉鎮政權組織執行目標任務的實際能力和鄉鎮、民眾認為重要的目標,致使鄉鎮權力的非正式行使,正如歐陽靜所言:當壓力型體制的目標設置和激勵強度與基層政權組織的現實能力不相匹配之時,就容易誘導基層政權組織以造假、“共謀”、“擺平”等非正式的權力技術來應對壓力型體制中的高指標。三是“共謀”機制為鄉鎮政權的一些非正式行使提供了再生產空間。在壓力型體制之下,上級對鄉鎮權力的非正式行使的默認、鼓勵甚至“共謀”,使得鄉鎮政權的非正式運作成為可能。四是作為高指標和多任務的執行者,鄉鎮機構、基層自治組織及相關人員,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會基于利益權衡和主觀意愿,為完成目標任務而作出行動。就如孫立平、郭于華在對華北B鎮定購糧收購過程進行調查時,B鎮干部向他們所坦言的“從現在的情況看,沒有干部包村,上級布置的許多工作就沒有辦法進行。”五是法律對鄉鎮機構職能的規定太過于籠統,雖然《憲法》《地方組織法》和《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對鄉鎮機構職能作了規定,但是非常抽象不具體,導致現實中的鄉鎮機構職能運行出現越位、錯位。六是對鄉鎮領導和干部的考核沒有改革。雖然鄉鎮財政收入不再作為考核內容,但半自治社會領域里的它會決定著鄉鎮領導和干部的未來政治前途,所以,應該對鄉鎮領導的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對此,關于鄉鎮的考核內容和方式的改革,許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案,例如金曉偉提出改革考核內容方面:上級政府對鄉鎮工作的考核內容要從以經濟增長狀況為中心轉變為以向農民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狀況為中心,只有如此,才能實現鄉鎮政府職能的轉變。改革考核方式方面:應建立“雙向問責制”。目前對鄉鎮政府的問責機制是主要體現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約束和要求的“逆向問責制”,農民難以參與這種問責過程,無法對鄉鎮干部的工作情況做出評價,也就無法制約鄉鎮干部的行為。因此,我們應當建立“雙向問責制”,即不但能使上級政府約束基層政府行為,而且能夠使農民約束基層政府行為。
參考文獻:
[1] 周雪光.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一個政府行為的制度邏輯.開放時代,2009(12)
[2]趙樹凱.鄉鎮政府的應酬政治.http://www.china.com.cn/chinese/EC-c/941231.htm,2005.8.15
[3] 哈特.張文顯等譯.法律的概念.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4] 劉星.法律是什么.法律出版社,2009
[5] 孫立平,郭于華.軟硬兼施: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過程分析——華北B鎮收糧的個案研究.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2000
[6] 吳毅.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7] [美]薩莉.法爾克.穆爾.法律與社會變遷:以半自治社會領域作為適切的研究主題.胡昌明譯,舒國瀅校,鄭永流主編.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8] Sally Falk Moor. Law and Social Change: The Semi-Autonomous Social Field as an Appropriate Subject of Study. Law and Social Review,1973
[9] 歐陽靜.壓力型體制與鄉鎮的策略主義邏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3)
[10] 金曉偉.當前鄉鎮政府職能轉變的困境分析及對策.今日南國,2009(2)
[11] 吳理財.縣鄉關系的幾種理論模式.江漢論壇,2009(6)
(作者單位:吳艷,云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社科部;謝曉如,云南中醫學院人文與管理學院 云南昆明 650000;作者簡介:吳艷,云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社科部副教授,云南大學法學博士;謝曉如,云南中醫學院人文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副院長,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民商法。)
(責編:賈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