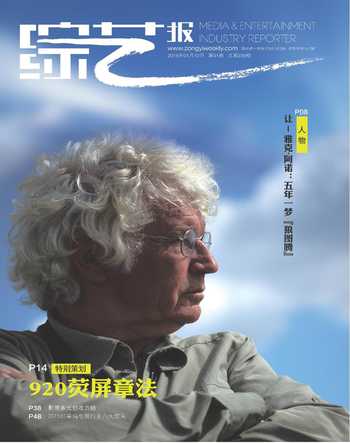那些扮演侵華日軍的演員
徐江
我很小的時候,老抗戰電影里的侵華日軍形象,是銀幕上一道獨有的風景。那些著名的反派演員,有很多都擅長扮演這類角色。最神奇的是老藝術家方化,永遠是戴著戰斗帽、雙頰留著泛青胡茬、腰桿筆挺,操一口中國人聽得奇怪、日本人肯定也都聽不懂的“銀幕鬼子話”,融兇狠、多疑、愚蠢、滑稽為一體,成為那個年代中國電影扮演鬼子的“頭號特型演員”。其他的反派明星如陳述、葛存壯,甚至著名京劇花臉袁世海,也都塑造了不少膾炙人口的鬼子形象。
經典的“鬼子”形象塑造,在后來的華語影視里有一些稀缺。尤其是電影,即便是《風聲》出人意料地用了漂亮且粉絲眾多的黃曉明去演日本人,感覺似乎仍不是那么一回事。二戰年代的日本男人里找不出像黃曉明那么標致的。“小日本”這個稱謂不只是蔑稱,跟他們當時的身高也有很大關系。日本人像高倉健那個身高的,在當年應該還是極少的。
雖說早年中國影視里的日本兵身高和面相,應該很貼近歷史。但精神氣質的塑造上還是有一些問題。喜劇性過強,表面上看是報復了敵人,往深里一想:不對啊!我們老祖先讓這么蠢的一幫子人欺負了十好幾年,難道我們的人比他們還蠢?這種誤區,幸虧被后來香川照之在《鬼子來了》里扮演的“花屋小三郎”形象糾正。“花屋”那個形象身上所傳遞出的侵略者氣質,更貼近人們在半個多世紀前新聞紀錄片里看到的侵華日軍,可以部分地啟發觀眾解答有關“人數眾多的國軍為什么干不過人數有限的鬼子”這樣的疑惑。
“神劇”風行的這幾年,抗日戲成了時髦。“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村姑、土匪、妓女、殘疾人似乎都成了無敵戰士,振奮得有一點嚇人。唯一的進步,可能就是演“鬼子”的演員,演技和類型都開始回升甚至超越了四五十年前的表演水準。這讓“老方化們”去世后觀眾的擔憂有了一定程度的緩解。目前還很難說誰是影視界的“第一鬼子”,但不同的類型里都有了值得大家追看的演員。
比如原汁原味的日本演員,除了矢野浩二,在《虎口拔牙》里扮演“渡邊”的三浦研一,在《借槍》里扮演“加藤敬二”的澀谷天馬等在娛樂中國觀眾的同時,承載了展示侵略者氣質的使命,他們在這些方面有當年的老方化所不具備的優勢。
本土演技派扮演侵華日軍的亮色,最常見的面孔之一是在《亮劍》《功勛》等眾多劇集出演的陸彭,單眼皮、不茍言笑,使這位電影學博士看著太像國人想象中的殘暴侵略者,但表演并不膚淺。在日本學習過戲劇的錢波,是位可以在演《茶館》時媲美英若誠的演員,他在《虎口拔牙》里扮演的“飯冢”,集狡詐、陰森和荒唐為一體,是過去國內影視從未出現過的豐滿的侵略者形象。
老戲骨趙恒煊,在演過了白眉大俠、刑警、黑社會、鐵道游擊隊長之后,挑戰侵華日軍,頗有方化重生的效果。耿長軍憑著《雪豹》里的“竹下俊”一舉成名,“宇文成都”陳昊在《利箭行動》里以“清水光一”一角驚艷、趙衛東在《地下交通站》里塑造的懷舊連環畫氣質的“黑藤”……這些演員對角色的成功塑造,都表明了國產影視在詮釋侵華日軍形象技法方面的進步。有了這些演技積累,將來再能在編、導意識深處盡量擺脫掉一些臉譜化和說教思維,抗戰題材的作品應該還有極大的提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