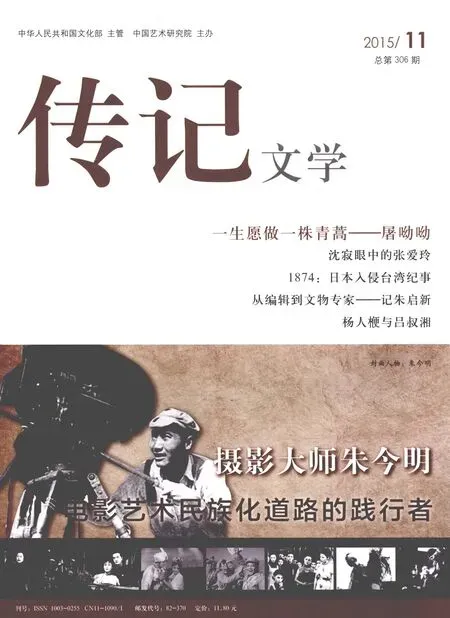族魂
——林連玉的華教事業
文 林阿綿
族魂——林連玉的華教事業
文 林阿綿

林連玉
在馬來西亞雪蘭莪州福建會館管轄的福建義山墓地里,有一座高大堂皇的墓園,正中是栩栩如生的林連玉先生的浮雕,上嵌“族魂”兩個大字,左右翼刻著林先生親筆書寫的詩句:“橫揮鐵腕批龍甲,怒奮空拳搏虎頭。”綠瓦覆蓋,極為壯觀。
1901年8月19日,林連玉出生在福建省永春縣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他7歲入私塾,16歲時,父親讓他到廈門當了3年學徒。正值陳嘉庚先生的集美學校師范部擴大招生,林連玉以優異成績考取,從此他便與教育事業結下不解之緣。他以優秀的成績畢業后留校教學。
1927年前后,林連玉渡洋南下,開始了他在東南亞一帶的教學事業和社會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林連玉加入雪蘭莪醫藥輔助隊,在新加坡參加馬來西亞保衛戰時,兩度幾乎喪命。馬來西亞淪陷后,為了逃避日寇的迫害,他躲在一個樹膠園里養豬過活。
恢復華文教育
地球上海水能到達的地方就會有華人,有華人處便會有華文教育。尤其是馬來西亞的華人,為了繼承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堅持不懈地維護母語的地位。
林連玉一生最輝煌的業績,便是“二戰”后,為了恢復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備受摧殘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極待振興。當時,華人約占馬來西亞人口的半數,他們的當務之急是恢復尊孔中學。尊孔中學位于首都吉隆坡的市中心區,“二戰”前辦有高級中學、初級中學、師范班和小學,擁有1000多學生,號稱雪蘭莪州的最高學府。馬來西亞淪陷期間,學校停辦,校舍被日軍占作軍部,所有設備蕩然無存,連空殼的校舍也是門破墻穿。其他華校已紛紛復課,尊孔中學的現狀令人們十分焦急。臨危受命,林連玉被聘為校長后,全身心地投入修復校舍的艱苦工作。他除了動員一些熱心教育事業的人士捐款外,便是把自己在淪陷時養豬積存下來的幾千元錢,全部奉獻給學校。一面修葺校舍,一面購置教具,一點一滴重新建設。兩年的辛勞奔波,終于使得尊孔中學煥然一新,于該年12月21日舉行了開學儀式,林連玉功不可沒。
林連玉當時的經濟情況非常拮據,有時候可以說是達到三餐不繼的地步。他的一位學生曾在文章中記述道:“為了尊孔,林先生的私人事業早已犧牲凈盡了……終于,有一天,在我們的教室門口上演了這么一出悲劇:那是一個六月的早晨,當林先生在第一節課踏入教室時,我便發覺到他的臉孔正給一團憂愁的云霧遮蓋著,他那無神的眼睛很明顯地表露出睡眠不足的神態。后來,他終于直截告訴我們,他的太太病了。昨天回來學校時,口袋里只有五毛錢,吃了一碗面,再買一包香煙便不剩下一個銅板了。他太太的病又是那么沉重,不曉得如何是好……”后來,學生們捐集了一點錢送給他,他起初拒絕,經勸告才肯收下,不禁流淚對學生說:“吃教育飯是死路,我老早就打算退出教育界了。可是,我始終沒有這樣做,這是因為良心不許我這么做……”
面對著華校教師十分清苦的境況,林連玉決心把他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以自身的力量謀求自己的福利,經過積極籌備,于1949年組織吉隆坡華校教師公會,他連任了十年的主席職務。這期間,他籌建會所,使教師公會經濟基礎永固,實行福利制度,使退休、去世的會員家屬不致陷入絕境。他為華校教師爭取公積金,爭取新的薪津制,使教師能夠安于教學,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通過教師節宴會提倡尊師重教,提高教師地位。
正當林連玉為進一步保衛華校教師的權益,發展華語華文教育事業積極展開工作時,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英殖民政府惡毒地拋出了一個所謂巫文教育報告書,妄圖以“國民學校”取代“方言學校”,也就是企圖用英文、巫文(即馬來文)教育來消滅華文教育。華文教育厄運當頭。正當生死存亡之際,林連玉領導的吉隆坡華校教師公會,在其他州教師會的要求下,挺身而出,召集全馬華校教師會代表大會,堅持反對英殖民當局消滅方言學校的報告書。并決定成立馬來西亞聯合邦華校教師總會(教總)。

1954年,當時在尊孔中學服務的林連玉與高中畢業班師生聚餐合影
華教史上的“林連玉時代”
1951年12月25日,教總的成立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的重要里程碑,標志著大馬華教運動進入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全新時代。可是林連玉并不熱衷于權力。教總成立后,他功成身退,把主席職位讓給他人,自己只居第二線,以一名理事的身份積極參與會務工作,并發揮他的巨大影響力,以大無畏的精神,掀起了反對殖民政府立法會制定的不利于華教的教育法令草案。他率領教總代表團與英殖官員展開面對面的斗爭,他說:“我們所爭的是整個民族的權利,并不是個人的飯碗。”
1953年12月的教總第三屆大會上,林連玉出任教總主席,從此開始了教總以至大馬華文教育史上的“林連玉時代”。他首先提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提出列華文為官方語言。這一建議,不僅石破天驚,也開啟了一個十多年爭取華語華文列為官方語文的運動。他以教總名義發表了《反對改方言學校為國民學校的宣言》,猶如一顆原子彈,震驚了整個殖民政府。
在一個細雨霏霏的夜晚,林連玉突然來到一個學生家中。那天他穿著一件白色的夏威夷T恤衫,T恤衫上和額前還留著淺淺的水漬。在那間狹窄的飯廳里,淡黃色的燈光映照下,他的面厐更顯得瘦小、蒼老,活像個剛從饑餓陣走出來的老難民。馬來西亞雖屬熱帶,可在夜里10點,又下著雨,冷氣逼人,他卻不以為意。學生遞過毛巾給他,又找出一件羊毛衣來。他搖搖手說:“我不冷,羊毛衣不必用。”只見他一邊擦額前的水漬,一邊說道:“最近,為了反對政府不利華文的教育法令,我經常代表教師會與殖民地官員爭辯。今天爭得非常激烈,結果不歡而散,政府很可能把我送進監獄或趕出境。我應先有準備,萬一被送出境或坐監,騰方兄已答應維持我太太的生活費,你們只要不時到我家看看就夠了。”那位學生笑笑說:“哪會這么嚴重,英國人是講民主的。”他不以為然地說:“英國人在他本國是講民主,在殖民地是無民主可講。一位華校教師教學生唱一首有民族意識的中國民歌,或批改作文時有‘帝國主義’四個字,而被逐出境的例子已經不少。” 林連玉越說越激昂:“我是代表教師公會爭取華文教育應有的權利,是代表全民華人的意愿,絕不怕坐獄和出境。再說現在世界的潮流,已是爭取獨立和民主的時代,各處殖民地紛紛宣布獨立,馬來西亞的獨立為期不遠了。我相信,如果殖民地政府把我抓入獄里,我們馬來西亞民主政府便會釋放我出來,若是趕我出境,也會接我回國。”這些從他內心說出來的話,可見他是多么熱愛馬來西亞,多么寄望于未來的民主政府呀!英殖民地政府審情度勢,在退出馬來西亞之前,沒有再興大獄加害林連玉。
1954年底,當馬來西亞聯合邦正醞釀自治——獨立時,林連玉領導的教總,改變過去華人團體不問政治的傳統,發表宣言表明“衷誠支持”馬來西亞的自治,“并將加強工作,訓導學童效忠于馬來西亞,與各民族平等,共建和平樂土”。同時他明確指出:“假如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它的第一語言是巫語,第二語言則為華語。”當國家由自治走向獨立后,他又挺身而出為華人爭取公民權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他在宣言中宣布:“我們的子子孫孫將世世代代在這可愛的土地上,同工作,同游戲;在遙遠的將來,更可因文化的交流,習性的相染,把界限完全泯滅,而成為一家人。我們當前的責任,就是要為我們的子子孫孫,打好友愛與合作的基礎,培養成共存共榮的觀念。”
由于林連玉領導教總取得一連串成就,挽救了華文教育,使他個人和教總聲譽鵲起,連英國殖民政府的官員都不得不承認,林連玉是“當前聯合邦最有勢力的人物之一”。

1972年1月5日,林連玉在雪蘭莪醫藥輔助隊30周年紀念宴會上吟詩之影
不屈不撓
馬來西亞獨立多年后,華文問題仍未徹底解決,華校教總當然要繼續向政府爭取,而且斗爭的氣氛更猛烈。萬萬沒想到,林連玉未被殖民政府抓進監獄,也未被趕出境,而民主政府竟于1961年首先取消了他的教師注冊證,逼迫他永遠離開畢生為之奮斗的教育事業。1964年,竟然把他的公民權也剝奪了。這是林連玉終身遺恨的事。
當消息傳來,群情悲憤,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而林連玉則處之泰然,將自己的得失置之度外。他在向尊孔中學師生告別講話中,一再勸慰大家,應當以學業為重,安心學習,不可為他個人的遭遇而憂憾。至于加諸于他本人的不公平的對待,將遵循法律途徑,繼續與當道者周旋到底,絕不低頭。
林連玉為保存他的公民權,被迫展開了長達3年的法律斗爭。官司從吉隆坡打到倫敦,又從倫敦打回到吉隆坡,最后以失敗而告終。從此,林連玉被迫離開了華教教育界的領導崗位,直到去世的20年間,他雖然患上眼病,仍然關心著華人的教育事業。在臨終前3個星期,由于聽到統治者寫了歪曲歷史事實、污蔑教總的文章,他還寫文章《駁東姑》加以申斥,指出:“爭取民族的權益是神圣的任務,我們永遠不會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濫用權力者棘手摧殘,仍然昂起頭來,頂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奮斗到底。”
生榮死哀
林連玉實踐著自己的誓言,他是戰斗到最后一息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與邪惡抗爭到底。1985年12月18日,這位偉大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因哮喘不治,終于離開了人間。當天,教總等15個華團為他組成治喪委員會。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打破了60年的慣例……將大廳辟為靈堂。全國華社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哀傷……不分階層、不分職業、不分黨派、不分老少,為失去一位導師、英雄、斗士而黯然神傷。遺體停放的3天里,每天都有大群來自各地的社團代表和公眾人士瞻仰致敬。人們熱烈響應15華團的號召,捐獻“林連玉基金”,以發揚他的精神,貫徹他的理想。盡管政府剝奪了他的公民權,人民卻給予他以人民英雄的最高榮譽。
下葬當天,他的靈柩在萬人陪送下,從大會堂出發,環繞吉隆坡市區游行5公里。炎日高照下,送殯隊伍在長長的街道排成1里多長的陣容,肅穆莊嚴地慢慢前行著,直到福建義山入土為安。
1986年,莊嚴肅穆的墓園隆重落成,“族魂”永垂不朽。
1985年12月18日,林連玉的忌日被定為“華教節”。華人社會世世代代將永遠銘記這位民族英雄的豐功偉績。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