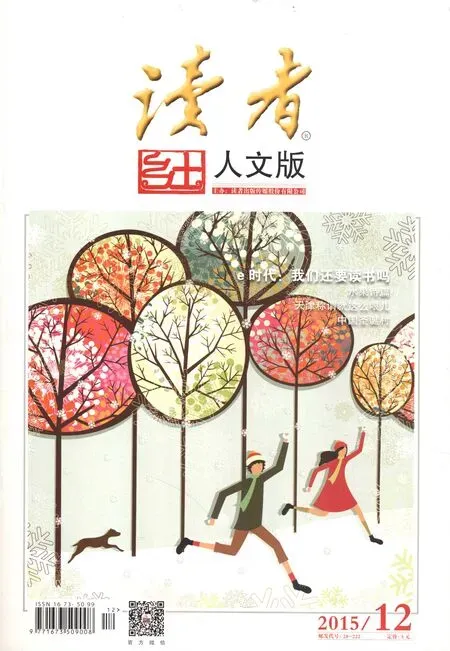冬藏
文/徐仁河
冬藏
文/徐仁河

老人們常說:“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其實關于冬藏,說句實話,它并不是發生在冬天的故事,而是在秋天就應該完成的事情。待冬天真正到來時,哪里還來得及。
什么是“冬藏”,意思很好解釋,一看字面就懂。但具體做什么農活,需要細細道來。最主要的當然是儲藏過冬的食物。最先收貯的自然是谷物,比如稻谷什么的,就應該是農歷十月份之前曬干揚盡,然后藏之谷倉。谷倉是一個圓形大甕,一般是黃土壘就的,外面刷了一層白石灰,講究的人家還會請老先生在谷倉外寫上“顆粒歸倉”幾個大字。谷倉里除了儲存稻谷,也得給芝麻、大豆什么的提供容身之所。大袋小袋的芝麻和大豆堆在谷堆上面,它們在田里做慣了鄰居,到了谷倉,也自然是親兄弟。
稻谷的兄弟不止這么多,都來的話,谷倉里住不下。比如玉米,就住不慣低矮、憋悶的谷倉,它們向往的是那種“高大上”的場地。主人就很了解它們的心意,一般是把它們成捆地綁束好,架在一根木杈上,然后高高地掛在屋檐下。這地方既敞亮又通氣,能曬著暖暖的太陽,卻又風刮不著雨淋不到,真是舒服。我們當地把玉米叫“玉蜀黍”,聽起來就像個漂亮姑娘的名字。千金小姐住閨樓,我們待它也的確是厚愛一分、高看一眼的。
如果說稻谷住的是“一居室”,玉米住的是“小高樓”,那番薯的住處就著實有些寒酸了。準確地說,它是不折不扣的“山頂洞人”。我們老家的房子一般臨山就坡而建,附近的山坡就會被我們掘出個三尺見方的小山洞,外面用木板釘牢,這就是番薯冬天的窩。番薯既可當飯,又可以做菜。煨番薯幾乎是我們童年必須經歷的事情,而番薯稀飯、番薯條,則是我們最為津津樂道的美食。這一切多虧了那個窖藏番薯的小山洞。番薯甚難伺候,既要接地氣,以免喪失水分,又要適度干燥,以防腐爛和霉變。有了那個干爽通風的小山洞,什么事情都迎刃而解了。
番薯野性難改,住山洞也是其咎由自取。唯覺可憐的是甘蔗,它住的卻是暗無天日的“地下室”。想來悲戚,這冬天唯一不在冬風到來之前進家門的便是甘蔗了,卻落得這般待遇。秋天甘蔗成熟的時候,農家一般把它們的大部分削干刨凈,送去榨房,榨成蔗汁,熬成黑紅色的糖漿,以便將來做甜粿時用。留下的那一部分,就在甘蔗地挖一個土坑,將青碧的甘蔗連皮帶稈地橫陳在土坑里,然后用土覆蓋。等到家里的糖糕甜粿吃得一干二凈,農家就會起出一兩捆甘蔗來,用單車或獨輪車推回家,供那些小饞嘴們享用。誠然,這亭亭玉立的甘蔗孤守田野荒丘,很覺凄慘可憐。但是靜心思量,不如此的話,那些一掐出水的“甜妹子”怎能熬得過凜冽的西北風呢。
當然,冬藏不光是為人準備的,我們還得為辛苦了一年的牲畜們準備過冬之物。瞧啊,每家的院門口都高高豎著個稻草垛。它的好處非常多,一方面冬天來了,老家的人喜歡用干稻草墊床鋪,那樣睡上去舒服、暖和。再有就是,干稻草是耕牛極為喜歡吃的“口糧”,大雪天里,扯一把干稻草給牛嚼,一整天都不會哞叫。牛是不叫了,如果不拿一捆稻草給旁邊的豬圈鋪一點,豬又會哼哼唧唧地發起牢騷來。原來,“天蓬元帥”們最喜歡睡在干稻草上,想念當初的那個溫柔之鄉,不知它們夢中的嫦娥是不是也“一個鼻子兩個孔”。
其實,不光是人,其他生靈也是深諳“冬藏”之道的。比如老鼠和螞蟻,它們忙忙碌碌一個秋天,為的就是把它們的小窩塞得滿滿當當。還有那些鳥兒,早早地換上了“羽絨服”,還把樹上的鳥巢絮得暖暖和和的,估計“小蟲干”也曬了不少吧。那些樹傻愣愣的,光頭禿尾,看起來寒酸可憐,殊不知它們的腳底下早已墊上厚厚的“落葉被”了。還有那些個一睡就是整個冬天的懶貨,原來它們才是“冬藏”的真正高手。如同躲貓貓的娃娃,怎么找也找不著它們。嗬,春天剛來那么一會兒,它們就齊刷刷蹦到你面前,嚇你一大跳!
(吳倩玉摘自《黃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