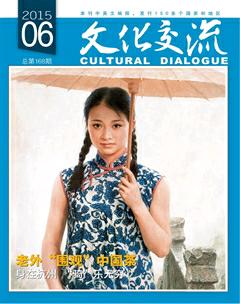毛春翔與文瀾閣書西遷
龔玉和



《四庫全書》是最豐富、最完備的中華典籍的集成之作。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圖書館為保護館屬四庫文瀾閣書作出過很大貢獻。
為此,筆者日前專門采訪了浙圖特藏部原主任毛春翔之子毛念誠,請他談談他父親當年參與搶救這一文化財富,歷盡艱難,將之護送到大后方,并負責保管所付出的努力。
父親(1898-1973)是浙江江山人,早年畢業于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曾在家鄉的中學教書,主編過《江山日報》,筆名有乘云、夷白、童生等。
1932年,父親去了北平,進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深感興趣,尤其對古籍研究情有獨鐘,將整個身心投入進去。然而,父親很快發現,北京作為文化古都,北平圖書館館藏豐富,但內容比較分散,個人精力有限,很難有大突破、出大成績。同時,父親更喜歡江南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氛圍,于是一年后,他回到浙江省城杭州,在浙江圖書館擔任善本編目員兼孤山分館主任干事,從事古籍編目與考證,終生不遺余力。
1937年抗戰爆發。7月中,奉教育部之令,浙圖館長陳訓慈組織文瀾閣書及其他珍貴善本西遷,浙大校長竺可楨協助運送,以避免戰禍。父親與同事全力以赴,將這些典籍打包成箱待運。
8月4日,閣書及善本由錢塘江南星橋碼頭起程,溯流西上,開始了流離顛沛的西遷歲月。館方授命父親作為押運管理員而全程隨行。此后九年中,父親與閣書及善本朝夕為伍,寸步不離,負責安全。
閣書及善本起先搬運到富陽漁山石馬村趙坤良家。父親在《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中記載:“八月一日,全館職員在孤山分館點書裝箱,總計閣書一百四十箱,善本書八十八箱,于四日晨裝船運往富陽漁山。……自江邊至石馬村,計程十五華里,雇工挑運,二人共肩一箱,半日竣事,趙君坤良、坤仲富有資產,待人和善,號召力強,一聲令出,數百挑夫立至,故搬運書箱毫不費力。”
石馬村處于群山之中,趙家房子頗為寬敞僻靜,且不收租金。9月13日,父親向館方報告:“地處群山圍繞中,舊屋不顯,可望不致遭損。”但是,11月后,隨著日軍的大舉入侵,存放在此的閣書也并不安全,館方決定轉運至建德北鄉松陽塢,存建德民教館緒塘分部東首方麗齋先生家中。
其時,浙大也開始內遷,停留建德。父親說,以文瀾閣書為主的浙圖典籍西遷,其實和浙大內遷是暗合的、有聯系的。浙圖沒有自己的車輛,閣書及善本轉運建德之時,竺可楨曾騰出汽車,又為浙圖從杭州搶運出一批重要圖書,與閣書及善本匯合。
浙圖典籍在建德停留時間不長,12月3日又運往龍泉,存放忠澤鄉村民家。據學者毛昭晰回憶,他讀到過一本日本著作(指松本剛著《略奪了的文化—戰爭與圖書》),里面記載杭州淪陷后,日本“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曾花三天時間調查文瀾閣、浙江建設廳、西湖博物館等二十六個政府與文化機構,但他們“很遺憾地”沒有找到四庫文瀾閣書。日本侵略者的企圖落了空。
此際浙大已在江西吉安、泰和,竺可楨電告教育部,鑒于日軍緊逼,形勢極為嚴峻,建議浙圖典籍直接遷移大后方。教育部同意后,竺可楨派一教師到龍泉,協助浙圖將典籍轉運貴陽,而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義的道途。
1938年3月23日,浙圖典籍從浙江出發,經福建、江西、湖南、廣西遷往貴州,一路崎嶇險惡,困難不計其數。車子經過江山時,有一輛翻倒在溪水之中,大約有3000冊典籍遭水浸泡,父親他們不得已停留縣城,在城隍廟進行曬晾。江山是父親的老家,人生離亂、命運難測之際,他沒有回去看一眼。車子匆匆又上路,此后大家只好見縫插針,休息時將水濕之書放在通風之處曬晾,保證了一冊無損。
許多年來,父親常鬧腰背痛,原來他正好坐在那輛翻倒的車上,摔下來時,因為身上背了一支手電筒,夾在腰上,致使腰部受傷。別人問起,父親擺擺手:老黃歷,老黃歷了。
歷經8個月,浙圖典籍運到貴陽,先存張家祠,隨即藏地母洞。保管工作起初由編纂夏定域主持,后來夏定域應聘去遵義浙大任教,便改由父親負責。
地母洞在貴陽北郊,少有人煙,比較荒涼,安全可以保證。洞高約十三四米,深約二十三四米,但是很潮濕。為了防止白蟻與霉變,父親他們“將書庫三面間以板壁,在箱底溝中多置白炭,潮氣可以稍煞”。保管圖書的日常首要工作是曝書。曝書必須搶晴天,往往歷好幾個月才能完成。貴陽多雨,地母洞曝書改每年一次為春秋兩次,全年沒有空閑停歇之日。如此六年,浙圖典籍保存完好,沒有受損。
父親講起,竺可楨多次來地母洞巡視,中間談到史地方家譚其驤幾回要求參與曝書,竺可楨未予同意(見《竺可楨日記》)。烽火遍野中覓一塊讀書的安定綠洲,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最好、最后的心境愿望。父親在地母洞也得便研習古籍不輟,對學業大有裨益。
1944年11月,日軍入黔。教育部令浙圖典籍再次遷往重慶。12月6日,浙圖典籍運抵西郊兩山隘口青木關—教育部駐地。此后,浙大不再參與浙圖典籍的所有事宜。文瀾閣管理委員會成立時,委派父親為秘書,負責保管浙圖典籍。
1945年抗戰勝利。1946年5月15日,浙圖典藏結束苦難的行旅,啟運返回杭州。夏定域和父親都在押運人員名單中。父親后來簡單有所回憶:“困苦之狀非數紙所能盡。在衡陽遇匪,警士開槍百余發始逸;在江西永新,余車左輪陷入水坑。幾傾覆;在上饒遇罕有大水,公路橋梁沖毀,停留十余日;在蘭溪過渡,書,烈日熏灼一日,皮膚若焦炭;凡此皆為了令人永遠難忘之遭遇。”7月5日,浙圖典藏終于西遷而東還、回到西湖孤山。
父親一直在浙圖研究古籍。鑒于抗戰時期館藏遭受到的磨難,他首先著手編寫《浙江圖書館特藏書目》(1949年版、1956年版),至今仍是查找浙江人文史料的經典手冊。此外,父親整理研究古籍的著述有多種,其中《古書版本常談》是一種較為權威的書。父親還有兩種油印本:《圖書目錄略說》《版本略說》為浙圖館藏。而今,我手邊仍珍藏著一種父親的手稿本《論語類編通義》。
多年來,父親與在浙圖工作過的陳訓慈、沙孟海、夏定域等人至為熟悉。他們都是治學嚴謹、考證確鑿、分析詳盡、文筆精煉的學者或古籍版本專家。
上世紀60年代中,父親退休,浙圖繼續留他在館內從事考證工作。“文革”來了,父親將戶口遷回老家江山,他早就有葉落歸根的念頭,想在家鄉安度余生。后來父親病重,不久就過世了。
文瀾閣展覽廳至今依然擺放著毛春翔當年護送浙圖典籍的照片,記錄著他為之付出的努力:傳遞和光大民族精神,保護和延續中華文明。
(本文圖片由毛念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