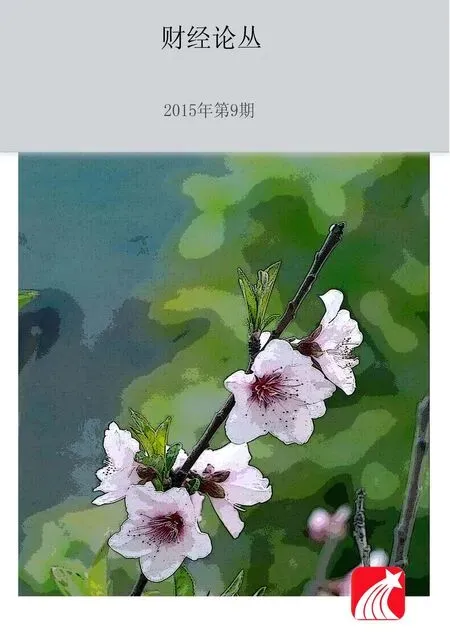知識資產與企業績效:激勵和監督機制的不對稱性
楊 青, 王 玉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
?
知識資產與企業績效:激勵和監督機制的不對稱性
楊 青, 王 玉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
本文對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及知識資產在不同的治理機制下對企業的經濟績效的影響機制進行理論探討,利用2007-2013年中國信息技術業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知識資產的增加有利于企業的經濟績效的提高,公司治理中的激勵和監督機制具有不對稱的調節作用,激勵機制強化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而過強的監督機制將弱化二者之間的關系。
知識資產;激勵機制;監督機制;企業績效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企業獲取和轉化資源、塑造資源差異及構建企業競爭優勢的有效來源,技術創新得到了企業界與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知識資產是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內在基礎,其主要凝結于企業知識型和經驗型員工中,企業能否有效開發和利用知識資產,形成新的知識和技術,促進創新活動,將決定著企業績效的高低[1]。然而,創新活動具有投資專用性、創新過程復雜性及未來收益不確定性等特點,這就決定了在任何時候與創新有關的各方不可能設立完全合約來確定各自的責任[2]。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隨著創新活動的增加而增加時,企業的創新決策者就可能做出侵害股東利益的自利行為,從而產生高昂的代理成本。那么,企業如何通過一套制度安排來確定不同參與者的權利和責任,引導決策者有效開發利用知識資產,進而提升創新能力,已成為公司治理機制的要旨所在。
企業層面的公司治理主要包括監督和激勵機制,學者們認為這兩種機制之間存在替代或互補的關系,不論監督機制還是激勵機制都可以降低代理成本、維護股東利益[3][4]。然而,外部董事與管理層之間本身就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尤其在創新強度較高的企業中,經營者對創新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過程更是無法被外部董事完全掌握。在此情況下,監督機制還能否有效地配置創新資源、提升企業績效,已成為亟待研究的現實問題。
本文從提升企業創新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發,結合資源基礎觀和代理理論,探討知識資產對企業經濟績效的作用過程,并就不同公司治理機制對創新資源配置效率的不對稱性作用機理進行研究,其創新性及貢獻主要在于:第一,從提升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發,分析公司治理機制對知識資產配置過程的影響效應,拓展對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視角,豐富現有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成果;第二,發現不同的公司治理機制對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影響具有不對稱性特點,對現有激勵與監督機制之間的互補關系作了有益的補充。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知識資產與企業績效
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擁有和控制的資源。企業掌握有價值的、稀缺的、難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資源是企業獲取和保持卓越績效的有力保證[5]。知識資產作為企業知識創新的源泉,能提高產品開發和產出的效率,已成為企業創造價值不可或缺的特有資源[6]。
企業的知識資產主要源于組織內部,表現為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兩類。知識創造理論認為組織知識創造起源于組織內隱性知識的共享及組織成員間、組織成員與群體間的交流、溝通和互動,知識在組織內部通過社會化、外在化、整合和內化實現知識創造,進而形成知識資產。因此,知識資產的形成具有組織情境依賴性和“根植性”的特點,使知識資產既難以通過市場公開定價獲得,又使其他企業的模仿行為面臨高成本約束。企業通過知識資產的積累構建天然的模仿與替代壁壘,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7]。同時,知識資產的持續積累能增強企業對知識的吸收和轉化能力,促進企業開發出更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8]。
同樣地,作為企業知識資產的外在表現,專利的法律特性也賦予了其異質性、稀缺性和難以模仿性等特征。雖然競爭對手可以通過分析企業的專利信息來進行產品創新,但由于受到知識、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其缺乏從專利信息中完全獲得未來潛在的創新投資機會的能力。因此,專利一方面保護了發明者的相關權利,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競爭對手的技術創新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1: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正相關。
(二)公司治理機制的調節作用
盡管企業的知識基礎廣泛分布于組織內部,但企業的高層管理團隊對創新資源的配置、重組和開發起著關鍵性的作用[9]。首先,具有營銷、銷售和研發職能背景的高管成員對產品和市場創新更加敏感,對產品設計及市場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因此更注重對創新資源的配置和創新帶來的回報[10][11]。其次,良好的領導方式能給員工提供智力激勵,鼓勵員工不要墨守成規,使員工關注自己的工作并產生濃厚興趣;關心員工的需求和想法,注重員工的個人發展并鼓勵員工表達自己的觀點,支持、鼓勵員工自由發揮想象力產生新觀念和新方法,有效開發員工的知識創新能力[12]。
然而,創新資源配置和開發的過程與收益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由于較高的信息不對稱使企業的高管往往為規避創新風險而減少對創新資源的配置與開發,有時甚至做出損害股東利益的自利行為。因此,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要既能促使經理有效配置知識資產,又不至于產生過高的代理成本。
1.知識資產與監督機制。知識資產的隱性特點使監督者即使花費大量的成本也難以達到有效監督的效果,甚至會影響管理者的決策質量[13]。此時,過度的監督可能會限制管理者對知識資產的配置權力,從而影響創新績效。在董事會的結構中,外部董事由于與公司的關聯程度低、利益沖突小而成為監督管理者行為的主要來源。但在信息不對稱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外部董事因無法獲得完全信息而降低對管理者創新決策行為監督的有效性。相比較而言,內部董事更了解企業實際情況、所處行業競爭狀況,更清楚企業需要采用的競爭戰略,更能發現、識別和把握技術創新機會,更能有效配置創新資源。
此外,兩職分離被認為是有效監督經理層行為的另一個途徑。當CEO兼任董事長職務時,CEO將獲得更大的控制權,董事會的獨立性受到損害,監控作用進一步削弱。然而,由于技術創新具有較高的風險性,董事和經理層的目標不一致會導致公司在重大決策時產生利益沖突。而兩職合一有利于董事會與經理層意見的統一,并賦予經營者更多的權利和創新自主權,加強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人力和物力支持[1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外部董事的比例、兩職分離的監督機制將弱化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
2.知識資產與激勵機制。企業技術創新需投入大量的資金,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投資回報周期長等特點,而經營者報酬主要依賴于企業的當前經營績效,因此缺乏有效激勵機制勢必會影響經營者進行創新的內在動力。此外,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需經營者和核心員工的大量人力資本投入,他們不斷地學習新技能增加了個人投入的成本,但技術創新的內在特征又限制個人將資源與技能投入其中。如果他們能分享由成功創新帶來的收益,那將提高其進行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因此,企業可通過授予經營者剩余索取權,有效實現經營者在技術創新中的剩余索取權與其擁有的剩余控制權的兩權對應,部分消除技術創新的外部性,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提高知識資產的配置效率[15]。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3:CEO的持股比例、薪酬水平等激勵機制將強化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中國2007-2013年在滬深交易所發行A股的信息技術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被ST和數據缺失較多的樣本,最終確定55家信息技術業上市公司共385個樣本觀測值。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和WIND數據庫、公司年報、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為確保數據的準確性,本文通過巨潮資訊網、中國上市公司資訊網等國內專業網站對數據進行核實和印證。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本文構建如下的回歸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
Performanceit=α+β1Innovativeit+β2Governanceit+β3Innovationit*Governanceit+β4Controlsit+εit
其中,Performanceit是被解釋變量,代表企業經濟績效,采用資產收益率ROA來進行衡量;Innovationit代表知識資產,采用企業每年獲得的專利總量(Patent)來衡量,具體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在模型中取對數處理;Governanceit代表公司治理機制,采用獨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和CEO兩職合一(Duality)兩個變量來衡量監督機制,獨立董事比例用獨立董事人數與董事會人數之比來測算,CEO兩職合一是虛擬變量,如果CEO兼任董事長,則該值為1,否則為0;采用CEO持股比例(Sharehold)和CEO的年薪(Salary)來衡量激勵機制,年薪水平在模型中取對數處理;Controlsit代表控制變量。根據以往研究文獻[16][17],我們對以下變量進行控制:(1)企業規模(Size),定義為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在模型中取對數處理;(2)企業上市年限(Age),定義為企業上市的年數;(3)資產負債率(Debt),定義為企業負債總和與企業總資產的比值;(4)企業所有權性質(SO),如果是國有性質,則取值為1,民營則為0。此外,本文設定年度虛擬變量(Year)來控制年度變化趨勢對企業績效的可能影響。
四、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
上述定義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及相關性見表1所示。

表1 變量的描述性與相關性
注:“* ”、“** ”和“*** ”分別表示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
從表1的結果可以發現,企業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正相關,而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的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并不一致,CEO年薪和持股比例與企業的經濟績效正相關,而獨立董事比例和兩職合一與企業的經濟績效負相關,這符合我們之前提出的理論假設,即公司治理的激勵與監督機制在資源配置效率上具有不對稱效應。
(二)檢驗結果與分析
在具體檢驗前,為避免異常值對檢驗結果的影響,本文對主要的連續變量在1%的水平上進行了縮尾處理,對所有進入模型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方差膨脹因子VIF診斷。此外,考慮到面板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時序相關和橫截面相關等問題,使用通常的面板數據估計方法會低估標準誤差,導致模型估計結果有偏。為保證檢驗結果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本文在后續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中主要采用Driscoll-Kraay標準誤進行估計。
1.主效應的回歸結果與討論。由表2可知,在所有的模型中,企業知識資產對企業經濟績效具有穩定的顯著正向作用(p<0.1),假設1得到驗證。企業具有越多的知識資產,則獲得更多的知識創新的來源,通過提高產品開發和產出的效率對企業經濟績效的提升起促進作用,這與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徐欣和唐清泉(2010)及Zhen Deng(1999)認為企業專利是R&D活動的結晶,專利的產出大大降低了R&D活動的不確定性,專利擁有量越多,對企業價值的貢獻越大[18][19]。
2.調節效應的回歸結果與討論。表2中的模型2、3顯示,公司治理中的激勵機制強化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之間的正向作用(p<0.1),表明經理持股能將個人利益與企業的長期價值保持一致,激勵經理人員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從事技術創新活動。在模型6中,經理人員的薪酬水平的調節效應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薪酬過高的經營者本身具有較大的權利[20],因而催生了他們攫取個人私利進而抑制企業的技術創新。模型4、5顯示,監督機制弱化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的正向作用(p<0.1),說明在信息不對稱程度較高的情況下,過多的監督將降低經營者創新決策的權利,影響創新資源配置的效率。在模型6中,兩職合一的監督機制并沒有起到調節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兩職合一將賦予經營者較高的管理自主權,進而產生損害股東利益的自利行為,減少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

表2 全樣本回歸分析結果
注:“* ”、“** ”和“*** ”分別表示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各模型對年份進行了控制,但結果沒有列示。下表同此。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以企業的R&D投入作為被解釋變量,重新對知識資產、公司治理與企業的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6中,除模型2外,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顯著正相關(p<0.1)。在模型2、3、6中,經營者年薪對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的正相關性有強化的作用(p<0.1),但經營者持股比例正向調節作用只在模型6中成立。模型4、5、6中檢驗的是公司治理中的監督機制,我們發現獨立董事比例對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的正相關關系有弱化的作用(p<0.1),但兩職合一的監督機制僅在模型5中表現出調節效應,模型6中的調節效應并不顯著。雖然表3的結果與表2存在部分差異,但總體檢驗結果基本一致,說明本文模型的穩健性較好。

表3 穩健性檢驗(以R&D投入作為知識資產指標)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資源基礎觀和代理理論,以2007-2013年中國信息技術業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檢驗知識資產對企業的經濟績效的影響及公司治理機制對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兩者關系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表明,作為稀缺性資源的知識資產能提高企業產品開發和產出的效率,對企業的經濟績效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公司治理機制中的激勵與監督機制對二者之間的關系調節作用呈現不對稱性,對經營者的激勵機制能提高其進行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提升其對知識資產的開發力度,進而強化知識資產與企業的經濟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但對經營者的過度監督會弱化二者之間的關系;知識資產的隱性特征增加了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外部董事因無法獲得完全信息而降低對管理者創新決策行為監督的有效性,進而降低經營者對知識資產的配置效率。
因此,創新程度較高的企業要加大對技術創新活動的投入力度,增加技術創新產出,提升企業的經濟績效;在選擇合適的公司治理機制時,應更加注重對創新決策者和參與者的激勵作用,降低他們對技術創新活動潛在風險的感知,激發他們有效配置創新資源的內在動力和能力,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
[1] David J.Teece. Capturing value from knowledge assets:The economy,markets for know-how and intangible asset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8,40(3):62-63.
[2] Belloc Filippo.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A survey[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2,26(5):835-864.
[3] Rediker K.J.,Seth A.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of altern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5,16(4):85-99.
[4] Zajac E.J.,Westphal J.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monitoring in large U.S. corporations: When is more not better?[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15(5):121-142.
[5] Fama E.F.,Jenson M.C. 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J].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26(2):327-349.
[6] Barney J.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7(3):99-120.
[7] 蔣翠清,楊善林.知識創新與企業知識資產形成機理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06,(5):82-86.
[8] Kor Y.Y.,Mahoney J.T. How dynamics,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resource deployments influence firm-level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7):489-496.
[9] McGrath R.G.,Tsai M.H.,Venkataraman S.,MacMillan I.C. Innovati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rent: A model and test[J].Management Science,1996,42(4):389-403.
[10] 馬富萍,郭曉川.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1,(8):87-92.
[11] 謝絢麗,趙勝利.中小企業的董事會結構與戰略選擇——基于中國企業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1, (1):101-111.
[12] Amabile T.M.,R.Conti,H.Coon,J.Lazenby and M.Herron. 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3):1154-1184.
[13] Burkart M.,Gromb D.,Panunzi F. Large shareholders, monitoring and the value of the fir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4):693-728.
[14] 龍勇,吳洋,張合.高新技術企業治理結構與技術創新的關系研究及指標設計[J].軟科學,2009,(4):56-60.
[15] 馮根福,溫軍.中國上市公司治理與企業技術創新關系的實證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7):91-101.
[16] Tuschke A.,Sanders W.G.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The case of German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5):631-649.
[17] Claessens S.,Djankov S.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Czech Republic[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9,27(4):498-513.
[18] 徐欣,唐清泉.R&D活動、創新專利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0,(8):820-29.
[19] Zhen De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predictors of stock performance[J].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1999,5(6):20-32.
[20] Adams R.,Heitor A.,Daniel F. Powerful CEOs and their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5,18(2):1403-1432.
(責任編輯:化 木)
Knowledge Asse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Asymmetric of Incentives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YANG Qing, WANG Y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Differ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has an impact on enterpris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sse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asset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oretically and then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ese IT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finds several major results. First, knowledge assets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economic performance. Second, monitoring and incen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have asymmetric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knowledge asse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ird incentive mechanism will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while monitoring mechanism will wea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knowledge assets; monitoring mechanisms; incentive mechanisms; economic performance
2015-03-04
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CXJJ-2013339);上海遠程教育集團科研計劃資助項目(JF1514)
楊青(1982-),女,江蘇常州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生,上海開放大學管理系講師;王玉(1953-),女,浙江寧波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F124.3
A
1004-4892(2015)09-007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