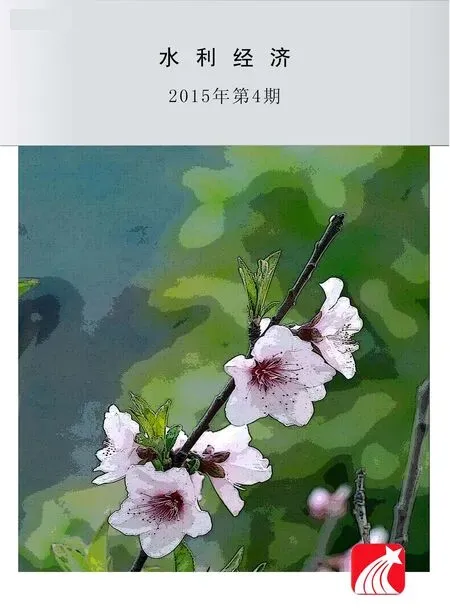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江蘇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的實證研究
童紀新,朱 園
(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南京 211100)
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江蘇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的實證研究
童紀新,朱 園
(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南京 211100)
基于江蘇省1985—2013年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相關數據,建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向量自回歸(VAR)模型。在VAR模型估計的基礎上,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江蘇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雙向作用機制。研究發現:江蘇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雙向作用機制,并且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大于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反作用;江蘇省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的主要表現形式為工業固體廢棄物,而對江蘇省經濟增長影響較大的污染物為工業固體廢棄物(抑制)和工業廢氣(促進)。針對分析結果,提出優化產業結構配置,改進生產技術、提升“工業三廢”污染治理水平、加大環保投入、完善環保法規等政策建議。
經濟增長;環境污染;VAR模型;雙向作用機制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保持高速增長, 2010年已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也付出了慘重的環境和資源代價,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快速工業化,環境污染趨勢加劇,環境質量嚴重惡化。江蘇省作為我國的經濟大省,綜合經濟實力在全國一直處于前列。自改革開放以來,地區生產總值已由1978年的249.24億元上升至2013年的59161.75億元。伴隨著經濟發展,江蘇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也呈顯著上升趨勢。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否說明江蘇省經濟增長是以污染環境為代價的呢?江蘇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怎樣的內在關聯?對這些疑問的解答,不僅有利于江蘇省在“十三五”期間實現可持續發展,還能對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其他城市的發展起到啟示作用。
綜觀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數研究證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雙向作用機制。國外對該問題的研究先于國內,其中Grossman等[1]開創性地研究發現了環境污染與人均收入之間的倒U型曲線關系。Panayotou[2]在進一步證實環境污染與人均收入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的基礎上,首次將該倒U型曲線定義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即EKC曲線。EKC理論提出之后,國外學者通過選擇不同的研究方法、指標、數據類型(主要有截面、面板、時間序列數據)驗證特定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是否符合EKC理論,研究結果進一步拓展了EKC曲線可能存在的形態特征,大體分為倒U、正U、正N(倒U+U)或倒N(U+倒U)。國內對兩者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主要開始于2000年以后。代表性文獻有:包群等[3]通過構建聯立方程組、劉金全等[4]采用線性和非線性方法、韓旭[5]運用時間序列研究方法對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是否遵循EKC規律進行實證研究,結論不盡相同,EKC理論在中國是否存在還不確定。在以全國所有省市為研究對象的同時,許多學者開始以具體省份或城市作為研究對象。丁繼紅等[6]以江蘇省為例,創新性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污染綜合指數,得出該指數與人均GDP呈N型曲線特征的結論。彭立穎等[7]以上海市為研究對象,通過回歸分析發現上海市主要4項污染物與人均GDP之間的關系遵循倒U型規律,并進一步探討了上海市EKC演變的驅動因子。王宜虎等[8]借助EKC理論模型對南京市進行研究發現,南京市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得到遏制,部分污染指標符合EKC倒U型曲線關系,政府的環境政策與環保投資取得一定成效。
由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數學者研究的重點是中國所有省份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是否遵循EKC規律,由于指標選取及量化、模型設定等方面的差異,各學者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同時,在已有的研究中,利用時間序列對具體省份的研究較少,利用VAR模型進行研究的文獻更是少見,基于此,筆者將通過VAR模型考察江蘇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雙向動態作用機制,并運用相關理論進行解釋。
1 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1.1 研究方法
參考已有文獻,筆者通過構建VAR模型,運用協整理論對進行過平穩性檢驗的指標變量之間是否具有長期均衡關系進行研究;再選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當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動時,整體系統會受到怎樣的動態影響;為評價兩類變量相互之間沖擊的重要程度,進一步運用方差分解來考察。最終結合以上分析給出結論與建議。
VAR模型是西姆斯1980年提出的一種可以很方便地進行指標變量之間動態性分析的動態聯立方程模型,各方程由相同的解釋變量組成,通過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的函數來建立模型。與傳統聯立方程模型相比, VAR模型很好地克服了在內、外生變量之間劃分、估計與推斷等方面的不足[9]。
VAR(p)模型的數學表達式為

式中:yt為k維內生變量列向量;xt為d維外生變量列向量;p為滯后階數;T為樣本個數;Φ1,…,Φp為k×k維矩陣;H為k×d維矩陣;εt為k維擾動列向量,并滿足cov(εt,εs)=0(t≠s)。
VAR模型的數學表達式也可以展開表示為


即k個方程組成了含有k個時間序列變量的VAR(p)模型。
1.2 數據說明
考慮到人均GDP相對于總量GDP更能準確地衡量真實的經濟發展水平,筆者選取人均GDP(元)指標來度量經濟增長,具體根據人均GDP平減指數與1985年不變價格進行平減[10]。污染物排放量與污染集中度是以往研究中較多采用的環境污染度量標準,根據江蘇省環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及數據的可獲得性,筆者采用污染物排放量指標,具體選取1985—2013年以來的3類指標:工業廢水排放量(億t)、工業廢氣排放量(億標m3)、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萬t)。為了獲得平穩性的時間序列,對所有指標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目的是為了消除變量在量綱上的差異以及在時間序列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表1)。數據由歷年《江蘇統計年鑒》和《江蘇省環境狀況公報》整理及計算而得。
2 VAR實證研究
2.1 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變量的平穩性對VAR模型估計的可靠性以及避免偽回歸具有很大影響,因而首先必須檢驗變量的平穩性。數據平穩性檢驗的方法很多,筆者選用最為常用的ADF檢驗。檢驗前先觀察時間序列的特征,看是否存在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根據表2的結果,在各顯著性水平下,P1、W1、G1、S1這4個時間序列均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屬于非平穩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ADF值均小于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滿足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
2.2 VAR模型的建立
根據ADF檢驗得出的結論,筆者將以江蘇省人均GDP、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為因變量,上述變量的滯后值為自變量來構建VAR模型。依據AIC(赤池信息量準則)和SC(施瓦茲準則)最小準則(表3),進一步確定VAR的滯后階數為4階,建立VAR(4)。最后通過AR特征根圖判定VAR模型的平穩性,若所有特征根倒數的模均小于1,即所有特征根倒數的模都在單位圓內,則VAR模型平穩;反之,不平穩。從表4可見所有特征根倒數的模均小于1,且在單位圓內,因此該VAR模型是穩定的。

表1 變量定義

表2 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3 VAR模型最優滯后期

表4 AR根
2.3 Johansen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目的是為了判定各變量之間是否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常用的方法有EG兩步法和Johansen協整檢驗法,前者最多只能用于判別多個變量存在的一個協整關系,后者常用于多變量協整分析,因此筆者將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在上文模型的條件下,選取滯后階數為4、且無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檢驗方式。表5的檢驗結果表明:按跡統計量標準,VAR模型的變量在1%顯著性水平下存在2個協整關系,在5%和10%顯著性水平下均存在3個協整關系;按最大特征根標準,VAR模型的變量在1%、5%、10%顯著性水平下分別存在1個、2個、3個協整關系。以上結果說明3類環境變量與人均GDP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且人均GDP與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呈負相關,與工業固體廢棄物呈正相關。
2.4 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筆者將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人均GDP與3類污染物指標之間的動態影響關系。脈沖響應函數是用以測量隨機擾動項的標準差沖擊影響其他變量當前及未來的取值,可直接反映變量之間的動態影響機制。筆者選取滯后期間數為10的脈沖響應模型[11]。

表5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a.3類污染物指標對經濟增長的脈沖響應分析。由圖1可看出工業廢水一直呈現負值,前2期較為平穩,從第3期開始下降,至第5期達到最小(響應值為-0.019 6),隨后逐漸遞增,并在第10期達到最大(響應值為-0.004 6);工業廢氣除在第2期有正增長外,其余各期均為負增長,從第3期持續下降,到第8期后轉為上升;工業固體廢棄物在前6期均為正增長,并在第3期達到最大(響應值為0.04267),在第4~10期內呈持續下降趨勢。進一步將3類污染物對經濟增長的各期沖擊響應值進行累加,其中工業廢水為-0.126 5、工業廢氣為-0.132 2、工業固體廢棄物為0.098 3。以上分析結果表明江蘇省經濟增長將導致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增加,工業廢水與工業廢氣的排放量減少。這一結果與上文協整分析結果一致,同時也與江蘇省的環境現狀比較吻合。江蘇省工業布局一直處于優化過程中,目前對工業廢氣、工業廢水的治理水平有較大幅度提升,而對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治理水平不甚理想。近幾年來,江蘇省工業廢水、工業廢氣的排放量基本得到控制,并趨于好轉,而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一直呈遞增趨勢。

圖1 3類污染物指標對經濟增長的脈沖響應
b.經濟增長對3類污染物指標的脈沖響應分析。由圖2可看出經濟增長對3類污染物一個單位的沖擊,在當期的響應值均為0,在剩余的期間內,對工業廢水、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沖擊響應值均為負,對工業廢氣的沖擊響應值均為正。與前文分析方法類似,將經濟增長對3類污染物的各期沖擊響應值進行累加,目的是為了方便比較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大小,其中工業廢水為-0.0881、工業廢氣為 0.68、工業固體廢棄物為-0.6171。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3類污染物指標中對經濟增長影響較大的為工業廢氣和工業固體廢棄物,其中工業固體廢棄物對經濟增長起抑制作用,而工業廢氣則帶動了經濟的增長。從整體而言,污染物排放對江蘇省經濟增長仍起抑制作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反作用機制。進一步將經濟增長與3類環境指標相互之間的累積沖擊響應值進行比較發現,江蘇省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比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反作用大。
2.5 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以VAR模型為基礎,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來評價結構沖擊的重要性[12]。根據方差分解結果(表6),在經濟增長的方差分解中,按照平均貢獻度的評判標準,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棄物對人均GDP的預測方差的解釋貢獻度相對較大,工業廢水則很小。這說明目前對江蘇省經濟增長起主要作用(促進或抑制)的是工業廢氣與工業固體廢棄物,工業廢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小。在3類污染指標的方差分解中,經濟增長對工業固體廢棄物預測方差的解釋貢獻度最大,工業廢水次之,工業廢氣最小,說明工業固體廢棄物為江蘇省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的主要表現形式。該部分分析結論與脈沖響應分析得出的結論大體一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本文所進行的VAR實證研究是可靠、穩定的。
3 結論和建議

圖2 經濟增長對3類污染物指標的脈沖響應
本文在VAR模型估計的基礎上,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對1985—2013年江蘇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雙向作用機制進行分析。研究發現:①江蘇省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比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反作用大,兩者之間存在雙向作用機制。②江蘇省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的主要表現形式為工業固體廢棄物,而對江蘇省經濟增長影響較大的污染物為工業固體廢棄物(抑制)和工業廢氣(促進)。

表6 經濟增長與3類污染指標的方差分解結果
結合上文的分析和得出的主要結論,筆者嘗試提出以下促進江蘇省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建議和措施。
a.優化產業結構配置。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經驗,一個國家或地區環境質量的好壞與該國或地區的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具有直接關系,并且三次產業結構中工農業、重化工業污染較為嚴重,而服務業、高技術產業污染相對較輕。江蘇省第二產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基本維持在50%以上,其中工業所占比例基本維持在45%以上,可以看出江蘇省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工業,現代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等行業的發展速度和傳統支柱行業相比還較為滯后。這樣的產業結構布局不可避免地造成環境質量的惡化。因此在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江蘇省應當以調優、調高、調輕為發展方向,加大對第一、第三產業的支持力度,尤其要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端制造業的發展力度,適當放緩發展第二產業中工業固體廢棄物污染較為嚴重的產業,逐步形成第一產業穩固發展、第二產業內部結構優化、第三產業各行業競相發展的良性發展局面。
b.改進生產技術,提升“工業三廢”污染治理水平。目前,工業固體廢棄物與工業廢水都在不同程度上抑制著江蘇省經濟的增長,而工業廢氣則帶動了江蘇省經濟的增長。因此,對于工業固體廢棄物以及工業廢水污染較為密集的產業,江蘇省應當充分利用本地教育科研資源,加大科研投入,重點扶持這些產業開發先進生產技術,并將其應用到從源頭的生產至結尾的污染治理過程中。對于工業廢氣污染較為密集的產業,也應當進一步優化生產技術,以達到污染最小化,經濟效益最大化的效果。
c.加大環保投入,完善環保法規。江蘇省早在“十一五”期間就已設定將環保投入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3%左右的目標,近幾年該比例已經提升到3%以上,據國際經驗,當該比例達到2.5%~3.0%時,環境質量會得到明顯改善。但可以看到江蘇省目前的環境污染問題依舊十分突出,環境質量的改善并沒有達到預期結果。分析原因,江蘇省在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期間,對于“工業三廢”的治理以及在保證環保投入的基礎上應當進一步提高環保建設資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各部門、各企業都應當建立完善的跟蹤監管、效益評價體系。政府與市場作用在某些情況下會失靈,而法律作為具有強制性、規范性、穩定性的保障性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不足。江蘇省應當注重解決環境政策的滯后性問題,靈活調整環境政策的同時還要兼顧有效性和低成本性,保證政策執行的透明度。與此同時,通過宣傳與教育提高民眾綠色消費的觀念以及參與環境污染治理的積極性,從而起到間接約束企業生產行為的作用,促使企業加快以節能減排為中心的技術改造,由重污染向輕污染、無污染產業轉移。
[1]GROSSMAN GM,KRUEGER A 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Cambridge: NBERWorking Paper,1991.
[2]PANAYOTOU T.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Geneva:ILO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Programme Working Paper,1993.
[3]包群,彭水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基于面板數據的聯立方程估計[J].世界經濟,2006(11):48-57.
[4]劉金全,鄭挺國,宋濤.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研究:基于線性和非線性計量模型的實證分析[J].中國軟科學,2009(2):98-106.
[5]韓旭.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4):85-89.
[6]丁繼紅,年艷.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剖析:以江蘇省為例[J].南開經濟研究,2010(2):64-79.
[7]彭立穎,童行偉,沈永林.上海市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18 (3):186-194.
[8]王宜虎,崔旭,陳雯.南京市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關系的實證研究[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3,15(2): 142-146.
[9]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10]張紅鳳,周峰,楊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的規制績效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9(3):14-26.
[11]閆新華,趙國浩.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VAR模型分析:基于山西的實證研究[J].經濟問題,2009(6): 59-62.
[12]彭水軍,包群.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基于廣義脈沖響應函數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6(5): 15-23.
F062.2
A
1003 -9511(2015)04 -0024 -05
2015-04 -23 編輯:方宇彤)
10.3880/j.issn.1003 -9511.2015.04.007
童紀新(1964—),男,浙江金華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技術經濟與統計分析研究。E-mail:jxtong@hh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