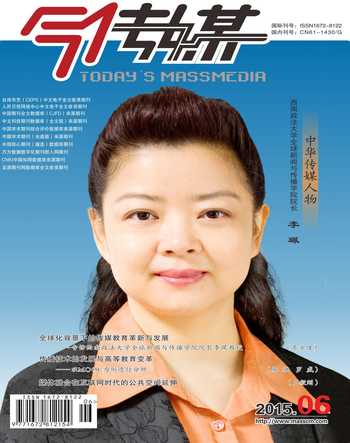社會轉型期網絡熱詞的社會學分析
閆宇曉
摘??要:“高端大氣上檔次”在2013年成為年度網絡用語之后,并未曇花一現,而是逐漸成為日常用語,這是轉型期社會生活發生深刻變化的結果。本文通過梳理相關的奢侈、時尚、消費的理論,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了該詞成為網絡熱詞的原因:生產力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費意愿提升是基礎;借助消費高檔商品向更高階層流動的欲求是社會心理原因;而大眾傳媒和廣告反復暗示,使高端、大氣、上檔次成為價值選擇,并借助網絡進入公眾視野。
從統計數據看,2014年我國GDP增至63.6萬億元,其中非農產業產值合計占比91.8%,高效的工業體系創造了豐盛的物質產品。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也大幅提高,201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26.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居民消費結構也持續改善,食品消費占比降至40%以下,交通通信、旅游、文化娛樂等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增加[6]。
因此,不論從統計數據還是從現實推動力上,可以發現當前中國社會生產力、大眾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都在不斷提高,這為追求“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商品和服務提供了基礎。但人們追求“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商品和服務,還有更深層的社會心理動因。
2.階層多元化背景下,向上流動欲求影響消費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改革前比較單一的工人、農民加知識分子的結構,向多元化發展。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渠道增加,其中以專業技術人員、自雇傭者、中小企業主為主的中間階層已經產生并不斷增長,2007年所占比例約為23%左右,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35%~40%[7]。每個社會階層總是向更高階層看齊,希望向上流動,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我國不斷壯大的中間階層作為主要的大眾消費力量,通過消費高檔次的產品和服務,除了滿足自己對高質量生活的需求外,無疑也是彰顯自己身份或向上流動的重要方式。而奢侈行業的大眾化、奢侈的分級,以及大眾消費品行業努力塑造的高端形象,通信產品的快速更新換代,使得每個社會階層的成員都可能擁有一兩件高端、上檔次的產品,比如香奈爾香水、寶潔的日化產品、蘋果手機等,并擁有這些產品附帶的“高端”標簽。
需要注意的是,上層社會地位的基礎是權力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高端消費只是外在表現。但對于較低階層來說,這些資源需要一代甚至幾代人持續不斷的積累才能獲得,而購買高檔產品或服務,更容易與較高階層達成外在的一致,因為單純的外在模仿更容易實現。媒體時常報道的用幾個月工資買蘋果手機、LV箱包仿冒品泛濫,均是中下階層希望提高其身份地位的一種表現。
3.大眾傳媒、廣告商使追求高端消費深入人心
西方品牌深諳消費的等級性,斥巨資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上塑造了高端、時尚、先進的形象,使其始終處于消費等級的頂端,不但將較高階層變成其消費者,更收獲了無數追求者。近年來,不少中國企業開始創立更貼近中國傳統、符合國人心理訴求的品牌,或重振本土名牌,本土品牌也努力通過大眾傳媒、廣告塑造高端、精致的品牌形象,主打對象也是高端人群或中產階級,這與西方品牌的運作邏輯是相同的。以中央電視臺為例,作為國家級官方媒體,是最正規、最高端,受眾最廣的媒體。企業通過央視發布廣告,既可以通過廣告內容向更多觀眾灌輸其良好的品牌形象外,還可以借央視的高端形象給自身貼上高端、上檔次的標簽。因此,不論是奢侈品還是大眾消費品、不論是國外品牌還是國內品牌,在大眾傳媒上均標榜“高端”、“品位”,并重復勸說人們“值得擁有”。反映在統計數據上,2012年我國廣告業營收4698億元,已位居世界第二[8]。在大眾傳媒和廣告商合力創造的這種消費意識形態中,“高端大氣上檔次”逐漸內化,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但社會中較高階層總是少數,大多數民眾可能擁有一兩件符合“高大上”的產品,但很難擁有“高大上”的生活方式。媒體營造出來的美好幻象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鴻溝,也使人們產生了一種自嘲、調侃心態。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當“高端大氣上檔次”一詞被推出,便頻頻見諸網絡,其中既有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向上流動的愿望,也有對現實的嘲諷。追根溯源,多樣、變化的現實生活是互聯網熱詞生發的土壤。“高端大氣上檔次”成為網絡熱詞,并融入日常用語,這是經濟、社會、傳媒三方共同作用的結果。社會生產力發展,人們收入水平增加,相關制度保障提高了人們的消費意愿,為高端產品和高端消費追求提供了基礎;社會階層多元化背景下,人們向上流動渠道增加,通過消費高端的商品以彰顯自己的身份或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則提供了持久而穩定的社會心理動因;大眾傳媒和廣告的反復勸告和暗示,則使得“高端大氣上檔次”這一詞語進入到公眾視野,并最終借助網絡的推波助瀾,成為網絡熱詞。
參考文獻:
- (法)吉爾·利波維茨基著.謝強譯.永恒的奢侈——從圣物歲月到品牌時代[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 (德)齊奧爾格·西美爾著.費勇,吳燕譯.時尚的哲學[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
- (法)讓·波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鋼譯.消費社會[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王寧.中國何以未能走向消費型社會[J].社會,2009(2).
- 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全文[R].http://www.gov.cn/test/2013-03/19/?content_2357136.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R].?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 陸學藝.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遷60年[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2010(3).
- 中國廣告協會:2012年我國廣告營業額突破4000億元[N].新華網,?2013-04-26.
[責任編輯: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