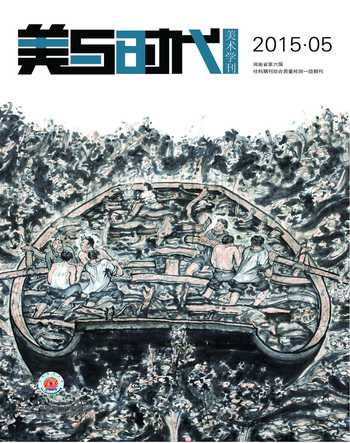傅抱石對我山水畫創作的影響
摘 要:傅抱石(1904-1965)先生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最為杰出的藝術家之一,他開辟了中國畫創作的新時代,他的藝術實踐和歷史功績在中國美術史上有著非同凡響的里程碑意義,對現代山水畫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也從其藝術創作中汲取大量營養,大致可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在題材選取方面;第二是對我的寫生活動的影響——尤為重視寫生在創作中的作用;第三是我對“抱石皴”的理解與應用。
關鍵詞:傅抱石 山水畫 題材 寫生 抱石皴
傅抱石先生是20世紀我國美術史上最為杰出的藝術家之一,他的藝術實踐開辟了中國畫創作的新時代。作為一名全面而優秀的藝術家,對后世的影響是深遠的,我作為蕓蕓后生之一,在山水畫創作方面也深受先生藝術創作的影響。
一、題材的選取
題材的選取是一名藝術家首當其沖要面臨和思考的問題,題材選擇的過程本身也屬于創作構思的一部分。
傅抱石先生在《我的作品題材》一文中總結其作品題材的來源時說到:“拙作題材的來源,很顯著的可以分為四類。即:“1.擷取大自然的某一部分,作為畫面的主題。2.構寫前人的詩,將詩的意境,移入畫面。3.營制歷史上若干美的故實。4.全部或部分地臨摹古人之作。”其第一點和第四點對我影響尤其深遠。
擷取大自然的某一部分,作為畫面的主體
其第一點“擷取大自然的某一部分,作為畫面的主體”即所謂的“師造化”。傅抱石的藝術生涯中他花了大量時間到大自然中去尋找靈感,他一生多次舉行寫生活動,足跡幾乎游遍祖國大陸,甚至擴及東歐。而且,給他一生真正帶來轉折性的關鍵影響也是從1957年東歐寫生開始的。
我在剛學習山水畫時,一談到創作,就有一種無從下手的感覺,只有當我深入生活,面對氣象萬千的大自然,創作才能有感而發。如我2010年登太行山,時值金秋時節,家家戶戶山民的樓頂都晾曬著他們豐收的果實,一晚從下榻處的樓頂遠遠望去,那果實在樹木掩映和昏暗的燈光中尤顯奪目,頓時感懷太行居民的樸實和辛勤,回去后即滿腔熱情創作了《太行金秋》;又如我2011年旅行至西藏拉薩色拉寺,寺廟在叢林掩印、云霧環繞中中顯得尤為神秘,寺中僧人虔誠誦經的場景深深地印在我腦海里,回去后又創作《云端古寺》。
在切身體驗造化給予的恩惠之后,我更是尤為重視觀察生活、力爭從大自然中獲取創作靈感。得益于此最基本的認識,但獲時機,我便抓住機會游歷祖國名山大川,并以此作為我的創作題材。
全部或部分地臨摹古人之作
其第四點“全部或部分地臨摹古人之作”便是臨摹創作了,即強調應當重視前人傳統。傅抱石是非常重視臨摹的,范寬、王蒙、周臣、石濤等等諸多名家他都曾專研學習過,也有大量作品是臨摹創作的,如《觀瀑圖》便是脫胎于張瑞圖的作品,《精廬中有誦經人》出自梅瞿山作品。
大師尚且如此勤奮,我又豈敢懈怠?我自學習山水畫以來,也認識到臨摹古人傳統的重要性,曾反復臨摹元吳鎮《洞庭漁隱圖》、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等傳世名作,宋畫小品、明清扇面、石濤冊頁等都有所涉及。
除了以上所列的全部臨摹古人之作外,我亦有部分創作屬“部分臨摹古人之作”的作品。如我酷愛趙伯駒的青綠山水《江山秋色圖》,便仿其筆意和設色方法創作了一組青綠山水“春臺明月”“平流涌瀑”“萬松疊翠”“平崗艷雪”。
臨摹不僅是學習山水畫的一個重要過程,也關乎山水畫的傳承問題,是學習山水畫的必由之路。
二、強調寫生在創作中的作用
19世紀末,西學東漸,西方美術觀念傳入中國,以東西方文化交融為特點的新美術運動逐漸展開,傳統繪畫遭到史無前例的沖擊。在中國畫程式日益僵化的背景下,為避免因長期臨摹出現的陳陳相因之弊端,寫生漸入人心。葉宗鎬所著《傅抱石年譜》考察詳盡,對傅抱石先生的寫生速寫均一一列出,從1953年至1963年共計寫生活動10余次。傅抱石致力于中國畫的創新,一生極為勤奮,晚年的傅抱石幾乎一直在旅途中作畫,寫生畫成為其晚年創作的主題,他的這一習慣也深深影響了我。
(一)我的四次寫生活動
2010年5月,赴河南省新鄉市輝縣太行山郭亮村寫生,為期28天。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寫生,之所以選擇到太行山寫生,是由于太行山多核桃樹,樹木蒼老而樹葉幾近凋零,這對于初學者來說易于直觀的看清樹木的結構和生長方向。雖說一開始只進行簡單的單顆樹的練習,但對于樹木的姿態、樹枝的穿插、樹皮的質感等等,每一樣都是我們要花時間去克服和解決的問題。經過長達將近一個月的寫生,我也一點點掌握了樹石是(尤其是樹)的基本寫生方法。有幸得益于當初年少,精力充沛、時間充裕、心態平和不急于求成,才有可能花費這么長時間旅居在外,只為解決單顆樹的基本問題。可以說,相對于許多山水畫學習者,我對樹的寫生還是頗下功夫或者說相對掌握熟練的,這也是造就了我在日后的山水畫創作中,幾乎以樹作為畫面主體的原因。
2010年11月,赴廣東肇慶鼎湖山寫生,為期22天。這一次以“山水小景寫生”為目的,在積累了數十張作品后陡然發現這些作品都是按照“所見即所得”的視覺方式來描繪自然,與其說是山水小景寫生,更多的卻更像是用國畫材料在畫素描風景。而山水畫講究“可游可居”,并不是直接對景寫生這么簡單,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從原本停留的鼎湖山后山繞到前山寫生。在輾轉的途中,我開始留心山體的走勢變化,踹度山間小溪從何而來又流向何處等問題。我也因此培養了處理畫面空間的能力、構圖能力。如《鼎湖山色》,我已經學會把初進山時經過的蜿蜒小溪、途中所遇行人、山間印象深刻的蒼翠古樹、山頂云霧環繞的寺廟融入在一個畫面中,其中不僅可窺見我登山鼎湖山數天來游歷的經過,更是國畫的寫生方式在我的創作中萌芽的開端。
2011年5月,再次赴河南輝縣太行山寫生。又一次登上太行,再次感悟太行的巍峨壯觀和樸實無華。前一次寫生的鼎湖山寫生多地處嶺南,陽光雨水充足,樹木枝繁葉茂,層層掩映,寫生也更多注重“深遠”。而太行壯闊,我常以大筆蘸濃墨率性而為,此次寫生的作品取景也更為開闊,寫“大山大水”,多為全景式構圖,我的創作風格也由此拓寬,為日后創作尋求了更多的可能性。
2011年11月,赴湖南省懷化市侗族自治縣、廣西桂林、陽朔寫生;相比太行威嚴的氣勢,南方的山水秀潤可人,處理起來理應細膩一些。以前我慣用焦墨落筆,對墨色層次并無過多思考,更談不上對其進行合理應用。而這一次,面對南方的涓涓細流,宛如嬌羞女子般的郁郁山色,又怎敢再粗魯待之?我試圖在墨色上作些變化,雖然這一次在墨色上的探索還顯稚拙,但有了更多的思考,對于日后的創作還是大有裨益的。
可以說,這4次寫生活動對我的山水畫創作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古代中國,所謂“行萬里路”,畫家或策杖于山林,或泛舟于江湖,飽覽山河美景,但幾乎多是閑情雅致的行旅。而我在多次的寫生中,逐漸解決山水畫技法問題,從現實生活中激發創作的靈感,初步形成了我山水畫寫生創作的風貌。
三、我對“抱石皴”的理解與借鑒
我們學習和研究山水畫,必然繞不開皴法的問題。山水畫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皴法的誕生、成熟與發展,甚至可以說,山水畫的發展嬗變主要取決于皴法的發展嬗變,可謂是皴法的成熟,一名山水畫家則自成風貌。
傅抱石擅長以破筆散鋒運筆,恣縱灑脫、奔放不羈、不加修飾、隨心所欲,在畫壇早有盛名,被稱為“抱石皴”。研究者通常圍繞傅抱石皴怎樣沖破中鋒、側鋒等固有筆法的極限來定義“抱石皴”。而我認為,逆鋒用筆或散鋒用筆只能作為“抱石皴”典型樣例,“抱石皴”的核心在于傅抱石創造的是一種“活”的皴法。皴法的系統介紹和流傳應當歸功于清朝康熙年間編撰的《芥子園畫譜》,畫譜記載的皴法不下三十種,這些高度程式化的總結確實給初學者帶來了許多便利,但長期摹古,相沿成習,皴法就失去其生命力了。傅抱石也曾在文章中感嘆《芥子園畫譜》在總結皴法時沒有提及“師法自然”是最大的缺點。
另一方面,從我學習山水畫的切身體會來看,皴法并不是孤立的,如果不能與“勾”“點”“染”結合起來表現,皴法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對“抱石皴”的理解也應當與其余幾種技法結合起來研究。如在《瀟瀟暮雨》一圖中,傅抱石在表現四川山岳半土半石的時候經常要用到這種皴法。他利用皮紙紋理粗糙的特點,硬毫逆鋒而上皴出山石結構,又結合“破筆點”豐富其紋理,最后又經過數遍渲染以烘托出雨景的氣氛。
長期以來,畫家們根據自然界真山真水的各種特點,在實踐中逐漸掌握不同的表現規律,創造出各種皴法,它是民族繪畫極為優秀的傳統技法之一,但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高度程式化的藝術形式。在長期摹古的風氣下,的確有人將原本發展于真山真水的、活的皴法誤認為是死的程式,生搬硬套。傅抱石并不拘泥于一家之法,所用皴法從臨摹古人的畫開始,再到生活中去寫生,長期實踐,逐步形成,“活”才是抱石皴的靈魂。
在20世紀變革風云激蕩的中國畫壇, 傅抱石既堅守傳統,又把50年代初開始的以寫生帶動傳統國畫推陳出新的運動推向一個歷史的高潮,并由此推動新山水畫在20世紀中期的發展,我也借先生的智慧尋求到了自己的山水畫創作之路,謹以此文向先生致敬。
參考文獻:
[1] 傅抱石.傅抱石談中國畫[M].北京:中國青年美術出版社,2011
[2] 萬新華.傅抱石繪畫研究1949-1965[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3] 葉宗鎬.傅抱石年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姜又銘,上海大學美術學院2012級國畫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