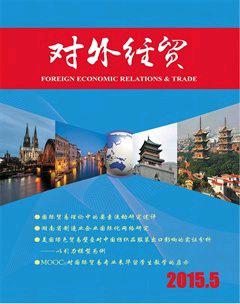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
李飛 劉寒波



[摘要]基于我國農村居民階段性大額消費特征,在構建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時變參數模型從動態演化角度分析了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表明:總體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且效應呈擴大趨勢;從區域上看,糧食主產區的擠入效應大于糧食主銷區,但糧食主產區擠入效應呈下降趨勢,而糧食主銷區仍保持穩定增長,波動較小。從提高農業基礎設施存量、流量水平以及優化農業基礎設施結構等方面提出了相關對策建議。
[關鍵詞]農業基礎設施;農村居民消費;動態演化
[中圖分類號]F3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2095-3283(2015)05-0098-03
[作者簡介]李飛(1989-),男,漢族,湖南益陽人,在讀博士,研究方向: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劉寒波(1965-),男,漢族,湖南岳陽人,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公共財政。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農業基礎設施供給的績效評價:基于“雙EQ”框架(項目編號:71273086)和2014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項目編號:CX2014B286)對本文資助。
一、引言
農村居民消費能力主要受家庭收入和消費平臺影響,而農業基礎設施公共投入既可以改善農業生產能力,促進農民農業收入增長,也能刺激要素流動,激發農村居民消費需求。但關于農業基礎設施政府公共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的關系至今存在爭議,其爭議主要圍繞擠出效應(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導致農村居民消費減少)還是擠入效應(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引起農村居民消費增長)。其中,Aschauer(1985)、楚爾鳴(2008)、Okubo(2003)、Barro(1985)、Tsung-wuho(2001)、李樹培(2009)和李建強(2010)等學者從投資總量的角度證明了政府公共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而楊智峰(2008)、申琳(2007)、Devereus(2004)、Karras(1994)、姜洋(2009)等學者卻認為政府公共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出效應;還有學者認為政府公共支出可能對居民消費具有“雙重”影響,即在短期內可能表現為擠入效應,但從長期看可能表現為擠出效應(謝建國,2002;溫嬌秀,2007);此外,也有學者從基礎設施投資結構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種類的基礎設施投入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賀京同,2009;洪源,2009;李春琦,2010)。
縱觀已有研究不難發現: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雖已得到學術界的關注,但由于樣本范圍、模型構建以及實證方法上的差異導致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結論。同時,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及農村發展的特殊情況導致西方的先進理論在中國并不具有普適性,如西方主流的生命周期和永久假設理論;其次,現有研究中衡量農業基礎設施投入變量大多采用“流量”數據,而未考慮“存量”基礎設施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再次,現有研究也并未考慮把農業基礎設施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進行動態化考量,即可能這種影響并不是固定地表現為“擠入”或“擠出”效應,它可能存在動態發展過程。因此,本文將利用農業基礎設施“存量”數據,選擇時變模型,從動態角度分析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
國內學者認為西方主流的現代消費理論并不適用于分析我國居民的消費行為(尉高師,2003),主要歸結于以下三個方面原因:第一,我國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具有階段性特征,如建房、結婚、子女教育等階段,而并非西方現代消費理論所闡釋的用一輩子的時間來平滑消費,因此,為實現某一消費目標,每隔一段時期就會出現大額支出;第二,我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尚不完善,同時受傳統觀念影響,農民并不愿意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因此,在大額消費前必須進行儲蓄;第三,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落后,農民收入偏低,導致生產行為并非追求收益最大化(即經濟理性),而是家庭成員需求滿足程度和勞動力辛苦程度之間的某種均衡,即家庭整體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本文試圖構建農業基礎設施投入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并用家庭整體效用最大化作為衡量消費能力的體現,具體建立模型如下: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了1989—2013年關于農業基礎設施、農村居民消費量以及農村居民收入等數據。同時,為使模型擬合效果更佳,本文選取人均數據作為各指標的衡量值。
首先,我國官方尚未有農業基礎設施存量指標的統計。目前,學者們主要采用貨幣和實物兩類指標進行衡量。但由于貨幣指標通常是投資量直接加總,難免具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實物衡量卻因度量單位的差異也存在缺陷,使得投資流量積累無法正確反映真實有效的基礎設施資本存量(Pritchett,1996;何曉萍,2014)。通常較準確的方法是利用永續盤存法估算農業基礎設施存量,但折舊率的選定和初期資本存量對盤存結果影響較大,所以學者們在農業基礎設施估算上存在差異。為此,本文在綜合現有基礎設施存量研究文獻中折舊率選取范圍的基礎上,取平均值作為本文折舊率指標①,而初始資本則直接采用當年農業基礎設施投資額②,而農業基礎設施當年投資額數據來源于中經網數據庫。
其次,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量數據分別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同時考慮到價格因素對收入和消費的影響,本文采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上述指標進行調整。
(三)實證結果及解釋
為了衡量我國不同區域的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同時考慮糧食生產等因素,本文將利用時變參數模型對糧食主產區和糧食主銷區③的農民消費情況進行分析,具體的測量方程和狀態方程見表1:
在此基礎上,根據表1的時變參數模型結果可進一步計算出農業基礎設施對全國糧食主產區以及糧食主銷區農村居民消費的動態效應值,具體見圖1。endprint
從圖1可知:1總體而言,從1989—2013年,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對農村居民消費并沒有產生擠出效應,而是具有擠入效應,且擠入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正逐步放大,這與陳沖(2011)等學者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2擠入效應的大小與趨勢存在差異,糧食主產區的農業基礎設施的擠入效應大于糧食主銷區。這是因為糧食主產區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改善了當地落后的生產條件以及交通基礎設施條件,在實現農民收入增長的同時使農民獲得了外部交易的機會,激發了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但近年來,糧食主產區的農業基礎設施對農村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呈下降趨勢,這可能是由于大量農村人口選擇外出就業,使得農村消費人群減少,從而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量。此外,糧食主銷區的擠入效應持續增長,但增長速度較慢。這是因為糧食主銷區一般處于經濟較發達地區,城鎮化水平比較高,農業經濟發達,特別是大城鎮周邊的都市農業發展較好,這些都能促進當地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高。
四、結論和對策建議
(一)結論
在我國,農業基礎設施一般屬于政府公共投資,考慮到不同時期農業基礎設施公共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的影響不同,本文利用時變參數模型分析了影響的波動情況,并根據糧食生產功能分區,綜合對比分析了糧食主產區與糧食主銷區間的差異及趨勢,得出以下結論:1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并呈逐步擴大趨勢;2糧食主產區的擠入效應大于糧食主銷區的擠入效應,但近幾年糧食主產區擠入效應呈現下降趨勢,而糧食主銷區的擠入效應保持緩慢增長。
(二)對策建議
第一,繼續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公共投資規模和強度,重點投資消費效應顯著的農業基礎項目,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內部結構”。
第二,“存量”與“流量”并重,落實基層管護責任,通過管護提高農業基礎設施“存量”水平。
第三,提高農業基礎設施與其他擴大農村居民消費主體的協同性。
第四,完善區域農業基礎設施體系,增強區域協調性。
[注釋]
①張軍(2004)設為9.6%,雷輝(2009)設為9.732%,單豪杰(10.96%),所以本文的折舊率為10.1%。計算方法如下: Kt=(1-δ)Kt-1+It,K和I分別表示t期農業基礎設施存量和當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② 農業基礎設施投資額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③糧食主產區包括遼寧、河北、山東、吉林、內蒙古、江西、湖南省、四川、河南、湖北省、江蘇、安徽、黑龍江;糧食主銷區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
[參考文獻]
[1]Aschauer,David Alan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3(2):177-200
[2]楚爾鳴等基于面板協整的地方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關系的實證檢驗[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8(6):5-10
[3]李建強政府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需求的動態影響[J]財經研究,2010(6):102-111
[4]陳沖政府公共支出對居民消費需求影響的動態演化[J]統計研究,2011(5):13-20
[5]謝建國等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一個跨越替代模型的中國經驗分析[J]經濟科學,2002(6):5-12
(責任編輯:梁宏偉)endprint